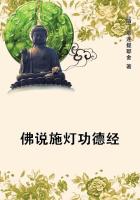雨,一滴,一滴,一滴,穿过林叶,洒过池塘,卷几个漂亮的涟漪,润物无声。
青儿踩着深深浅浅的水露,奔跑在永安当后山的竹林里,着急的心情就像小鹿一样跳个不停。
小楼犯了错,被他爹罚捆在林尽头八角亭外的黄桷树下。那孩子还不到5岁,是什么弥天大错,才会有此等重责?
听伙计说,他弄坏了铺子里的古董。7岁余月的青儿想不明白,不就是些铜器玉器,最多不过打了易碎的瓷器,难道,古董的价值会比小楼还重要吗?
昨日景天大发雷霆的模样,她仍历历在目。那是她从未见过的小天叔叔,眼中有火一般喷簿而出的愠色。然而她却没能想明白个中缘由,亦不敢开口询问。
景天怒发冲冠,脚蹬屋地:“我时日无多,一定要在走之前教好这个孩子!”
雪见无法阻止,在厢房惆怅难眠,紫萱安慰了她一整夜。
今日未至拂晓,小楼便被爹从被窝里拽出,径直绑于了竹林之缘。
青儿赶至,远远地便看见他脚尖点地、浑身难安的模样。
髫年的小楼身高只三寸有余,绳索离地约摸半丈,即使双臂伸直,他的脚也无法完全平掌落地,只能倚重脚尖,于落叶表面一点、一点。
青儿四顾张望,终于发现一块石板,蹒跚着步子抱起,半拖半拉地置于小楼脚下。
高度刚刚好,起码,他现在能歇一歇手臂。
雨势渐狂,小水落得密了,点点滴滴浇于两个孩子身上,沾衣欲湿。
凉亭就在旁边,而小楼,无法移步躲雨。青儿出门的急,亦无备伞。
西南的雨季枕着春深,不少树木此时已枝繁叶茂。青儿机敏,懂得四处寻觅,终于在石阶半腰,发现了一棵芭蕉。
她小跑奔至,踮脚扬臂,生拉硬拽,总算摘下了最大的两片,举过头顶遮住雨滴,回到小楼身边。
蕉叶不硕,却恰好能护得两个娇小的身形不湿发肩。
这两个孩子,自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仿如亲生。
^^^^^^^^^^^^^^^^^^^^^^^^^^^^^^^^^^^^^^^^^^^^^^^^^^^^^^^^^^^^^^^^^^^^^
紫萱抱小楼进屋时,青儿正扯住母亲的衣角,乖巧同路。
雨疏风骤,海棠依旧,粉色花冠向屋前开,如同两百多年以前,南诏的草丛里,肆意绽放的那一片鸢尾。
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恼,须道花枝好。一向发娇嗔,碎挼花打人。
他和她在南诏的短暂相处,并不平和安宁,折枝掷人,辣面裹腹,溪头生怨,含怒离走。
实在桩桩都是曲折的回忆。
或许生活就是这样,哭有时笑有时,欢乐有时,悲伤有时,当时只道是寻常。
原来,当时以为是寻常的,都是一去不复返的,易碎时光。
可如今,小楼弄坏的却不是什么易碎品。
五斗柜顶格,安静地躺着那一只、折了翼的金色马面具。
两百多年的风雨洗礼,它依旧保持着优雅姿态,笑傲人间。可以看出,无论是它原本的主人,还是交托保管的掌柜,都将其视如珍宝。
可惜稚子顽皮,好奇想取,搭了凳子刚刚够着,忽在触碰的瞬间凳摔人仰,面具亦随着指尖的滑动飞出,先于孩子落地,被他并不沉重的身子压断了翘起的如翅膀一般的马尾。
昨日夜里,景天进屋见状,终于生怒,狠狠凶了孩子一道,又施了今日之罚。
面具的女主人对此倒表现得异常平静。在外人眼里她本就不记得这只金色马面的来历,又如何会因它的损害而激烈起伏?
东厢里安慰了雪见一整晚,劝她切勿悲伤,虽有惩罚,孩子总不会有大碍,而她,更应该珍惜当下所余不多的韶光。
紫萱的语气始终恬淡,彷如三月东风,杨柳不曳,吹面犹暖。
然而,没有人看到,她一向纤长白皙的食指中节,被拇指的甲尖掐的通红。
***************************************************************************
美好的时光总是被岁月偷走,再细细品味时,已白驹过隙。
一晃月余。
紫萱回了CD府找圣姑叙旧,青儿留在永安当,同小楼玩耍。
端午节如期而至,一年里阴气最盛的时节。家家户户挂起了艾草,射五毒,点雄黄,结彩绳,想着法子驱除邪晦之物。
景天许久没有用的通讯器被掏了出来,拭去面上一层浅灰,幸好,还未失效。
“你是不是也胆小鬼,只有她不在的时候,才敢联系他。”
背后徒然响起的尖利女声几乎吓了景天一跳。他愕然转身,偏头扬眉:“什么嘛,今天是至阴之日,要除晦气的,我恰好想听道长念念经。”
“切!你说我就要信啊?胆小鬼,薄面皮!”雪见右手叉腰,左手食指在景天胸口戳来戳去。景天受击,主动退后,结果一攻一让,两个贴近的身影窜遍了屋子每个角落。
伙计小柳端着午间的食材从门前经过。
景天抓到救命稻草,飞扑而去,抢过小柳手中的盘子,高高举起在雪见眼前:“面皮在这里,虽然薄,但很有韧性,做成锅盔,入蒸笼的时候也不会散架。”
锅盔虽为佳肴,端午,其实还是要吃粽子的。然而青儿却不爱吃。她听了屈原的故事,总觉得粽子应该用来投江喂龙,这样,那条长长的神物就不会带走美食贡献者想寻觅的人。无论是尊敬的士大夫,还是想念的至亲。
每每这时,她就会碎碎念诅咒那条神龙,速速退散,还亲人归家,而忘却了龙是华夏族世世代代的图腾,她也算龙的传人。
阿福正打扫屋子,忽地感觉胳膊被一只手晃得厉害。低头时,小楼正望着他,满目好奇的模样。
“福叔叔,你可不可以跟我讲讲属相的颜色怎么计算呀?”
“属相的颜色?”阿福一脸迷惘。
“大人们不都说,今年是金蛇年吗?难道我是小红鼠?”
“红……红薯!”阿福噗嗤一声笑来,手中的扫帚都几乎落地。他伸出右手,一把拽过小楼,把孩子的脸捏成面具形状,“小少爷,掌柜的没教过你吗?
白生生的小爪子挠挠头:“他哪有空理我。”
“是么?那他一定焦头烂额。“阿福自言自语中,眉心微蹙。
一旁的小柳终于看不过眼,跨步上前,大发慈悲地讲解:“不是颜色,是人们喜欢在属相前面加一些特殊的形容词,代表吉祥。”
“哦,所以福叔叔你是大肥鸡,柳叔叔你是美猴王。”
额……
现在轮到两位叔叔焦头烂额了。
雪见步至走廊,便见得自家小幺正不停问着问题、而两位伙计上演着“被点穴”戏码的场景。
她舒展笑容,清了清嗓子,道:“你们把厨房里剩下的菜端到饭厅,可以开饭了。”
屋内的青儿听得开餐,合了《诗经》跳下椅子,跟着阿福背后小跑一阵,又折回雪见身边。“雪见婶婶,那我呢?”
雪见拍了拍她的肩膀,慈爱地说:“青儿乖,数一数今天一共有几个人吃饭,回头告诉小天叔叔,给大家取碗筷。”
“哦。”青儿得了任务,甜甜地一笑,随即左顾右盼地开始了计数。
^^^^^^^^^^^^^^^^^^^^^^^^^^^^^^^^^^^^^^^^^^^^^^^^^^^^^^^^^^^^^^^^^^^^^^
片刻后,屋里众人均已落座。雪见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鲜汤,午宴可以开始。
她正欲落座,发现阿福与小柳毗邻而坐,青儿和小楼一左一右紧靠景天,全桌唯一的空座,却是在小柳右侧。
雪见犹疑间,青儿已跳下凳子:“雪见婶婶,餐具是我帮忙拿的。”小楼接踵而至,摇着她的袖缘:“娘,椅子是我算的喔,也是我协助福叔叔摆的。”
不想打击姐弟俩邀功的兴致,雪见向二人一一点头以赞:“真乖,可是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的位子在柳叔叔旁边?”
小柳会意,倾了身子抱起青儿,转移到了自己身侧。
再坐下以前,小楼已经拉住了他的衣角:“柳叔叔,你不能让青儿姐姐占领别人的位子啦!”
“没关系,夫人不会介意的。”小柳言罢,意味深长地望向掌柜夫妇。
“不是啦,那是白豆腐叔叔的位子,爹爹说今天端午,妖魔鬼怪出没,所以请了道行高强的白豆腐掌门叔叔来驱邪。”
头顶有一只乌鸦飞过……
雪见面露尴尬之色,嗔怪地剜了一眼自家夫婿,伸手于他腰间一拧。
哎哟!
景天吃痛,却不得发作,毕竟是自己理亏在前,请了昔日好友出山也不曾提前告知。
阿福早已笑的前俯后仰,好半天才顺了气息,连忙询问:“那小少爷,你娘座哪儿呢?”
“啊?”小楼望着缺少席位的桌子,掰着指头核算:“爹,娘,福叔叔,柳叔叔,白豆腐掌门叔叔,青儿姐姐,一共是六个人没错啊。”
话音未落,众人不约而同地投去同情的目光。
养不教,父之过也。景天神色僵硬,思考着怎样挽回局面,一袭纯白衣襟飘向台面。
束发道人,儒雅面容,五官玲珑,信步踏来。见了桌畔情形,他将目光定格在全桌唯一的小姑娘身上,面色微动,又不露声色地隐却。
继而,他轻松地抱起柳青衣衫的小女孩,置于自己膝盖之上。
没有人看得到,他内心的波涛汹涌。
而他只是暗自运功将浪头压了下去,装作一切如常。
“幺妹,我们一起座,把空椅子留给雪见婶婶好吗?”他开口时,已像极了对一位不甚谙熟的别人家孩子的语气。
青儿从未见过这位大叔,却被他温柔的声音所动。她约略地转了脑袋,对抱住自己的人问:“你就是小天叔叔口中那位本领很大的白豆腐掌门叔叔吗?”
长卿没有应声,只是点了点头。
他害怕,一旦应声,刚才所有的伪装前功尽弃。
女孩兴奋不减,继续开朗地与这位刚结识的“忘年交”谈心:“白豆腐掌门叔叔,你好,很高兴见到你。我叫青儿,不是轻言细语的轻,也不是倾国倾城的倾,是青青子衿的青喔。”
真好,她娘把她教的外向大气又不失礼仪。
“我有个爹,好像也穿你这样的衣服,很好看。”
爹,大概是景天和雪见告诉她的?长卿如此想着,心里的郁结忽的坦然。孩子的词汇其实并不多,“好看”二字,却是他觉得此生里最重的赞美。
“我娘跟小天叔叔是好朋友喔。你跟小天叔叔也很熟对不对?那你认不认识我娘啊?”
长卿抿起嘴,露出甚符合身份的儒雅笑意:“同是天涯客,何必曾相识。”
“同——是——天——涯——客,何——必——曾——相——识——?”奶音缓缓地重复着道长的语句,偏起头细细思考其中含义,却无果。
稚女年幼,不明其意。
景天与雪见短暂地对视,又笑着切断了走向越来越歪的对话。
“吃饭吧,菜都快凉了。”“对啊,大家不要客气,随意。”
“吔,开动!”青儿在宽大的怀抱里小幅度挪了挪身子,“白豆腐掌门叔叔吃饭,小天叔叔吃饭,雪见婶婶吃饭,福叔叔吃饭,柳叔叔吃饭,小楼吃饭~~~~青儿,也吃饭。”
先客后主,长幼有序,最后也没落下自己。实在是这个年纪的孩子中鲜有的知事又不乏童真。
一时间筷影交错,座中立时箸动起来。
四分之一炷香时间后,“本领很大”的白豆腐掌门叔叔在一碟菜肴面前一筹莫展。
剥蟹,去壳,还要将蟹爪里的一丁点嫩肉毫不落下地挑出来……这实在不是他的长项。长卿已经彻底放弃,告诉笑成一团的小家伙,应该去找更熟悉指上功夫的帮手。
语方毕,青儿已利落地处理好一只雄蟹,白嫩的鲜肉被聚集到一堆。她用筷子小心翼翼地夹起,递到身后男子的唇边,笑靥如南诏陌上的萱草。“叔叔,我请你吃的。”
长卿伸长脖子去接,双眸已然湿润,只能哽咽着声音说:“景兄弟,请移开这盘洋葱。”
景天不明所以,一声尖锐的反驳:“什么嘛,这盘是回锅肉,里面的洋葱只是拌菜而已。”
甫落座的雪见用胳膊肘“中伤”了某人。“受害者”嬉皮笑脸,凑近嘴唇咬耳朵:“以后别再说我胆小了,有个人跟我一样胆小,只敢在别人不在时,才下山拜访。”
雪见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细声反驳:“第一,长卿大侠并不知道紫萱姐姐不在。第二,他喝了忘情泉,根本不记得紫萱姐姐是谁,又怎么会刻意避开呢?”
景天巧笑依旧,放大了嗓门应道:“是,是,夫人说得好,夫人的一切观点都是绝对正确的。”
“爹爹,抱抱……”稍时有懒音飘起。
原来,是小楼见了对面长慈少恭的画面,心生艳羡。
“乖儿子,爹最疼。”景天迅速地抱起身旁的孩子,得意地向对面老友扬了扬下颔,示意自己也有珍宝于怀。
“爹爹,你吃。”小楼夹了一块回锅肉,亲切地送到景天唇边。
景天故意放大了咀嚼动作,不甘示弱地挑战着白豆腐。
你样样都强过我,终有一样,我与你平齐。
长卿不语,只握住青儿的手,箸到之处,盘碟狼藉。
好难得,像个食家一般扫光餐碗,不用顾及身份,不用思考大义,不用心怀天下,只需拥着怀里简单的幸福,简单的爱,身边陪着交心的挚友。
忽如一夜花开尽,一家人就这样,有说有笑地吃罢端阳的午餐。
心中若无烦恼事,便是人生好时节。
很久以后,坐中人再忆起这日的场景,都会感激被岁月温暖过的时光。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