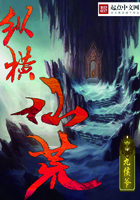二
这里远远望去,瞒眼绿色,似乎春意无限,充满生机,但走近细看,凡能入口的都己被人们果腹,荡然无存,甚至有的树叶树皮也巳被扒剥殆尽。就在这时,鲍老太太收到娘家侄儿的来信。当她读罢信的内容,颤抖着双手把信纸捂在胸口,仰天长叹:天不灭曹啊!眼下又是一年一度的青黄不接时,无论怎样未雨绸缪,精打细算,可真要接不开锅了。都说勒紧腰带也能挺两天,但要是连勒腰带的力气也没有了,无疑是等死。儿子和大孙女大孙子每天去队里磨工夫,靠工分;小孙子上学,也和大人一样没个活气,把苞米芯捣碎掺在苞米面里吃,他拉不下屎,不哭不闹只叫奶奶帮着往外抠。鲍老太太疚心啊!村里年轻人有的偷偷跑了,老年人有的领着孩子要饭去了,难道真的要走这条路一一领着小孙子去讨饭,她不敢想象。
鲍老太太出生的家庭称得起大户,从小养尊处优长大;后来嫁到地主家作媳妇,帮助婆婆料理家务,凭着娘家耳濡目染的影响,倒也能做得井井有条,实实在在地过了几年舒心好日子。社会形势的改变,她无力扭转;但历经风吹雨打,带着儿孙坚定活下去的信心,还未曾动摇过。就在她岐路彷徨的时侯,不曾想侄儿还记得她这把老骨头。从信里看侄儿过得还不错,记得当年他被打成****时,她冒着风睑,带着两个老南瓜和十几个鸡蛋,偷偷跑去看他,侄儿媳妇抱着她痛哭流濞。
鲍老太太打发儿子上赂,并叮嘱说:即使不能象信里说的那样入队落户,也要和表弟商量,让他帮着在那里找条活路,争取尽快站住脚。人挪活,树挪死,她鼓励着儿子,其实是让他明白,无论前景怎样,都不能回来了。同时,在她的心里也作着打算:一旦得知儿子的确切地址,马上就把大孙女和小孙子打发走,留下大孙子和她处理完家里的杂物随后再去。一一这里还隐藏着她的一个悲哀想法:万一活不下来,身边要有一个人把自巳埋喽。大孙子毕竞已成人,轻手利脚能够完成她的最后嘱托。
这次鲍老太太打开儿子的来信,首先高兴地看到随信寄的户口准迁证明以及里面夹带的二十斤全国粮票。她小心地把这些递到孙女的手里,心情忐忑地仔细看着信的内容,随后双手一撒,信纸飘到炕上,一把搂过仰脸看她的小孙子,激动地说:咱,得救了!她改变了主意,决定让孙女和大孙子先走,早到一天能多挣一天的工分。第二天她早早地起来进城,用寄来的粮票悄悄地带回十斤成品粮,自己留下五斤备用,剩下的装进孙女的内衣兜里。她兴奋地指挥孙儿们捆绑行李,拣日常不可或缺的东西打成三件,告诉孙子背那件最重的,最轻的一件让姐姐背,那件两人共同拎着。还要叮咛哪些话,她一时竞想不起来。
尤梅坐在火车上,看一眼身旁昏昏欲睡的二弟,机械地望一下行李架上的行李,继续想自己的心事,呆呆地望着车窗外的风景;火车与钢轨的撞击声,丝毫没有影响她的情绪。临出门的头天晚间,他和奶奶紧埃着躺在炕上,分明彼此都感到没睡着,但又不知说什么。让奶奶领着两个弟弟先走,她要自己留下,但奶奶不同意。破家值不上万贯,话虽这么说,但有些零碎东西,送到城还要尽量卖几个钱,因为到那里仍要过日子;房子尽可能卖掉,如果处理不掉,还要委托可靠的人家帮忙照看。奶奶凭着一张老脸,在人际中还有些面子,不肯让她抛头露面、一个姑娘家来处理一些想到和想不到的后事,她遵从了。即将到来的生活,她没有兴奋,也没有恐惧;如何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心中也没个谱,几缕淡淡的哀愁,袭上心头。许是不能再回来的家乡,越来越远,在她心里愈是清淅,那些熟知的人和事,仍缠绕在记忆中,俘现在眼前。年龄相仿的轻年男女,基本开始了谈婚论嫁,不是没有她心议的男子,但凭人家的条件,不可能娶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子;反过来,又有哪个有印象的青年看上自已,还没有发现,她的双眼朦胧。她掏出叠得方方正正的崭新手娟,在鼻下嗅了嗅,又不经意地拭了下眼角。这块手帕是要好的小云临行前相送的。她去向小云告别,小云很是羡幕她家有门好亲戚,把一家人介绍到一个好的明确去处,从此可以过上好日子。因为小云的哥哥逃走跑盲流己有两年,二十刚出头的一个毛头小子流落到何方,杳无音信,生死未知。小云代表家里嘱托好友到了那里要帮着留意打听,如遇到一定写信相告;那样,她或可逃离苦海,她们姐妹也能相距不甚太远,继续交好相处。
姐弟二人来到知青点,尤千里搓着双手,把一双儿女迎进屋里。多年来,尤梅发现了父亲的笑容。鲍国平下斑之后,把父子三人叫去吃了晚饭。
知青点是村民们的习惯叫法,当年知青下乡插队,队里为他们盖的三间房;东西两间分住着男女,中间生火做饭为共用。随后的几年里,知青们渐去渐少,等到返城时,房子也就闲置起来。尤千里把东间屋原有的火炕扒掉,搭起炉堂,另两间屋基本没动,自已家用。儿女到时,己准备就绪。
尤千里出生在农村,家里富裕,但从没得到娇惯。他不仅读书识字,也继承了家里打铁的手艺;成人之后,顶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帽子。在生产队里他继续打铁,当然也干其他农活。打铁又累又热,并且马虎不得,不如干大帮活轻松,队里没有几个人愿意干。等到他的儿女长大入社,身为一个阶级的徒子徒孙,自然一起去受苦受累吧。女儿学会了全部技能,儿子打个下手也游刃有余,父子三人在叮叮当当中,配合却也默契。
忙完春播,准备铲趟,一年之中最苦最累的时节就要到了。队里调试犁铧,各家各户修理锄头镐头,其他人可以借机轻松几天,尤千里父子三人却忙得不可开交。队里规定,不仅本队和社员的活要干,外村外队的活也接,至于怎么收钱,该收多少或免费,由队里定价出条。这天,父子三人刚把队里的几付铁犁打造完,十几匹马又陆陆续续牵来挂掌。拉车趟地的马一年要挂两次掌,去年秋后挂的冬掌已基本磨损,此时必须要换一茬夏掌。曹柱子牵着他那辆车的四匹宝贝,要亲眼看着它们穿上新鞋才放心。这是他的骄傲。几匹马个体并非十分强壮,但合起来能拉队里的头车,主要还是他赶车的技术上乘。他鞭头硬,一个鞭花甩起来,那马立刻有了精神,四腿绷直,合力向前;遇到坑坑砍砍的路段,别的车打站,他的车一气闯过去
曹柱子拉过一匹体型优美的枣红母马,这马目前正值黄金年口,并且怀着身孕,是队里一等一的好马。他和尤千里用绳子把马套在挂掌桩上,同时提醒慢点,连说话的声调都透着小心。他正准备跟父亲说:建议队里这匹马该休产假了,但愿这回生的马驹与它的哥哥一样强壮飘亮。
尤千里吊起马的一只后蹄,接过二弟递上来烧红的烙铁,细心地烫着马蹄,一股焦煳的香味随着淡淡的轻烟飘散。随后他又操起修刀,把烫过的马蹄修理了一番,接着就去处理另一只前蹄。尤梅拿起一支铁掌在修剪过的马蹄上比试着,随即又换了一支合适的,四颗掌钉被她利落钉进马蹄,盘好钉尖,一只马蹄挂好了掌。
曹柱子把马从挂掌桩上解下来,牵着走了两圈,步态平稳,再走两圈,四蹄不瘸不拐。他第一次见女人给马挂掌,感到惊奇。尤千里见他的样子,心里涌动着亲切之感。他主动去牵另一匹马。
这是匹枣红色的公马,是上匹马的第一个儿子,刚上套拉车不久,张显着龙性,见到挂掌桩扬鬃奋蹄,尤千里根本控制不住它。曹柱子急忙赶过来,接过缰绳,一手摩索着它的脑门,一手抚慰着它的脖颈,它翘起的尾巴慢慢放了下来,并靠向挂掌桩。马上了掌桩,他仍一手紧紧地拽着它的笼头,一手拍着它的脸,同时轻声吆喝着,似乎和马在耳语。俗话说打马摸牛,他不是没有打过它。当初这匹马还没被驯服的时侯,脖子上被套着绳子,连踢带刨;面对它的骠悍,队里其他几个车老板,尽管心中渴望得到它,可束手无策。曹柱子扬起大鞭,一个脆响,一鞭抽下,它跪在了地上,安静地被戴上笼头。曹柱子牵着它,只见它的前腿里侧,一条高高凸起的血道子。
给马挂完掌,尤千里又帮曹柱子试好铁犁;等送走曹柱子并礼让在这里吃饭时,太阳已落山了,一抹鲜亮的晚霞笼罩大地。队里其他社员早巳下工,或许吃完饭,这时,尤千里感到说不出的疲倦。回到屋里,听女儿和儿子正议论曹柱子,不知那脸是怎么搞的,对这人感到纳闷,他洗脸洗手同时介绍说:这人就是他来到这里,吃第一顿饭那家人的孩子。
尤梅已点着火,这时从锅里舀出父亲洗手洗脸剩余的热水,心里盘算着做什么饭,有米有面,可该怎样吃既节省又能让父亲和二弟吃得饱呢?她犹豫间见一人走进院来,一手拿菜刀,一手拎筐。她不认识这人,转身向屋里轻声喊:“爸,来人了。”队里一下能让她认出的人,除今天的曹柱子就是昨天来的队长。队长指示他们赶快做几付铁犁,豪劲十足地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将从这几付铁犁开始;似乎在训导着他们的无知,指引着他们的美好前景。
尤千里刚躺在炕上,身体还没舒展开,听女儿的叫声,扭头向窗外一望,急忙穿鞋走了出来。
“老会计,你这是一一”
‘‘吃饭了?’
老会计反问道,同时把菜刀递向尤千里,又指着己放在地上的筐,向跟在父亲身旁的尤梅说:
‘大春天的,没啥菜,都吃这玩意儿。’
‘这,这咋行!’
尤千里不知说啥是好,感激之情使他有些紧张。尤梅手足无措,不知是该礼貌接受或拒绝。
‘你把这刀给我收拾一下。’
说话间,老会计不请自便地向屋里走着;尤梅这才拎起筐,陪在后面进屋。老会计坐在炕上,从兜里掏出几把豆角籽和几穗老苞米,指向屋后对尤千里说:‘有空把这园子种上。这些年也没见那帮小兔崽子种出啥来,尽撂荒了。”他发现爷几个还没吃饭,就对陪站着的尤梅说:你快去做饭吧。尤梅满脸疚愧不知怎样接待这位尊贵客人。老会计掏出烟和火,向尤梅示意一下,又催促说:“你去吧,我和你爸没啥说的。”尤梅这才离开。
尤千里入队干活,最先接触的人可以说是老会计,从砌烘炉开始,又共同去城里买工具,几次感受到老会计对他的爱护,尤其是从队里借口粮时,尽管有保管员在场,老会计也让秤头高高的;接着又帮他把粮抬到加工厂,在保管员的见证下,加工出的米特别精细,去掉的糠皮让他看着都心疼。菜刀的钢口还好,只是不够快了,木把也活动。尤千里先把木把退下,重新加固;在磨刀石上,有节奏地磨着刀两面的老锈和刃口。两人说着话,共同计算打刀需要的钢铁、煤炭及人工,队里要在麦收之前生产出一批镰刀。
老会计送来的是满满一筐土豆,上面还有一捆羊角葱和两大把带根挖来的瘦弱韭菜,这对尤梅来说是多么珍贵。她解开草绳,摘了一把嫩绿葱叶,泡在盐水里,余下的葱和韭菜,让二弟栽到房后园子里。她挑出几个冒芽的土豆,小心地去掉芽,又薄薄地削了皮。她要炒点土豆丝,心想煮的小米粥可以少放一把米,不用太稠了。她煮好粥,开始炒土豆丝,又滞又涩的锅越翻动沾地越历害,挺好的土豆丝眼看炒瞎了。她急红了脸,眼泪都涌了上来。这锅是知青们留下的,长时间没用,何况又没有一点油的滋润,她没往这里想,或根本没想到;二弟帮她烧火,提醒道:“姐,添水吧,熟了就行。’
老会计从里屋出来,见到锅台上的饭,锅里的菜,又看一眼姐弟俩,没言语;出了门回头向送他的尤千里说:
‘粮没了,吱声。’
曹柱子给马挂完掌的第二天,和队里其他几位车老板赶着车,趁开犁之前的空闲到河套为队里各家各户拉秋后扒炕抹墙的黄土。由河水冲积形成的黄土,和成粘稠的泥,抹在墙或炕上,干涸之后不掉不裂。这时的河套,地己经化透,河的水位又低,能拉到最好的黄沙土。柱子他们赶着车走在拦河大坝上,嗅着青草的芳香,人马都精神气爽;瞒眼望去,一条请亮的河水温顺地缓缓流淌,与河槽相连的几条沟岔,由于河面的水位低,里面的水也断断续续,形成小小的水泊。除水之外,一片苍萃,偶儿高出的柳树点缀其中。各生产队的闲牛散马为了节省草料也已赶来这里啃青,一天基本能吃个七八分饱。牛马多的生产队派专人看管,少的与其他队合并,轮流派人。婉沿的坝梯上,朵朵蒲公英竞相开放。柱子他们沿着往年里走过的道,把车赶下大坝,寻找优质黄土坑,并且人装车也要省劲。柱子停好车,把马从车上卸下来,让马得空吃点鲜嫩的青草,解解一冬天嚼干草的谗气。他下到土坑,用铁锹清理黄土上面的一层黑土和杂物。往年里他只为自家挑两车好土,至于其他人家,赶上啥样算啥样,马马虎虎也就过去了;但今年不行,他还要为知青点拉两车和自家一样的好土,让铁匠炉的师傅把房子好好抹一抹,冬天住着也暖和。能给他的马挂这样好的掌,应该!
人们彻底脱掉了棉衣,仿佛一下进入夏天。队里留下能拉车趟地的牛马开始加草加料,豆腐渣和压豆腐流出的残汁,是很好的马料;豆腐房做出了豆腐,每天清晨都能听到豆腐倌优扬的叫卖声;主妇们偶尔捡回两块,调济着苦春的饭桌。尤梅没有买过一回豆腐,父亲和二弟也没有这份奢望。热心的人们为他们送来了咸菜酱,甚至有的孩子把挖来的野菜放下就走,都不知是谁家大人支使来的。所有这些都令尤梅感动。表婶送来几棵老酸菜,还有半罐头瓶的猪油,她试着吃了第一回,酸得直抽舌头,后来也就吃习惯了。她惦念着奶奶和小弟,该写信催问一下情况,把临来时奶奶塞给的粮票再寄回去。她看信还行,写信实在勉强。表叔家有纸和笔,让父亲去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