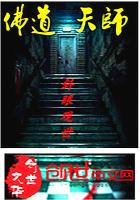那是一个人头,头发稀疏的在头顶上如同生长在青石表面的苔藓。有些粘稠的黄色液体从光滑的头盖骨不停流出来。适才瑟瑟发抖的不寒而栗在地面上卷起风沙,遮天蔽日。在那个地方,人头腐烂,旁边有个深坑,里面爬满了杂乱的荒草。
诡异的刀疤斜斜的从那个人的耳际划过整张脸庞,一直延伸到那个人的下巴,于是他的整张脸从那个地方错开,里面浑浊的液体和乱七八糟的器官都一股脑的流了出来,裸露在外面的颗牙齿上面爬满了蛆虫,还有一大群黑色蚂蚁。刘雪在走上前,只是看了一眼后,就趴在旁边呕吐不止。舍瞳和晓婷站在这个黑暗的无以复加的院落中,站在这个凉风嚣戾的院落里,站在正在慢慢腐烂的人头前,面容都看不清楚。晓婷感觉自己脚下经年累月的荒径四散崩裂,她感觉自己的皮肤正在一寸寸错开,露出里面乳白色的肉,就像这个人头流出来的白色脑浆。
刘雪已经站了起来,颤巍巍的用手臂将嘴角上残留的吐泻物擦干净,然后她愤恨的叫骂道。‘妈的。怎么回事。’
‘妈的!难道女护士真的杀了人?!’
晓婷一直盯着身旁的舍瞳,他的一双眼睛漫漶而过的悲伤,轰隆隆的辗过去,又轰隆隆的碾回来。他直挺的站在她的身旁,时间淅淅沥沥的从他身边前赴后继的死去,他一直没动,和沙漠中的仙人掌一样,失去了意识的站在那里。
‘很可能!’晓婷听到自己兴奋的附和。她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感到兴奋。她的手臂上缠裹多日的白纱布已经揭了去,上面的黑褐色疤痕仍在。她宁愿让悲伤或恐惧将她完完全全淹埋,然后看着自己被一点点折断。带着惊恐的神情,永远隔离这个该死的世界。她不喜欢在这样的时刻,露出那该死的微笑。
这让她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来自她自己本身,而且深入骨髓。
刘雪惊恐的看着她。身体一点点朝后挪动。‘你笑什么?你怎么还能笑的出来?’
‘没有啊。’晓婷微笑的看着她。她看到舍瞳也已经回过神来,神色看上去非常疲惫。‘我只是在想,会不会女护士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
‘什么真相啊。一定是她杀了所有人。她就是凶手’
‘可是理由呢?’
‘我怎么会知道理由。真好笑。’刘雪气愤的将双手紧握,突兀的白骨看上去异常清晰。‘我们问问她不就知道了。可是你敢吗?’
她脚下的荒草不安的挑拨着那天的时光,脆裂的白瓷碎地的声音,几乎让她在那天那个无比压抑的气氛中窒息而死。她忘了后来是怎么回的房间。她躺在床上的时候,天光大亮,好像时间才过了一点,又好像时间已经过去了许久。她躺在床上睡意全无。满脑子里都是刘雪微笑的说出的那句话。‘你敢吗?’
我有什么不敢。
女护士在周一早晨,给她们送了一次饭。头发绾起来,帽檐压得很低,将她的两边耳朵都遮掩在内。她临走的时候,回头冲大家微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只是在他们心里,早已有了一个计划,她们决定先不要将事情挑明,她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跟踪女护士。
晓婷第一次感到距离真相如此接近。她既兴奋又不安,在床上辗转难眠,被单被她揉皱成一团。将那天的仅有时光全部埋葬在里面封印着睡眠。
周五的时候,墙面非常潮湿,挂在线绳上的枕巾到了下午还没干透。女护士来回去了食堂几次。走廊里的灯亮了一天。
周六的时候,晓婷在床上滚过来又滚过去,尽管天光弥散,她却总是感觉自己身处霰雾,看不清任何东西。那天的时候,她们尾随女护士,看到她去了厕所几次,进了一些不知名的房间,出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她去食堂的时候,分别在早晨7点,中午11点,下午2点,和太阳西落之后的6点,还有夜晚9点。
九点回来的时候,她手里多了两个纯黑色的塑料袋,里面的东西在她走动的时候,不停发出稀稀落落的耸动声。她穿的是高跟鞋,这是晓婷第一次看到她穿高跟鞋在走廊里来回穿梭。
好像她生怕别人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干了什么事情。
中午两点她站在食堂门口,里面潮热的湿气铺天盖地的从敞开的门缝中流窜而出。扑打在她不施粉黛的面容上,流离出百味陈杂的光芒。她在走进去之前朝两边不停观望,如同一个间谍在执行秘密任务。她没看到他们是因为她没回头。他们不清楚为什么她始终都不回头看。她的衣摆在手臂不停回摆的时候,寂静的尸体腐烂成殇的声响回荡在幽寂的森林,没有道路的,伸展向可怕的远方。
晓婷拍了拍头,发现自己又胡思乱想了。自己这些天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总是浮想联翩而且不停伤害自己。她很多次都以为是女护士拿来的拿些食物里掺了东西。可是她奇怪的是,为什么舍瞳没事。难道是-----?
晓婷不敢再往下想了。
周天的时候,晓婷她们没有看到女护士去了什么地方,因为她们来到女护士门前的时候,女护士的房门已经紧锁,天黑下来,她也没有出现。整个人就像突然蒸发掉了一般。消失在了窄狭而细碎的时光罅隙中,在细水流长的光芒和色彩斑斓的切割下,她就像一枚灰尘突然就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