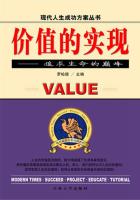我没有瞎子算命的本事,我唯一能和瞎子比肩的,就是终日的宅。什么又是宅呢,我想来想去,宅就好比是个王八蛋,虽然藏在蛋里就能高枕无忧,可总也会有孵化出壳的那一天吧。撇去今天不算,我在家里已整整宅了500天,生活若可以用除法归结的话,那我宅在家的日子除2,就是我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么下去终归也不是办法,我虽没有鸿鹄之志,可自食其力这点信念我还是早就竖立的。
此刻的家就如同一棵大树,在我的兄弟姐妹们饱尝日晒风吹时,我却仍能背靠这个既安全又安稳的保护伞里赖以生存。当我慢慢意识到,已不再适合继续混杂在未成年人这个受保护的群体时,我猛的拍了桌子,伸出生疼的三只手指,生平第一次发誓:我绝不再去守株待兔了,我也绝不再相信世界上会有近视眼的兔子。于是我在24岁这年脱去火红耐克,换上黑色夹克,冠冕堂皇的对我娘说:光宗耀祖,指日可待。
人嘛,总得在成功前就先写好理想,以便在成功后发表阔论不是?我一面在博客里滔滔不绝去记述我创业前的雄心,一面在电脑桌上吃着江米条儿,喝着绿茶。食物一直以来都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源泉,我想不管创业成功与否,我都还要活着不是?很多次我都把自己写的义愤填膺,那只准备去拍电脑桌的手,每次扬起后又都缓缓放下。电脑桌像是我和电脑之间的桥梁,如此,水一样平淡的生活才不会把我逾越。
我告诫自己,梦想才是我不断追逐的岸边,随即我便让博客草草的进入尾声阶段,然后双脚把鞋子胡乱一甩,侧着身子倒头睡去。梦想嘛,不过是梦中的胡思乱想罢了。可梦中浮现的并不是我日后的辉煌,而是一双破旧不堪的球鞋,它那满是疮痍的面孔正对我进行严苛的审问。我的鞋子从来都是遵循自然旧的过程,我从来都不会刻意擦去鞋上的泥土,就像我从来也不会强迫自己遗忘生活里,那些意义非凡的昨天。
那是在我小学六年级,正值十三周岁的那个夏季。我伸手向我爹要钱时,我爹立起眉头说:滚滚滚。我迫于生活,才第一次启动了脑子里的赚钱按钮。当时我娘把三张崭新的百元大钞从中间对折,然后娘把这三张折的很精致的钞票,塞进我衬衫的口袋里,在用一支别针把口袋封住,最后拍拍我的屁股说:儿啊,去吧。我就犹如一匹脱缰的小马受到了主人的鞭策,驾驶着一辆满是泥土的飞鸽牌女式自行车离开家,然后径直冲往城里最大的批发市场。
我把双腿频繁的弯了又直,直了又弯,滴落的汗水顺着自行车前梁一直流到大盘,飞鸽的标志终于在前梁的泥土中露出了端倪。我怀揣着三百元钱,就像怀揣我的所有梦想,此刻的我幻化成了一只飞鸽,在炙热的骄阳下,不知疲倦的飞舞。
顺着出门前母亲给我指引的路线,我不费吹灰就找到了批发市场,算上中途小便的功夫,总共花了35分钟,我看了看表盘,时针已经游走到5的位置。
批发市场像是我的一个心结,我心向往之,可却一直未能了却夙愿。当我由一个不知名的巷子穿出,清晰的望见令我神往的批发市场时,我似乎开始了一种莫名的激动。
这里有一条很长的商业街,商业街又分支出好多的丁字路口,这些丁字路口限制着人流的肆意通行,人群在这种限制里被压缩的密密麻麻,人们都直挺挺的站着,弯腰这个异常简单的肢体动作,在这里竟会成为一种奢望。批发市场人流的数目似乎不能用潮来形容,我觉得更像海,而且还是黑海,远远望去黑压压一片,我想这多半都该归功于中国人的发色。
在我看惯了合作社里井然有序的队列时,我的视觉在批发市场里第一次遭受冲击。在这种视觉冲击力下,我不知道批发的究竟是货,还是人。
当我正在犹豫是否挤进这个盛大的商品交易中心时,却被迎面而来的一个很胖的中年男人狠狠的撞了一下胸口,我立即下意识的去摸衬衫口袋,还好,梦想仍在。之后我用梦想和一个中年妇女摊位上的货品进行了交换。她没有褒扬她袜子的质量,所以我也没有和她过分去讲价格。她的战利品是得到了三张折的十分精细的钞票,而我却换来了一堆我这辈子也许都穿不完的袜子。
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三个旅行包,把袜子一只一只的往里捡。开始我数的还极富耐心,后来烦了,就索性不管塞进了多少,只是塞满一包后,就去塞下一包。当我发现每个旅行包外的图案,都由一名瘪瘪的少女变成一位孕妇时,我竟鬼使神差的笑了起来。
这之前,我曾把梦想看的很轻盈,如果我会武功,我一定用乾坤大挪移把我的现实和梦想转换一次,倘若在古代我一定能成为个绝世高手,可如今我只能感慨生不逢时。我愈发觉得自己脚步的迟缓,三个塞满袜子的包似乎正顽皮的消耗着我硕果仅存的力气。我用胯部倚着车身,腾出两只手,然后五花大绑的用绳子把这三位“孕妇”扎在自行车后座上。我扎的过程极慢,我要不断去摇晃包裹,以便确认它们与绳子的松紧程度。
我实在是没了力气,蹬上几圈就会随着轱辘的惯性而歇上几圈,一路上我就这么歇歇蹬蹬。骑到一半路程时,我开始担心身后的旅行包会否掉落,于是我开始用一只手扶着把,而另一只手去扶身后的包,自行车在我这种不太熟练的姿势中开始频繁抖动,我在抖动中也开始频繁冒汗,我生怕我会和身后的包裹一起坠落。车轮却并未因我的恐慌而减缓转动,回家的欲望像是炙热的火,点燃了我身体中的小宇宙。
途中我偶遇一位菜农,他挥舞着马鞭,那匹看来和他年纪颇为相仿的老马,在他的吆喝中不断前行。这种场景如今在城市中并不多见,可在我孩提时代却是司空见惯,所以令我惊讶的并不是能在城市里看见马车,而是遇到一匹和老农同样干瘪的老马。我加快了速度,当超过了马车有二十多米远后,我把闸皮搂的吱吱作响,然后猛的停下,一只脚撑在地面,一只手去擦拭脸颊的汗水。
我转过头打量这匹和我同为强弩之末的老马,这个在骄阳下比我还要倔强的赶路者,也在和我同样的气喘吁吁。马脑袋由远及近的变得愈来愈大,我在老马的瞳孔里看到了一个缩小近百倍的我。
我推着自行车,和马车并驾齐驱。我看见老马的头上戴着一顶柳条编成的草帽,而我光秃秃的脑袋却被太阳毫不留情的灼烧。老农坐在马车上,垂着两条腿悠扬的哼着小曲,烈日炎炎里,老马头上的草帽比起耳畔的小调,似乎更像是一种嘉奖。
生活,哎,生活,就像老马和我的脑袋,或许带上草帽就会惬意,没有草帽就会抱怨。我豁然觉得这匹戴着草帽的老马很美,它总在平静的追逐前方的路,而不去抱怨脚下的坎坷。说话间马车把和我的距离越拉越远,此刻留在我眼底的,除了马屁股后那条像姑娘辫子一样飘散的尾巴外,就只剩车后满载的大葱。葱堆上铺着一张破旧的稻草席,葱叶无比娇羞的躲藏在毛茸茸的闺房中,只有像老农胡子一样苍老的葱须,仍在陪马尾巴一起向我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