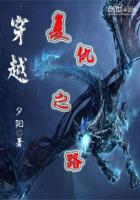诺厄缓缓吐出一口气。
“面试的时候,叶翔和宫野唯哀发现他拆掉了检查装置后就留意去打探了一下,这个孩子租了一间小公寓住,周围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他,性格很孤僻!”他说着转身从身旁的档案袋中抽出了两张几乎一样的照片,并排推至两人面前。
头顶的水晶吊灯照着照片上的一片墨色,一瞬间吸住了两人的目光。老旧的公寓天台上,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坐在天台边缘,大半个身子晃在楼外,咖啡色外套白色内搭,深灰色牛仔裤,霓虹的光从背后射过照在他的侧脸和眼眸中,好像一切都是透明的,静止的。
屋里静了下来,三个人不约而同的再次陷入沉默,一片死寂中,舞衣缓缓站起,转过茶几走到那张欧式长条形餐桌旁,单手一撑坐在桌面上,两脚轻轻晃动,像是踢起了一朵又一朵水花。
“嗳?”诺厄一愣扭头过去看她,舞衣目光空空的,像是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她扯出一丝淡然的笑,脸上却是一层吹不散的落寞。
“没有月亮呢!"
她微微抬起头,目光聚焦在水晶灯闪动的光斑上,脸上淡淡的没什么表情,像是真的面对着一片漆黑的透不出光来的夜色。
”这······间歇性神经错乱了么?”诺厄有些愕然,本来舞衣的表情安详的犹如一张油画,再配上娇媚动人的脸,足以让大批小男生喷鼻血而亡,但是放在这样的环境中就显得有点恐怖了,就像是你看古装剧男侠女侠骑在一匹骏马上狂奔,额发飞动眉目含情,浪漫的一沓弧度,但过两天剧透出来了,如果你再看见那样拉风的场景竟然是骑在木凳上,被大功率吹风机迎面吹着拍出来的,大概就一点儿美感都不剩了,只剩下点窘和搞笑。
“嘘,别说话!”冽比了个小声的手势,也看着舞衣,眼神温柔。
“嗯,总是一个人······很倔强的性格······经历过很多事,喜欢高和安静的地方,不爱说话,有些本能的逃避人却又希望有人能真正了解关心自己,嘛,一个死小孩么!”舞衣忽然深深的吐出一口气,从桌面上跳下来,随即咧了下嘴俯身揉了揉自己的脚腕,把棉拖鞋甩掉光着脚蹦到地毯上,剪得圆圆的脚指甲上涂抹着一层银白色的指甲油,“呵,脚疼脚疼,还是不习惯穿高跟鞋!”
“侧写啊!”诺厄忽然明白了,这是一种犯罪心理学常用的手法,把自己想想称当事人,从而揣测出他人的心理甚至事发状况的方法,“没想到你还会侧写,留了一手啊!”
“没什么,最近没事干,就学学玩的,技术还一般般呢!”她蹦回沙发边坐下,端起酒杯猛灌了一口,一股酸意钻进喉咙,舞衣吐了下舌头,满脸通红被呛得一阵猛咳,冽有些无奈的拍着她的后背,这时候她看上去就还是个小孩了,整齐柔软的齐刘海漆黑得象丝绸缎,让人有种想伸手过去摸摸她脑袋的冲动。
“死小孩?你们90后的名词很难理解啊!”诺厄玩弄着已经空掉的香槟杯,舒服的后仰,整个人陷在沙发里。
“死小孩就是死小孩喽,就是什么都自己死撑着不给别人看喽,心里明明很难受还硬是要装出一副我很好的样子,佐助就是个死小孩,鲁鲁修也是,月咏几斗也算喽······”
“你的脑袋里难道除了动漫就没有一两个名人了么?”诺厄叹了一口气,把照片收回,“还比如说,你也是个,嗯,死小孩!”他扣好文件夹的扣子,低着头有意无意地说。
冽心里一颤,下意识的看向舞衣,舞衣低着头,细密的睫毛低垂,像是盯着地毯上很淡的米白色花纹发呆,她撇了撇嘴忽然有些生气,诺厄总是超犀利地一把就把她的伤疤给揭了,揭完还一脸不关我事的路人甲表情,但其实他说的也没错,舞衣就是一个死小孩,前些天过完二十岁生日后,她就买下英皇顶层自己搬出来住了,百里风派人叫了她两三次,她就是不肯搬回去,也没有人知道她是一时兴起还是在闹什么别扭。舞衣从小就是这样,有什么心事从来不给大人说,而且心事总是稀奇古怪的,她爸妈想破脑袋都猜不出来,所以冽总是被委托去探听她的想法,然后打个小报告给他们。
“嘛,是又怎么样,死小孩都很帅的,一个笑容秒杀一军团的少女嘞!”她抓过一个垫子抱在怀里。
“你爸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诺厄又轻描淡写地说,“那个老家伙很头疼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看起来你永远是个小孩子。”他指了指舞衣怀里的垫子,偷偷对冽挤了挤眼睛。
冽一愣,准确来说应该是打了一个冷颤,感觉这个快一百岁的老家伙像是给自己抛了个媚眼,还抛得含情脉脉的,诺厄右手依旧端着香槟杯,左手缓缓地比出了三个数字。
二,五,二。
冽猛地明白过来,他微微一笑,对诺厄点点头,这是他和百里风的默契,每次百里风搞不定他的宝贝女儿时就会悄悄比这个手势给冽,“二五二”是一种不能或不便说话时的求救信号,意思也就是SOS,百里风又把这项探听的工作委托给了冽,但其实也只有冽可以胜任,舞衣那种死小孩也都是有自己的软肋的,佐助的软肋是鸣人,几斗的软肋是亚梦,而她的软肋,大概就是冽了······
“呀,感觉自己瓦数一下子上升了,你们两个是在眉目传情么?虽然现在网游上禁断恋很多,但这爷孙式禁断总还是不好······”舞衣偏着头看向两人,满嘴白烂话。
诺厄有点尴尬的干咳一声,站起来绕过茶几拍了拍两人的肩。
“这项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两个年轻人了,我这位老人家也该回去睡了,给你们准备了客房,这两天就在我家出题吧,这份试题是绝对机密,不能外泄一点点。”诺厄喝干了瓶中最后一点香槟,潇洒地转身冲两人摆摆手,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转回身来,“对了,晚上最好还是不要出去哦,保不准有狼!”
“怎么有种完事会被你灭口的感觉?”舞衣从沙发上跳起来,羊绒地毯柔软得像是棉花,她在原地蹦了蹦,“嗯,好舒服,羊绒果然要比羊毛软!”
“喂,很贵的,别当蹦蹦床使!”诺厄有点无奈的扶额,“你这神转折的思路,我只是打算在考试结束前把你们两个关在一间小黑屋子里罢了!”
冽看了诺厄一眼有点无力,真想象不出他竟然是出生在一九二几年的老古董,按理说那个年代的人不都应该和《山楂树之恋》一样牵手还要找根树枝么?就算有着欧美开放的血统,怎么连一点儿矜持都没有,几句话从内而外透着一股······冽忽然词穷了,一时间竟找不到词来形容他。
“笑得好猥琐······”舞衣皱着眉,很默契地帮他补充完整了内心的OS······
诺厄不再说什么,微笑着拉开门转身关上,门合严的那一刹那,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舞衣盯着门发了一会儿呆,忽然拿肩膀拱了下冽。
“嘿,要不要去看星星!”
“星星?校长不是说别出去么?”
“切,那种骗小孩的话你也信,如果能找到自己的星座,对着它许愿会很灵的哦!”
冽心里一动,“你想许什么愿?”
“秘密!”舞衣穿上棉拖鞋拉开门一溜小跑,“愿望这种东西说出来就不灵了,而且”她回过头狡黠一笑,可能是因为喝了酒的关系,脸庞粉红。
“有些愿望不适合说给你们听啦”她忽然换了英文,眼睛眯成一条缝,小狐狸一样笑了。
“Thegirl‘ssec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