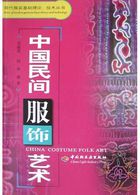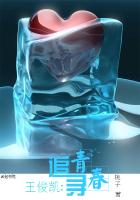林桃烟又敲了次木门:「荷阳师父,是我,桃烟。您在屋内吗?请开门。」
门内依旧一片寂静。林桃烟「咦」了一声,伸手推推木门,门没阖上,「咿呀」一声,开了。屋内空荡荡的,没有人在。
「奇怪,荷阳师父上哪儿去了呢?」林桃烟轻声自语:「说好要带解谜的人来,这会儿应该要在屋内等我们呀!」
林桃烟伸手从耳旁拉出便利铃,按下几个键。
阮潚玉踏入屋内,环顾四周。小屋布置得十分典雅,墙上挂着字画。字是颜真卿的临帖,画是细致的工笔画。画中美人侧着脸,目光微敛,嘴角似笑非笑,清秀雅致的脸上带着傲气,灵秀动人,柔中带刚。
「不行,无人接听。」林桃烟叹口气,收了便利铃。
「桃烟,这是妳吧?」郭依柔指着画中女子问道。
林桃烟抿嘴一笑:「是我没错。荷阳师父本月初才作的画。」
「怎么觉得画中的妳和真实的妳不太一样呀?」郭依柔侧着头,略带疑惑地皱起眉。
林桃烟笑笑:「绘画原就无法等同真人,不是吗?」
「这个荷阳师父年纪多大了?」阮潚玉忽问。
「八十五了。」林桃烟疑惑地问:「怎么了吗?」她忽地醒悟,急忙解释道:「我们只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荷阳师父找我当绘画模特儿别无他意,你别误会。」
阮潚玉皱着眉没说话,只是伸手朝墙边的原木拐杖一指:「这荷阳师父的腿脚不便吗?」
林桃烟点点头道:「是啊,荷阳师父年纪大了,出入都需要这根拐杖。没了拐杖,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阮潚玉凝眉:「你是说,他人离开了屋子,却没带着拐杖?」
林桃烟一时警醒,有些慌张起来:「是啊!可是,这不太可能……」
「……奇怪了。」阮潚玉沉吟。
「会不会是有人强行带走了他?」蓝莫庭插嘴。
「嗯……」阮潚玉环视屋内,道:「屋内整整齐齐,丝毫没有打斗过的迹象,我不认为……」
「那么,这样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会丢下拐杖去哪里呢?」蓝莫庭问。
林桃烟也是摸不着头绪,只得抬头对众人笑笑:「既然一时见不着荷阳师父,我们还是先去找下一位人选吧!」
第四位长者名叫天紫,是位沉稳睿智的中年人。木屋里的架子上,摆满木雕作品,桌上还搁着几件小型的未完成品。
天紫身形硕长,双手满是雕刻所遗留的伤疤。见到阮潚玉,他慢悠悠道:「我不愿意说谎,也对啸渊这种无聊的把戏一点兴趣也没有,所以不论你们问我什么问题,我都不会回答。我还有雕刻品等待完成,不留各位了,请回吧!」
阮潚玉被天紫一下把话堵死,只得摸摸鼻子道声谢,悻悻然离开。
刚踏出木屋,郭依柔忽然脚下一绊,身子晃了晃,一块扁平的方形事物从口袋掉出。她却浑然未觉,只是自顾自地向前走。
林桃烟急忙上前一步,捡起那柔软的白色方形事物,提高声音呼唤郭依柔:「郭小姐,妳的东西掉了。」
「啊!」郭依柔回头见到那方形事物,立刻胀红了脸,一把从林桃烟手里夺回,塞进怀里。
林桃烟有些受惊,连忙问道:「怎么了?那是什么东西?」
郭依柔抬头望着林桃烟,眼眶泛红,眼中彷佛随时要滴出水来。那神情,既疑惑又委屈。她狠狠吸了两口气,忽地拔脚冲进树林里。
「怎么了?」众人不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忙跟着追上去。
几百公尺开外,郭依柔蹲在树根旁,曲手抱膝,头紧紧地埋在双臂中。
林桃烟拉拉旗袍蹲下,轻柔地拍抚着郭依柔的背脊:「郭小姐,没事吧?」
「我没事,我很好,别再管我了。」郭依柔闷着声音道。
汪子骐翻了个白眼:「啐!麻烦的女人!郭依柔,我们没空陪妳使性子,阮潚玉还有性命悠关的事情要办呢!」
阮潚玉抬起手,轻声道:「不……正好我也累了,就在这里坐一会儿,整理一下思绪也好。」
汪子骐不满地望向阮潚玉,正要开口反驳,却发现阮潚玉的眼神中果真带着几许迷茫和不解。
「你发现什么线索了吗?」汪子骐问。
阮潚玉朝汪子骐摆摆手,示意别再多问,就在桃树林中席地而坐。他倚靠着树干,静静地闭目思索。
好一会儿,阮潚玉才睁开眼,问林桃烟:「桃烟,以天紫师父这样的性子,怎么还会帮着啸渊师父隐瞒身份,而不直接点破答案呢?」
远方,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那还用说!当然是被啸渊抓住了把柄!」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佝偻着背,缓缓朝这里走来。
「这位是玄羽师父。」林桃烟道。
「闭嘴,没人问妳。」玄羽冷道。
林桃烟抿了抿嘴,低下头没再说话。
「装那什么小媳妇脸?看了就恶心。」玄羽再喝。
阮潚玉有些尴尬,急忙岔开话题:「玄羽师父,您刚刚说天紫师父被啸渊师父抓住把柄?怎么回事?」
「呵呵!」玄羽笑道:「谷内的人可都是清修者,有哪个人会无聊到玩起了猜谜游戏?大家卯足劲,勉强陪着啸渊演戏,还不是个个都被抓住了把柄嘛!」
阮潚玉思索了会,点点头道:「您也无法告知我们答案。这么说,您也被啸渊师父抓住了把柄,是吗?」
玄羽声音哽在喉咙里吐不出来,好半晌才悻悻然转身,丢下话来:「反正我不会是啸渊就对了。小伙子慢慢找那浑蛋吧!」她忽地止住脚步,回头对阮潚玉促狭地笑笑:「对了,我可以提醒你:最不可能是啸渊的人,就是啸渊哪!」
「最不可能是啸渊的人,就是啸渊……」阮潚玉凝望着玄羽离去的背影,缓慢地复诵。
「依你看,最不可能是啸渊的,会是谁呢?」汪子骐问。
「以我们至今遇过的人来看,我认为电工师父最不可能。」阮潚玉道。
「那么,就是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