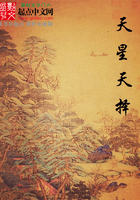出殡之日,细雨蒙蒙。沾在脸庞上的水滴,悄然地扮作眼泪。巧莲木然的抱着父亲的灵位,不语不言,如失魂的布偶,吃便吃,睡便睡,规律得让人心疼。
邻县的陆家自备送丧行头,有些讨好之意。巧莲默不作声,采衣与其它的姑娘唤着人,将他们打发了回去。
丧礼的正日,陆家的二老亲自来,面色憔悴,浑浊的眼睛下也肿胀了几分。他们跪着在灵堂之外,无人搀扶,也无人理采,直到午后礼毕的乡民归来,依旧跪着。
采衣想代巧莲掩上门,可门外的妇人一声“姑娘”扑进了屋,老泪纵横的向巧莲诉哭:“请姑娘饶了小儿!杰儿年少无知,请姑娘饶了你吧!”
妇人磕着头,连连说着自己的过错,愿以命换命,或是为巧莲家做牛做马也无半句怨言……妇人说的极多,言下之意,是求巧莲给陆家留下一脉。没有其意,主家母首先要虑的是给夫家多留子嗣,在陆杰这一辈,就姐弟二人。陆家的香火全指望陆杰了,他要没了,妇人九泉之下还有何颜面见陆家的列祖列宗?
陆家的当家还跪在外头,低着头,不见神情,听着妇人的恳切言词,不由得轻叹一声。
妇人还在说着,而巧莲冷哼哼笑出了声。
“哈哈哈!他年少?他无知?无过无错!那我爹爹横死于他手就是最该应得?哈哈——我为何要饶他?我恨不将他撕成碎片,扔进仙女湖喂鱼去!给我滚,滚得远远的——”
妇人还在央求,却当突然起身的当家,拖走了。
久久的还能听到妇人咒骂书生之类的言词。陆家其实也不过是个书香门第罢了,何来权势?无非生个女儿,进了王府,入了王爷的眼。
旁人总会简单的概论听闻的事,无八九分全真,也有六七分意,到最终不过一切传言。
头七的夜里,在云来家酒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子兜着风衣出现在了巧莲家屋外。与她同来的还有一位男子,性子不如女子柔顺,十分傲野好动。
“是望霞姑娘?”采衣不清楚二人为何特意出现在这儿。
“是。姑娘出门八九日未归,望霞只能寻到此处来了。”望霞言罢,从袖中抽一封书信,递于采衣,道:“是小姐临行时言明留给姑娘的。”
撕开信件,信上没有留下字句,只画了些花花草草,一条小路上跑着马儿,两个娃跟着背着书往东走,接着是山头,还有是雪或是雨状的之物。
采衣不明所以,抬头递出信,摇摇头道:“不太明白。”
“这还不明白?花花草草枯了景色不好看,他们师傅三个去别地方看雪山了。”天旋抢过信指着画道。
“是望霞的过错,没能向姑娘解释清楚。小溪姑娘正是我家小姐,承蒙姑娘多次照顾,望霞代家主谢过姑娘了。”望霞施福欠身道。
“望霞姑娘言重了,先生等人于我有救命之恩。”采衣惊慌地连忙推脱。
“既是救命之恩,你们大算怎么报!”贸然出声的是屋里休息的巧莲,她冰凉的眼神,直直的盯着望霞。
“只要采衣姑娘开口,望霞等人必竭尽所能,以报姑娘大恩。”想来不会说出什么天外之话,他们应该能轻易办下。
“杀了姓陆的,采衣!杀了姓陆的!”巧莲发狂的吼道。
天旋怕听了心恼,一掌霹晕了巧莲,接着笑哈哈的对着痴痴的采衣说道:“晕了而已,继续。”
采衣回过神对望霞说:“如果?如果可以的话,请圆了巧莲的心愿吧!”她不由自主的想起了陆氏夫妻,白发送黑发。她这么说会不会太过?
“姑娘真是心善。秋后,陆杰就该问斩,此事无需姑娘要求。姑娘若一时想不出有何要求,大可放在日后提起,此约定永不作废。只要姑娘想起了就可去同福楼亮出这块玉佩,自会有人引姑娘见望霞。”
同福楼?深夜,采衣还是思量,有着千金小姐不作,何苦跟着先生游四方?而先生为什么要离开?真只是为了观遍天下美景吗?
昼夜漫漫,千翻侧转,她难以为入眠。
柳国,版图之大远胜于北楚,耕地贫乏自是不宜五谷播种,但草原空旷,牧业兴旺,与各国的贸易也十分频繁。
入得十一月,柳国的天气已如严冬。街道上来往的人群披着裘衣裹着毛领袄子,埋着头走过,看不清模样。
而不畏严寒的龆龀之童,堆着雪人玩着雪仗不意乐呼。也不知从何处传来的笛声,悠远飘渺,让人忍不住的沉沦,不可自拔。
三三两两的孩子,痴痴的向巷子的深出走去,许久都不曾出声,来寻找的大人,再也没能找到自己的孩子,似乎是凭空的消失。
“岂有此理!竟丢了十七个孩子?民心不稳,何以固国!还不让去查!”杜璟扔下手中的详文,怒气能消,满腔愤恨一言难尽。
杜夫人领着下人端来了参汤,见老爷的脸色不正,退下了随丛,亲手盛汤递到了杜璟面前,说道:“再气也不能把身子给饿垮。”
“唉,听夫人的就是。”杜璟接过参汤,想起事,对杜夫人说:“恒儿可回来了?”
“已经回来了,一年不见,性子变了不少。真不知如何是好!”杜夫人忧虑的回道。
“性子本就懦,难不成还养出个假小姐来?”说起自己的么儿,杜璟无可奈何,杜恒是么儿不错,但更是嫡子,日后还要接管家主一职,在家中时就让老太太宠上了天。夫妻二人也百般无奈才将他送入楚国的山同学院,望他的性子能有些改进。
“到也不是,现在比往日在家还多了些气势,方才竟将三房的珏儿打伤了,老三家的媳妇正跟妾身闹得慌!”放在别人家,主家的定骂上慈母败儿,可杜璟盼得几年才见儿子有那么一点长进,能不开心吗?
“这是好事!瞧瞧儿子去!”杜璟携着夫人的手,向儿子的小院去了。
杜福捧着药,拿着绵布给杜恒受伤的鼻梁上了些药。所幸不深,不至于会留下疤痕。小少爷的脾气是他一天一天见着长的。原先在山同学院还算乖巧,可近几月的,不知少爷发了什么狂。若有谁发难于他,他一定会打得对方怕才罢手。
“少爷,可好些?”杜福问。
杜恒跳下椅子,笑嘻嘻的说道:“怎么会呢?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少爷,您变了好多。”杜福有些感慨道。
杜恒摸了摸鼻子,讷讷的说道:“天天以往总说我性子懦,他定是生气了,才不来学院上课的。”
“青天少爷知道了少爷的改变,一定会来找您的!”杜福呵呵的笑道。
杜恒揪着杜福腰带,开心的问道:“真的吗?真的吗?”
大致是杜恒用力过猛,把社福的腰带都扯散了。
“哈!掉了咧。”杜恒鼓着双眼有些好奇的说道。
杜福急忙拉起裤腰,泪眼婆娑的说道:“阿福还是童子之身,少爷不兴这么逗的小人的。”
二人扯皮了片刻,杜璟与杜夫人一同踏进了杜恒的屋子。见儿子挂了彩,也不哭闹,杜璟十分欣慰。不过,作为当家之主,训斥几句总要的。
“恒儿,你可是与珏儿打过架?”杜璟摆出一副严父的模样说道。
“嗯。”仔细的瞧着儿子还真胆气了不少,可怎么就这么实诚呢?
“你为何事与他打起来的?”
“他诈我钱,还领了一群小子恐吓我,罪加一等。”说完,杜恒低着头,两指托着下巴,思虑了片刻,又道:“我揍轻了呃!”
“他是哥哥,你做弟弟怎么就不能礼让些?”杜璟憋着笑意很是严谨的说道。
杜夫人听着怎么感觉有些怪异,不免得看了自家相公一眼。
“自古只有哥哥让弟弟的,哪有弟弟让哥哥的!何况?何况他们诈我钱财,就是坏孩子,坏孩子就应该揍———小时不改,大时祸害——嗯?棒子出孝子!就该揍!”杜恒胡啾了一通,前面还扯在理上,这后面听得杜璟一口茶呛几回。
杜夫人俯下身子,好好的端细了杜恒,问道:“可是书院里先生教的?”
杜璟不敢苟同,先生都是立礼之人,怎会——怎会教出“该揍”二字呢?
“嘿嘿!是天天以往每次揍我时的说词,都能背了!”杜恒还有些小得意。
惹得杜福急得眼泪都快飙出来了。我的少爷唉!您怎么就这么实诚呢!被人揍了,也没见谁像您这么欢腾来着!
“恒儿,你先去祖母那儿请安,她叨念着你许久了!快些去吧!你父亲与我一会也会去。”杜夫人使话支开了杜恒,留下了杜福。
杜福立马向当家的二位跪下,身子惊得直哆嗦。
“你这奴才!竟任由着自家主子在学院受人欺辱,好大的胆子!快说,那浑小子是何人,竟敢如此欺儿!”杜夫人怒目喝诉道。
============================================================
“阿嚏!阿嚏!”小溪捏了捏冻红的鼻子,颇可怜的对穆奇说道:“阿奇,我好像感冒咧!”
“上来吧!”
冰天雪里,小溪拎着竹筒,靠着穆奇后背的暖意,渐渐的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