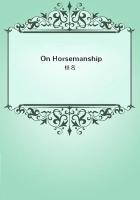第十八节:衣国的花神
看着竹筏随着流水慢慢远去,北木兮觉得心里空空的,四肢无力,自己是要死了吗?可是不能,不可以死。我要去衣国,我还要看七彩栀子,他说过,如果找到七彩栀子我会怎样,自己没有回答,是因为不相信。原来七彩栀子一直存在,只是存在的好隐秘,就像卜易,存在的好透明,感觉不到,呼吸不到,为什么不大胆一点,卜易,为什么。
为什么不信任,北木兮,你好笨,为什么不信任,不信任世界上有七彩栀子,以及和七彩栀子同样珍贵的一个人的心。
可是要自己怎么活着啊,可以怎么活着,现在的我,连死去的借口也没有了,没有了。
太阳不知何时又升起了,它微笑着,看着一切闹剧,一切惋惜,北木兮看着太阳,眼睛好疼,好疼,是什么?太阳毒辣了起来,可是自己觉得好冷,手脚无力,好昏,最后北木兮倒在了河边。
当北木兮醒过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绑在柱子上,从柱子往下望,只看到满地的栀子花,柱子四周都插满了栀子花,满天满地都是馥郁的香味。
可是,北木兮摇摇头,想让自己清醒一点,耳畔是惊天动地的声响,北木兮感觉到四周的房屋正往后移,而自己不知被什么推着向前走。
再摇摇头,北木兮清醒了八分,终于听清楚他们说的什么了,“祭花神,祭花神······”“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不断有人重复着,北木兮终于清楚了,原来人们是在祭花神啊,“可是”,北木兮皱着眉头,“可是,不对啊。”喃喃自语道,他们祭花神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会被绑在柱子上,看着满布四周的栀子花,北木兮第一次失去了想要欣赏的兴致,当前最关心的只是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自己不是在河边吗?
“喂,”北木兮喂了两声,可是没有人理她,自己依旧被什么推着前进。忽然之间,北木兮有着一种恐慌,当一个念头在头脑中炸开的时候,北木兮感觉到了死亡的恐惧,听说衣国每年都会祭花神,而他们所谓的祭花神,其实就是在族群中选取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进行火葬,以求得来年的太平。
难道他们是想让自己来祭花神?北木兮疑惑急了,可是自己不能死的,不是吗?自己不是答应过一个傻瓜要好好活着,去衣国,去看七彩栀子花的吗?现如今,衣国是来了,可是还没见着七彩栀子花呢,自己不能死。
“停下,停下。”北木兮叫喊着,可是回应自己的只是震天动地的口号声,“祭花神,祭花神。”口号并没有因为北木兮的喊叫有了片刻的停歇,人们还是向前走着。
看到自己的反抗不起作用,北木兮只得另想办法。
眼看着祭台就要到了,北木兮却没有想到任何办法,这一刻,心中充满了无助,不要死,不要。
祭台上铺着栀子花,白色的,像仙子的颜色,可是今时今刻北木兮没有丝毫觉得栀子花可爱,相反的,自己对着这个自己爱了那么多年的花有了一种恐惧。
这时,北木兮看着人们拥着一个人走向祭台,那个男子也一袭白衣,头上带着栀子花围成的花环,只见他端过侍女递上来的酒,右手食指在酒碗里点了一下,酒碗里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紧接着,男子将酒洒在祭台上,嘴里念念有词,“花神降临,保我衣国,国泰民安。”祭台之下的群众全部双手合十,虔诚的说道“国泰民安。”
连续念了三遍,台上的男子说了一句,“抬圣女。”北木兮觉得有人将自己抬起,向祭台走去。北木兮想反抗,可是不知何时,手已经被绑在柱子上,为了美观,绑住手的部分甚至插满了栀子花,可是却绑得很严实,北木兮尝试着挣脱,可是总是失败,眼看着自己就将被抬上祭台,北木兮真真实实的感觉到了死亡的恐怖,是的,自己好害怕,可是卜易怎么甘愿死去?北木兮想到了卜易,眼前不知怎么迷上了一层水雾,卜易,兮儿想听你的话,好好活着,可是,兮儿真的要来找你了,兮儿要自己找到你,不会让你总是站在身后了。
北木兮吸吸鼻子,此时此刻,恐惧已经被冲淡,她笑了,唇角上扬,微闭上眼,就这一笑,天地似乎失了颜色。
而祭台上的男子也看到了这一笑,好素净的笑容,好明媚的阳光,就像,就像,男子微皱了一下眉头,是的,就像一朵栀子花。
当车子在祭台上停下时,男子走到北木兮的跟前,看着眼前这个微笑着的女人,男子右手食指微微勾起北木兮的下颚,看着她的眼睛,男子道:“孤的花仙,孤终于等到你了。”男子亲自将北木兮手上的绳子解下,在她的额头轻轻亲了一下,将她打横抱抱起来,抬起头对着祭台下的人说,“孤亲爱的子民们,今天,孤终于找到了孤的皇妃,庆祝吧!”北木兮还没弄清楚,就被这个叫孤的男人抱走。
衣国皇宫中,孟冠棠将北木兮轻轻放在榻上,俯下身,看着眼前的花仙,孟冠棠不由自主的笑了,还记得自己六岁的时候,国父说过,将来自己会喜欢一个栀子花一般的姑娘,那一刻,自己就发过誓,如果真的碰到那么一个姑娘,自己一定要纳她为后,衣国皇后。
孟冠棠看着北木兮的眼睛,“孤的花神,你愿意做孤的皇后吗?”北木兮看着眼前这个面如冠玉的男子,身上散发着和子謇哥哥同样的气质,他的神情,他的语气,都像极了子謇哥哥,如今,他请求自己做他的皇后。北木兮看着眼前男子的眼睛,笑了,可是迟了,不是吗?是的,迟了,北木兮从他的怀抱中退出来,站在床前,面对着他,“对不起,我不能。”北木兮已经知道了,他是衣国的国君,孟冠棠,可是即使他是国君,自己也不能。
继而北木兮说道:“承蒙皇帝厚爱,只是臣妾已经为人妻。”北木兮仿佛看到了卜易站在自己的眼前,卜易,你听到了吗?北木兮不知不觉又朦胧了双眼。
孟冠棠听到他的花神说自己已经嫁人了,忙忙翻身站起,从背后抱着了他的花神,把头深深的埋在北木兮的后颈,“没关系,我不介意你嫁过人,只要你嫁给我就行。”北木兮掰开他抱着自己腰肢的手,转过身看着眼前的男子,“可是皇上,臣妾今生今世,非他不嫁。还请皇上不要为难好吗?”北木兮看见孟冠棠眼中闪落一丝失望之色,“还望皇上成全,卜北氏不胜感激。”
看着他的花仙,孟冠棠的眼中有着深深的刺痛,“他姓卜?”
继而又自言自语,“真是好运,如此令孤太羡慕了。”
孟冠棠看向殿外,正是日上三竿的时候,为什么心底会那么的冷,这么多年来,自己不曾爱过任何人,如今,面前的女子自己明明第一次见,却感觉已经见过千万次,如果自己的存在只是为了等那么一个人,那么自己可以肯定,那个人就是她,眼前的花神。
春天快过去了,天气也慢慢热起来,为什么在这短短几秒钟内,心底却仿佛过了一个冬。
殿外又有人浇水避暑了,水顺着房檐淋下,第一次觉得这个场景会如此凄凉。
孟冠棠看着殿外的雨帘,从小到大,从没有人拒绝过自己,没有人可以例外,自己是皇帝,一国之君,没有人可以和自己相比,花神是我的,会是的。
孟冠棠走到北木兮身边,“宫人们又在浇水了,姑娘可有感觉不适应?”北木兮看着殿外的水帘,这一切在冰国已见过多次,当然见怪不怪,“忽然间觉得凉快了,真惬意。”北木兮见他不再纠缠,也没必要在那个问题上久久不放,转而问道:“早就听闻衣国的国花是栀子花,所以一直想来衣国,只是没想到初次到贵国竟然遇到这种事,皇上,你们祭花不是应该挑选本国人吗,为何为难我这个小女子?”
“你不是衣国人。”孟冠棠修眉微皱,若有所思,衣国的祭祀活动只有本国人才有资格,今年是怎么回事,怎么今年的圣女竟然会不是本国人。
“那北姑娘是哪国人啊?”孟冠棠看着北木兮,眼前的花仙不是衣国人,那么自己要怎样把她留下,自己看中的女人,就算嫁人了又怎样,自己不在意,只要心意相通,又何必在意那么多。
“我是······”差点就说了出来,北木兮转念一想,如今天下三分之势,如果自己说是冰国人,而北姓在冰国是少姓,衣国皇帝一定可以猜出自己是冰国右丞之女,到时会不会因为自己而连累父亲尚不可知,再者,这个孟冠棠初次见面就说要娶自己为皇后,一定轻薄放荡,就怕最后······北木兮不敢想下去了,便改口说道,“我是灵国人。”
“哦?”孟冠棠向前逼近了两步,“北姓在灵国是少姓啊,我所知道的姓北的也只有冰国右丞家,”北木兮被孟冠棠逼得连连后退,低着头,最后被逼到墙角,北木兮蓦然抬头,“你别向前了,你说的冰国北家我根本没听过,再者如果我真的有幸和冰国北家有联系,又怎么会被你们当成圣女来祭花神?”北木兮抬着头,看着孟冠棠的眼睛,义正言辞,孟冠棠看到眼前女子突然爆发的倔劲,越发觉得有意思,自己也只是问问而已,道一声“没事儿。”便作罢。
先前看见花仙,觉得她淡雅,就像栀子花,现在觉得,那点火气似乎有了一点红莲的味道,有点火辣,却刚刚好,越发觉得眼前的花仙迷人了。
孟冠棠上前抱住了北木兮一盈而握的纤腰,手臂用力,将北木兮贴在胸前,而另一只手托起北木兮的下巴,北木兮的头不自觉的上扬,孟冠棠趁北木兮分神的空当,一个吻早已经落下,蜻蜓点水,却也惊起了北木兮双颊的红云。
北木兮发觉失态忙忙后退,边退边揩拭着被羞辱的唇,指着面前目中无人的孟冠棠,“你,你不要脸。”
北木兮觉得自己的天都快塌了,自己做了什么啊,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卜易,你说要我来衣国,可是当时如何预料的到现在的情景啊,如果可以,我就不来了,就呆在城隍庙,至少那时,陪在我身边的人是你。
而一旁的孟冠棠看到跑出去的花仙,当即给了自己以巴掌,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啊,那是他的花仙,不容亵渎的花仙,虽然自己愿意把后冠给她,即使自己喜欢她,而又怎么可以,孟冠棠懊悔的追出。
第十九节:如果可以守护
不知跑了多久,北木兮跑到一处隐蔽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满天满地的栀子花,北木兮跑到一处湖边停下,瘫坐在湖畔,眼泪吧嗒吧嗒止不住,北木兮知道自己不过是大题小做罢了,自己不是气他的轻薄,自己伤心的是卜易,自己和他的回忆也只是一个拥抱,那么爱着自己的一个人拥有的只是一个拥抱而已,北木兮想到了卜易越发觉得委屈,以前娘亲就告诉过自己要珍惜,免得失去之后后悔,自己也以为自己珍惜了,没想到到头来,却依然后悔,是不是自己永远都那么的不幸运,自己爱了那么久的人可以在旦夕之间放弃自己,而自己一直忽略的人却是真正爱着的人,“老天啊,你好愚昧。”北木兮双手捏成拳头,不断敲打着地面。
满园的栀子花开放着,白色的花仿佛也在祭奠。
不知哭了多久,就倒在湖畔睡着。
孟冠棠紧随北木兮来到花园,看着哭泣的花神,孟冠棠觉得自己错得真是深刻,只有静静的在远处看着,花神的哭声却也像一把刀子,狠狠的剜着自己的心。
原来,自己又错了,一直以来,无数的女人都争着想要自己的眷顾,所以就以为没有人可以拒绝自己,即使拒绝也只不过是欲擒故纵,惺惺作态,没想到却会令花仙如此伤心;原来,爱着一个人,是真的会心痛的。
孟冠棠远远的看着花仙,深深的自责,只是他不知道,他的花仙并不是为自己而哭。
不知过了多久,当孟冠棠发觉哭声停止时,转过头看到他的花仙蜷缩在湖畔,那么小一团,令人心痛。怕惊醒了佳人,悄悄的走过去,将她抱回凤天宫,临走时对宫人说,对待她要像对待皇后那样,不可有丝毫怠慢。
站在凤天宫外,孟冠棠觉得有一丝的温馨,偌大的皇宫,第一次让人感到亲切,不知不觉中笑容已浮上嘴角。
孟冠棠看着凤天宫的匾额,凤天,凤天,凤舞九天。花神,孤再也不会强迫你了,孤会尽力让你忘记,如果不能忘记,那么,就让孤守护你吧。
不知不觉已到了掌灯时分,夜来临了,孟冠棠看着今天的夜,越发觉得亲切,四周静悄悄的,晚春的夜静谧极了,只有月光经过树梢来到大地的脚步声,轻轻的,像一个出嫁的女子走在出嫁的路上,羞涩的让全世界只剩下她的心跳和呼吸。
夜是如此宁静,而自己的心却无法平静,自己的爱,可以释放了,无怨无悔。
自孟冠棠走后,北木兮睁开了眼,下了床,其实在他的怀抱里自己就已经醒了,只是不知道如何面对而已。
北木兮环顾四周,真是豪华,连瑾姨住的地方也不及这里的一半,衣国当真富有到这个地步?
北木兮来到案桌旁,看着桌上的文房四宝,第一次有了想要写点什么的冲动。
她摊开宣纸,取来砚研磨,却发现砚竟然是红色,研磨后变成了黑色,顿时明白,原来是雪砚。雪砚是长期埋在积雪下的方砚,可是雪砚是红色磨出来却是黑色,听哥哥说雪砚是由雪狐用血养成的,所以会是红色,可是兑水后就会变成黑色,用雪砚写的字遇水不化,可以保存千年。
雪砚想来珍贵,连自己的相府中也没有,没想到衣国的一个小小寝宫中就会有雪砚,看来衣国的实力不是一般的强盛。
北木兮如是想到,慢慢用水晕开,看着墨一点一点的晕开,就像舒展的云朵,跳着一种舞蹈,从未见过,却摄人心魄。
一切准备好了之后,北木兮坐在案桌上,一时间忘了要写什么,不断的提笔又放下,最后,当卜易的竹筏顺流而下的场面出现在脑海中时,北木兮喟叹一声,不知不觉中早已下笔。
去年扶锄种花,
春风不理人情故,
徒留清愁。
今年花开风不知,
知时花落成残红,
海棠风情,
独为思君瘦。
北木兮看着宣纸上不知不觉间写下的小诗,百感交集,“独为思君瘦啊。”瘦的岂止是海棠啊,岂止是海棠。
放下宣纸,北木兮慢慢走到床边,月亮又上来了,没有风,静如水,亦凉如水,月光倾泻,为世间万物披上一层清霜,多少人都睡了,北木兮感叹着。
正待睡时窗外飘进一阵琴声,悠悠扬扬,却也像涓涓细流,延绵温柔,听着听着,心莫名的安静下来,北木兮闭上眼,感受着旋律如清风拂过花面般拂过自己的心口,“心无物欲”,是的,心无物欲,就是这首曲子中的意境,闻曲识人,想必抚琴着也是一位心无物欲的人。北木兮凭着心口的好奇,沿着琴音搜寻着琴音的源头。
琴音越来越清晰,刚刚还如隔帘看花,现在觉得似乎只在眼前了,北木兮来到了一个小庭院,入鼻的是一阵夜来香的香味,还有微微檀香的味道,北木兮好生奇怪,这一日自己在衣国所见的花基本上都是栀子花,怎么这里竟嗅不到半点栀子花的味道?
透着月光,北木兮看到一个黑影在花丛边的亭子上抚琴。微微的夜风吹落些许花朵,又消失不见,忽然,琴声戛然而止,弹琴人看向北木兮的方向。就着月光看得不真切,但北木兮可以肯定那是一位的女子,那女子看着北木兮,良久后站起身来朝北木兮走来。
直到女子走到眼前,北木兮才终于可以看清她的长相,眉如远山,眼波荡漾,琼鼻贝齿,也是一等一的美人胚子,可是,北木兮注意到她带着头巾,原来是没有头发的,北木兮皱着眉头,看来是落发为尼的了。
而在北木兮打量女子的时候,抚琴人也在打量着北木兮,抚琴人看了好久,掐指一算,面露惊讶之色,再看北木兮,眼中已带了一份惊恐。
只见抚琴人忽然扣住北木兮的手腕,将她拉到亭中,将北木兮摁在凳子上,拿起一旁的剪刀,一口念念有词,“妖孽,妖孽······”抓起北木兮的头发就欲剪下。
而一脸疑惑的北木兮终于明白过来,打掉她的手,站起来面对着她,口气中有着些许的愤怒,“你想干什么?”而抚琴人向前,看着北木兮说道:“三千烦恼丝,剪了是好的,不然你的下辈子都别想安宁。”
感觉到眼前人的奇怪,北木兮只当她是一个疯子,也不回她,径自离开。
而抚琴人看着北木兮的背影,喃喃自语:“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不入空门,最后有得苦了,一入空门,四大皆空。”
北木兮回到了房间却止不住想着刚才那个女人的话,越发觉得奇怪了,真是怪人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