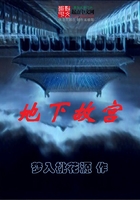因为只是体力透支和胃肠呼吸道的一些感染,我和胡子五天就出院了,二叔因为肋骨断了两根,虽然不用手术,但还得在医院修养一段时间。
我和胡子出院的第二天,二叔就让胡子、老张、大壮还有华子他们回东北了,二叔公司那边还有有很多事情,老张他们三人也没必要在这里耗着。
至于胡子,本来是想留在这里陪我和二叔的,不过这次探险铁柱不幸遇难了,二叔让胡子跟老张他们回公司领100万先给铁柱家里送去。二叔的公司与探险者签订的合同上意外补偿也只有30万,况且铁柱还不是二叔公司的探险者。虽然铁柱的死二叔没有表现的那么伤心,但从这点上可以看出,二叔是真的拿铁柱当朋友,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毕竟人已经死了,这些钱只是希望能够给铁柱的家人一些帮助吧。
我留下来也只是陪陪二叔,根本就不用我照顾,这些天我基本都是晚上去一趟医院,其他时间基本都在外面闲逛。
虽然这次罗布泊探险前后加起来不过一个月的时间,但当我从医院中出来走在人车涌动大街上的一刻,就仿佛过去了几年一样。
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城市!
这几天我一直想好好的大吃一顿,结果几天来几乎找遍了库尔勒的大小饭店,只找到了两家东北菜馆,而且做的味道一点也不对,看来只能回到东北这个愿望才能实现了。
除了吃,这几天我不是住在酒店就是洗浴中心,当然其中有很多娱乐服务,本来我对这些没那么大兴趣,但可能是这次的经历太过凶险压抑了,我只是想单纯地发泄一下,结果不到十天,卡里的二十万就被我发泄没了,最后只能先让公司财务打钱过来。
对此二叔也没说什么,因为本身二叔平时就是这样生活的,而且二叔应该也知道我这是在发泄,不但没反对还鼓励了我两次。
这样过了半个月,二叔出院了。
因为库尔勒没有直飞沈阳的航班,我和二叔先转车去了乌鲁木齐,第二天下午到的沈阳,我和二叔也没在沈阳停,直接打车回了阜新。
回到家,躺在床上,看着熟悉的一切,回想起这次罗布泊的经历,就好像做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梦,这一觉我睡的很香,很踏实。
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我没去公司也没出门,自己做了点吃的,看了两场球赛,看来是在库尔勒那半个月身体消耗太大了,有点虚,球赛还没看完我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这样在家缓了两天,身体状态终于调节过来了,第三天去公司,发现胡子来公司上班了,而且还是和我一样的副经理职位。
我在公司也没什么事,闲晃了一上午就和胡子去外面吃饭了,本来想叫着二叔,不过这趟出去了这么久,公司攒下来的事情很多,二叔忙的一塌糊涂,我和胡子去二叔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打着,我们也就没叫他。
一家特色鱼店,我和胡子点了俩菜,要了两瓶酒。
之前也没机会闲聊,这时候我才知道,胡子和铁柱都是当兵出身,退伍之后也没什么稳定的工作,给别人干过几年保镖,胡子左脸上的刀疤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后来那个老板出事了,当时他们恰巧接触到了探险这个行业,因为挣的不比保镖少,危险系数也相对低些,他们就干起了探险。
他们和二叔是八年前认识的,当时是在神农架探险,他们在深林中迷路了,然后悲剧地遇到了几只凶残的野猪,当时他们本身就受了伤根本跑不了,绝望的时候恰巧二叔救了他们,所以他们才对二叔那么感激。
后来他们几乎一直都跟着二叔,不过两年前犯了点事(我问胡子什么事他没说),他们跑国外去待了两年,刚回来不久还没来得及到公司入职,就和二叔前往罗布泊了,没想这一去,铁柱就再也回不来了。
聊胡子和铁柱的过去,聊这次探险的经历,情感所致,这顿饭和胡子吃到了下午三点多,都喝多了,我没回公司车也没开,迷迷糊糊就直接打车回家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凌晨三点多,头疼的厉害,去客厅倒了杯水,结果迷迷糊糊的没找准杯子口,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水都倒在了杯子旁边的电话上。
“谁打电话了?”擦了擦电话,我发现有两个未接电话。
点开一看,二叔打来的,看了下时间,23:44,23:45。
“二叔这么晚打电话干什么?”我有些奇怪,现在快四点了,不过二叔可能有事,我还是给他回一个。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没电了?”我又打二叔的另一个电话。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什么情况?”我有些纳闷。
因为事情很多,无论是哪个电话,二叔从来都不会关机的,就算偶尔出现意外,最多也就一个电话没电了,而这种情况我也只遇见过一次。
两个电话我又都打了一遍,还是都关机。
“奇怪了。”我打二叔家里的座机,结果打了两遍都没人接。
二叔半夜连着给我打了两个电话,这本就少见,现在他两个电话又都罕见地打不通,家里座机也没人接,到底什么情况?
我放下手机喝了口水,这时候手机退回到主页面,我发现有一条未读信息。
“应该是二叔的。”我点开短信。
信息的确是二叔发来的,可是信息的内容却让我摸不着头脑。
短信只有五个字:“我去趟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