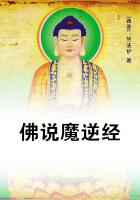“哥?”阮桃花迷茫仰面,她没有握住哥哥的手,而是转眸望吕梁风。
长空晚霞丝染,穿着新郎喜袍的吕梁风,片片融化入暖红色的背景。他的站姿依然熟悉、挺拔,只需静静远观,阮桃花原本不安的心境便会踏实下来。
“桃花,别看了,快上车。”肖兆离忧虑紧眉,催促妹妹,“我们不回卧柳客栈,哥带你离开东京城。”
离开?昨日才进京,今日就离开?
阮桃花不甘心。预知大神分明让她“看到”了……同一背景下,吕梁风怀里抱的女孩儿,如果不是吕绣芸,那该是她啊!可是,吕梁风的宝石眸子一与她相接,很快错开,好像阮桃花的身上附着什么可怖的妖魔鬼怪。
吕相不舍地放开吕梁风的手。燕十牵来天枢马儿,吕梁风伸手接过缰绳。
“少爷,是桃花姑娘?”燕十提醒,殊不知吕梁风比他早瞧见。
阮桃花转眼站到吕梁风的面前,她手按马鞍、阻止他上马,调整呼吸问:“喂,你为什么假装看不见我?”
燕十嗅出不同寻常的语气,扭头走远两步。吕梁风瞥一眼树下的肖兆离,说:“桃花姑娘,他在等你。”
“吕、梁、风!你为什么不敢正眼看我?”阮桃花一语道破。
吕梁风顺从地抬眸,眸色灰冷、不带神彩。阮桃花真的生气了。为了他,她擅自闯入皇城相府,他却没有半句感谢之言想对她说?
是啊。吕梁风的话,已经全部在早上和她说得清楚明白。阮桃花自以为的“失身”是场严重的误会,她甚至不是他的亲表妹。二人之间,再没有一星半点的联系。阮桃花瞬间变成第二个吕绣芸,不,想想她比吕绣芸更可悲……
她受够了,她阮桃花又不是没人要!挑剔又高傲的男子,她才不稀罕哩。
阮桃花另一手拽低吕梁风的袍肩,升高音调、细眸冒火:“吕梁风,你以为我很喜欢你?你少得意了!我告诉你,我不喜欢你,我讨厌你!全世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
“……”吕梁风垂眸,舌尖轻舔苦涩的上唇。
阮桃花控制不住地鼻头一酸,逞强挤出一个笑容:“呵,我哥要带我出城去。我们再也不用见面了,真好。”
阮桃花突然放手,吕梁风宽厚的胸膛稍向后弹。
吕梁风深眸定住,瞧她拔脚跑远。对情况一知半解的燕十,凑近他道:“少爷,相府能放你出来,多亏了桃花姑娘。我是不知她做了什么,但她一个女孩儿家,肯定很辛苦。你瞧,桃花姑娘的手臂都划破了……”
吕梁风才觉,阮桃花手落过的马鞍侧面,粘着一道浅浅的新鲜血迹。
吕梁风三指捻血,“燕十。”
“少爷?”
“我们回卧柳客栈。”
话音未落,吕梁风人已在马上。他压低身子,白马如云飞梭。燕十回头看,阮桃花窝在肖兆离的怀里,肖兆离安慰妹妹。
西边日落、东边月出,日月没有明确的界线而各奔东西。燕十叹气,上马追赶。
“燕十,你记得我提过的‘命数’么?”
“少爷,那是假道士骗钱的花招啊!”
“不,那是真的。相府的千金因为喜欢我,才剃度出家……”
“少爷!你赶走桃花姑娘是不愿牵累她?”
“燕十,我若真孤独终老……”
“少爷,燕十会陪着你的!”
.
吕梁风回到卧柳客栈,不吃不睡,换了身衣服,吩咐燕十将吕家在京城的一十七家店铺的账本通通送去他的屋子。
“少爷。”
“……”
“少爷?”
“你走吧,我在看账目。”
门外,燕十摸须侧立。天已黑透,吕家的店铺大多关门了。燕十翻出几本商团随行的旧账册,硬着头皮送了进去。而一向做事严谨的吕梁风,好像没发现?
傍晚街市车马如龙、灯火如昼,一日内,与京城相府有关的第二条传言不胫而走。
“相府家的千金连夜剃度出家啦!”
“哦,确有此事?”
“那还有假?她死也不进洞房,命府中丫鬟剪了自己的长发。啧,正值芳华,可惜、可惜啊!”
“会不会,入门女婿的‘那’方面有问题?”
“嗯,我听说新郎官在家乡风流的很,怕是染上了什么花柳病……”
“——呸,你胡说!”
阮桃花跳起来,怒指邻桌:“你们两个大男人,躲在暗地里,捕风捉影地传闲话,也不知道害臊吗?”
“嘿,老子爱讲谁就讲谁,你个小丫头片子讨打?”
“谁敢打我妹妹?”
肖兆离甩着步子,黑脸走过来。对方两人一见他腰间闪亮的方刃大刀,不再吭声,闷头吃饭。
肖兆离脚跨条凳坐下,用上身挡住对桌两人,面向闷闷不乐的妹妹笑道:“桃花,我们先在这儿住一晚,明早上路。你说,去青州找邓伯伯,好不好?”
“不好。”
阮桃花手持木筷,上唇托起筷子尖。肖兆离点了一桌的饭菜,阮桃花没有食欲。
“那哥带你应天府,你不是喜欢吃那儿的马家烧鸡吗?”
“不去。”阮桃花摇头回答。
肖兆离外表不羁,但他劝解妹妹时的语气很温柔。他是宠溺阮桃花的,毋庸置疑。
“桃花,告诉哥哥,你想去哪儿?”
“我……我想回家。”
“不行。”肖兆离的否决坚定得诡异。
“为什么不行?”阮桃花红了眼睛,委屈抬头。她上京来,是为了见吕梁风。现在吕梁风和她没关系了,她只想回到她熟悉的地方。她想回、家。
“唉,真的不行。”出于和阮母同样的担忧,肖兆离不打算告诉妹妹真相。莫说临安府,整个江南对阮桃花都不安全!
“哥……我是不是长得丑,惹人讨厌?”
“怎么会?我们桃花最美了,谁见了都会喜欢。”
“你骗人!”阮桃花没忍住,一颗泪珠划下脸蛋,掉入桌上的赭石漆花饭碗里。
肖兆离敏感察觉,事情和吕梁风有关。他宽心笑笑,岔开话题:“咳,瞧我笨的,明天去哪儿,我来‘看一看’不就知道了?”
一道淡蓝银线由上至下平切眼底,肖兆离半垂面。阮桃花抹去一颗泪。
“不、这不可能……”肖兆离的两道长眉颤动紧拧,眼眸里再翻一道光页。阮桃花疑惑看哥哥的额头泛起冲动的血色。肖兆离深深埋面,双眸接连闪烁一片荧荧光浪!
“哥!”阮桃花小心以掌虚遮他的眼,悄声问,“你在干嘛?”
肖兆离浑身力量一松,他对视阮桃花,目光复杂。在他的预知里,没有妹妹!他只看见,明早自己一人上路,身边何处都找不到妹妹的影子。
妹妹不在他的身边,那么,是去找吕梁风了?
转瞬,肖兆离的失落,被强烈的抗争意志所取代。阮桃花眼望情绪反常的哥哥,不禁紧张咽下口水。
“哥,你看到了什么?”
“桃花,你还在想着吕梁风、想要回去找他,对不对?”
吕梁风不是小黑,他比小黑危险许多。妹妹体质特殊,不该接触那种男人。为什么,桃花就是不肯乖乖听他的话,明早陪他一起出京呢?
“桃花。”肖兆离狠下决心,明知他没有能力更改预知之事,为了妹妹,他必需试上一试。肖兆离暗暗咬齿,凸出下颚线条刚毅,他正色对阮桃花道:“吕梁风……”
.
汴京城。高栈卧柳,灯烛寂静。
吕梁风独身凭窗,屈一腿坐,另一腿长长伸展于虎窗前的黄木重榻上。
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坐着,一动不动地挨过两个时辰。他很想起身忙事,比如,翻翻两个时辰前燕十送来的账目。可他思绪乱得很,没法集中精力。
吕梁风右手三指捻得快要磨出茧子来,可仿佛仍能触到沾染指尖的薄薄血迹。
他忘不了,那血迹,是桃花姑娘的。
吕梁风不喜欢肖兆离。君子行事,需堂正磊落。肖兆离委托他去劝桃花姑娘对他死心,这手段,未免不够君子。
吕梁风看得出,肖兆离喜欢阮桃花。说白了,二人并不是亲兄妹,肖兆离当然可以喜欢她。肖兆离为人不够君子,但吕梁风不得不承认,肖兆离的手段很高明。想到阮桃花以后有肖兆离做依靠,他能够放心了。
烛窗影淡,他什么累活儿没做,心神却很是疲惫。吕梁风斜靠窗,慢慢阖上眼睑。
“……你少得意了,我讨厌你!全世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
耳畔回响女孩儿铿锵有力的宣称,吕梁风吸气张眸。半晌,他笑了。二十一年来,吕梁风头次听人说:不喜欢他、讨厌他……呵,吕梁风边笑,边心里酸涩。
“砰、砰。”
无风窗动,有人从外撬开吕梁风背后的窗子!
吕梁风阒然起身,零星窗纸和着碎木杆掉落一榻。
“嘁哩喀喳——空通——哎唷!”
一人翻滚而入。
路琅琅小手捂两眼道:“花花,你非要在他面前丢脸么?”
“冤枉啊,我以为他睡着了。”
阮桃花哪知卧柳客栈的墙牖如此结实?她本想趁吕梁风睡觉,悄悄进来装鬼吓唬他。唉,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阮桃花迅速拾掇衣裙,努腰坐起,双手歇膝斜坐,尽可能摆出端庄可人的模样。
“你……”吕梁风轻捏她手肘,“你先起来。”
“你要赶我走?”阮桃花不敢相信。她进屋的方式确实不太高雅,可他一见面,就要赶她走?
“不。”吕梁风轻舔上唇,灰蓝眸子斜扫满榻的碎屑问,“你坐着,不疼吗?”
阮桃花一愣。疼,活像坐在沙砾堆上,股部扎扎的……阮桃花没来及反应,已被吕梁风握着双肩提起来。吕梁风温厚的手掌在她臂上停留了极其微妙的半秒,隔着衣衫,阮桃花直觉肌肤发烫。哎,她很没出息吧?
刚说了讨厌他的话,又莫名其妙地出现。无论什么年代,喜欢一个人,可真吃亏。
阮桃花忐忑压下受伤的自尊心,越过吕梁风宽挺的肩膀,瞥一眼案上油灯,又瞥一眼折得整齐的床榻。
“你没睡觉,在看帐目?”
“噢。”吕梁风模糊回应。二人的距离很近,这次,他没有闪躲。
吕梁风看阮桃花明眸乱转,惴惴脸庞与她身后撕开一道口子的窗阑,搭配得分外诙谐。吕梁风忍俊不禁:“唔。”
吕梁风从没想过阮桃花会回来,他以为肖兆离不会让妹妹回来找他。
“桃花姑娘,你为什么回来呢?”吕梁风的问题状似随口,绝非随口。
“咳。”阮桃花垂眼看脚尖,既而抬目笑说,“我来取回我的行囊。”
“可你住在隔壁的院子。”
“我记性不好嘛。”
“可你没走门,你爬了窗子。
“天太黑,我看错了嘛。”
“可我屋里点着灯。”吕梁风自始至终态度平和,语气比阮桃花更无辜几分。
“……”阮桃花哑口无言,吕梁风,他是故意的?
果然,烛光侧映吕梁风俊朗如玉的面容,他沉默直视阮桃花,面上笑意若有若无。三更夜深,若有一名女子闯进一名男子的窗子,任那男子再君子坦荡,也能洞察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