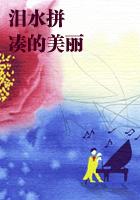中学的第一天,我看见好多不认识的面孔,第一节课都是自我介绍。英语老师是位很英俊的男人,再加上会说一口我们听不懂的语言,更是让女生崇拜至极。我的同桌是一个很腼腆的小男孩,看样子不太爱说话,我笑哈哈的和他打招呼“嗨,你好,我叫小米,”他听完愣愣的看我,“叫我小米,好记。”
我和漫琦每天一起回家,她是我的小学同学,只是她那时总是独来独往,不怎么和大家玩。我是个三分热的人,不一会就能和许多同学打成一片。漫琦家就住我家后边的加工大院,在我一次次找话题攀谈后,她终于能笑着和我聊好一会儿。
金柯,是我中学交的第一位新朋友,超爱搞逗的她总会有笑不完的怪事。于是放学,我、金柯、漫琦一起回家,金柯和我打闹的时候,漫琦是那样安静的看着我俩笑。金柯到小路岔口就向另一个方向走了,如果我俩有没聊完的事,总是会在小路口逗留一会,这时漫琦就靠着电线杆,像个思考者一样,不知道在深思什么。
小贝是金柯的小学同学,她一直是骑自行车上学的,后来就和我们一起步颠儿,小贝的好友荣希也来了,荣希和我们不是一个班的。人多了,回家的时间就长了,偶尔我们几个会坐在操场的墙头上没边没界的聊。有一次由于大家争论哪种超能力好而很晚回家,妈黑桑着个脸不说话,弟就躲得远远的,他才上小学二年级,所以我有很大的资本在他跟前吹牛。妈发怒不会持续很久,睡一觉就没事了,第二天早晨照样有牛奶和香喷喷的蛋炒饭等着我们。
西木再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他问了我近况,问了我好多问题,一开始我都不怎么想去回答,因为生气。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生气,直到冲他喊出八个月没联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他一直就在那里,并没有因为升学考试而忽略掉,没有因为萧萧的离去而忘掉,没有因为交了新朋友而不再想念。
“我没考上中学,”他的声音略带沙哑。
“那你······”
“我爸送我来了军校,”
“军校?”
我们聊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电话都捂热了,我想如果再不挂的话,电话肯定会烧掉。末了,他说会给我写信,这样会比较方便表达。
我班有个很疯的丫头,她总会出奇怪的点子,并真的去实践,我们都叫她“人来疯”。她说男的想法都很变,小雨把这说法告诉了大田,于是展开了一场关于“男女谁更变”的争论。我感觉西木变了,他的声音变了,想法也变了,他没有和我聊飞机的事,我说我好久没看见飞机的尾气了,他只是默不作声。
圣诞节的时候,我收到了西木的贺卡,还有一封米黄色的信,字迹工整有力。他让我要一直快乐,他说他把石头丢了,因为这绝食三天。石头,我的石头放哪了呢?我绞尽脑汁的想,还是没有任何线索。后来终于在床底的箱子里找到,上边刻着的名字依然清晰,我笑着摸着石头,想起那天西木兴高采烈的表情。
西木说要送我一个东西,作为彼此的见证物,万一有天失散了,就拿这个出来默念,他就会像超人一样嗖一下出现在我面前。可是,当我发现等了好久的东西竟然是一块石头的时候,我好失望,他说那可是他用小刀一下一下刻上去的。无论怎样,我还是勉强收了,他相当高兴,挠着头呵呵的傻笑。
元旦,班里要组织活动,大家三三两两的组一起出了个节目,我、小贝、金柯唱了一首当时火遍大街小巷的《心太弱》,这么悲伤的一首歌,金柯竟笑得唱不下去,退场了。
中学第一场考试,我砸了,几乎是倒数十几名左右,班里六十多人,那些经常逃课的人为什么没有掉在我后面?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这几个无耻的人肯定搞小动作了,但无论怎样,我还是倒数,妈妈只会从名次表的后边看到我。当天,妈妈哭了,她是一个人躲卧室里哭的,想到这个寒假肯定不会好过到哪去,我悄悄的打电话给二哥。
“真的假的?好啊,我和姑姑说,”二哥爽快的答应了我的请求。
二哥在族人里,是公认好学指数非常高的,妈妈喜欢他,舅舅也喜欢他。没想到哥哥的一句话,妈妈就答应我假期去二哥家了。
二哥家离我家有两个小时的车程,临走的时候,妈妈给我带了半书包的书和几件换的衣服。
“去那听舅舅的话,别老贪玩,不会的问你二哥······”妈妈不止一遍的强调要我学习,要我听话,就像唐三藏念经一样。
以为离开家就可以高枕无忧的睡觉、玩耍了,但我却算错了。第一天还好,二哥带我和毛子去爬山,毛子是二哥的堂妹,就在二哥家后边住着。第二天,二哥就开始实实在在的教学了,规定的时间写作业,规定的时间睡觉,规定的时间吃饭,只有黄昏一小会可以找毛子玩,真是出了“虎窝”又入“狼穴”,这样说有点夸张,但足以代表我当时绝望的心情。
腊月初八,我决定要回家,大舅说吃了腊八粥再回。当天下午,我坐上回家的车,想到回家能比较自在,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年根里的日子乐坏了我们,也忙坏了大人们。妈妈一边忙着经营部子,一边忙着收拾家,还要做年货,简直恨不得能有七十二般变化,我和弟弟只能打下手,弟弟经常变成添乱者。
虎子长得越来越粗,越来越壮,吼声粗犷有力,吓得路人都不敢在我家门口逗留。我和妈妈擦玻璃的时候,虎子就扒着窗台,两条后退支地的站着,看我们有说有笑,它就着急的拍能够着的玻璃,于是,无论我们怎样努力,那几块玻璃总是沾满它梅花样的脚印。遇到好天气,妈妈就会整天收拾屋子,晒地毯,扫屋顶。有人要买东西就会给妈妈打电话,我就骑着我的小赛车飞一样的冲到部子里,东西在哪,多少钱,妈妈都会提前告诉我。
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家里收拾的亮亮堂堂,我看着妈妈做年货。有糖浇的马蹄酥,有炸甜圈,有卤猪肉、鸡肉、牛肉。妈妈会做各种花样的大馒头,堪称一绝,还有各式各样的面点,做食物要持续一个多星期,到最后,西房里大盆小盆,大坛子小坛子都是吃的。
过年的那天晚上,礼炮噼噼啪啪的就没消停过,妈妈放了几个响麻就开始煮饺子吃了。
西木的电话是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打来的。
“新年快乐!”西木沉沉的声音,我不知道该不该回应一个,可是隔了好久就问了一句“吃饭没?”
“嗯,正准备吃,你呢?”
“正吃饺子呢!”
“好啊,替我也多吃几个,今年我家貌似不是吃饺子啊,哈······”他竟然笑了,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后来西木和我聊了许多,我都记不起来了,唯一有印象的是让我错过了半场过年晚会。
年后的一段时间很是无聊,我去找漫琦,她家的大猫生小猫了,一窝毛球。我俩坐在她家的屋顶上看人们扭秧歌,冻得直发抖。之后我俩又去找金柯,她家没人,很是扫兴。
过了正月十五,假期就进入了倒计时中。
很快就开了学,大家许久没见,彼此聊得热火朝天。金柯去姥姥家过年了,她说是坐了两天的火车去的,她说那里有海。当大家各个都还沉浸在过年的欢乐中,我却还得重温“倒数”的阴影,班主任让最后十几名叫家长,听到这话,我的心都凉了。
晚上,昏黄的灯光下,妈正在缝补我们的旧衣裳,眼看就要到睡的点了,我凑到妈跟前,“妈······”
“啥事?”
“老师明天让您去,”这句憋了整晚的话终于没卡磕的说出去了,好半天妈都不做声,末了,她说:“知道了,早点去睡吧!”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的宣判,只是记得第二天一整天都过得很是揪心与漫长。妈说老师也没说什么,就是让我好好学习,原来是这样子,老套的话嘛,早知道是这样,我也不必虚惊一场。我妈当然希望我好好学,我也很认真的学,只是有时候贪玩了一点。
金柯考得不太理想,但至少在我前边,她说她妈妈都对她失望了,我俩共同感慨世界的不公。夕阳西下,即使抱怨一整天的学习苦闷,依然还得装作在昏黄灯下认真学习的样子给妈看,只有我自己知道演练本下藏着的是新出的《水浒漫画》,苦苦思索时心里装的都是西木的脸庞,而屋子的另一头坐着欣然织毛衣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