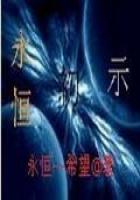五月的漳水淌着浊黄的水,静静地向入海口流去。几百里的漳水,一入从山间流到平原,到了龙溪子城边,虽流得很急,却很平静。
台风刚过两天,上游还不断漂下零星的枯枝,顺着水流,无声地向入海口移动。
正值正午,阳光压制着除蝉虫之外的一切,大地万物也如江水一般,静默无声。
漳水北岸临着的是子城,土筑泥墙,既不高大,也不壮丽,只是这个时代华夏大地上普通的一座小城罢了,城外有个小码头,却无一船一桨,城外更是看不到半个人影。
漳水以南,是大片收割完的水田,金黄的稻禾扎成圆锥状,零乱地立在田间……方圆几百里,除了子城,大多覆着盛夏的绿,将房屋掩盖其中,竟难寻到一个人影。
稻田往西,便是大片墨色浓烟般的树林,从四周向中心的圆山收拢,愈到山脚,林木越盛,骄阳之下,静谧如画,连分散着蹲在林间灌木杂草中的十几个人也一动不动。
“啪!”地一声,少年摊开手掌,掌间是滩指尖大小的鲜血和一只扁了的花脚山蚊,反着头顶密叶间透过的斑驳阳光,一红一黑,让少年有些眩目。
“张文!你不要命了!”几步之外传来一声低吼,声音压得很低,却难掩说话人的愤怒。周边或蹲或伏的几个人也都投来愤怒的目光,但他们都保持静止不动,连喘息都缓慢得难以察觉。
少年抹了把流上淌下的汗,憨笑道:“黑牛实在对不住,我……”
话未说完,便听到数十步开外一阵哼哼,接着便是沙沙的枝叶抖动,林鸟乍飞了起来。
被少年称作黑牛的,狠地一下站了起来,手中拿着把三叉,喊道:“起来!准备!”
少年愣住了,他分明听到黑牛叫喊的时候林里传来的哼哼声已转变成了嘶嚎,这种嘶嚎他听过,邻村杀猪的时候,被捆住的猪便是这样叫的……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手里拿着家伙,不过拿着铁三叉的只有黑牛一个,其他人都是手是黑竹杆子,前端削尖过火,竟也都反着油光。
嘶嚎很快从一声,变成了一片,夹杂着的是一片沙沙乱响和低沉的轰鸣,那是野猪群冲锋的声音!
林子很密,杂木、灌木、杂草和藤蔓交错着,但所有人都将枪头对准了眼前的野猪道——一条野猪群平时过路在密林**出来的隧道。
嘶嚎声越来越近,直到地面都微微颤动的时候,张文这才醒悟过来,慌张地抓起卧在身边的竹枪,一下蹿了起来。但已经太晚了,跑在最前头的是一头巨大的野猪,它已经冲到他跟前,猪鬃飞扬,尺余长的獠牙从嘴里伸了出来,下巴还淌着粘糊糊的口水……
张文愣住了,这是他第一次跟着村人进山打猎,这样的阵仗他又怎么可能见过?出于本能,他将竹枪刺了出去,没想到野猪只是一甩头,便把竹枪拨开了,依旧直冲向他……
黑牛也急了,眼见着野猪就要拱到张文,就这野猪的个头,拱一下不死也要去半条命,情急之下,他挥动了铁三叉,丈长的三叉直直向张文刺去,三叉尖穿过张文后背的衣服,竟没伤到半点皮肉!又是一拨,张文便向后飞了起来,掉到七八尺高的藤蔓顶上。
黑牛一个跨步,借着挑走张文的那股子势,向前一个正蹬,正好踹中野猪的脖子,五百余斤的野猪居然被他一脚蹬倒!
惯性中倒下的野猪只在地上翻了一翻,便又起来了,直直向黑牛冲来。
黑牛慌忙闪到一边,一个突刺,脚下不稳没使上力气,只在野猪身上留了三道浅浅的血痕。野猪没有停下,依旧向前冲去,黑牛还来不及开口,它已经拱倒了一个青年。青年刚刺倒了一只猪崽,没来得及防备,他又长得精瘦,一下被拱了起来,重重摔在地上,一动不动。
“三德子!”黑牛吼了一声,持叉冲了上去,却不顾倒在地上的三德子,只是飞了一般地追上那头野猪,突地一叉出去,铁三叉直直没入野猪后门……
“我没事!”三德子从地上一下蹦了起来,拔起油黑竹枪,在黑牛惊诧的目光中,将竹枪从野猪后门推入,丈长的竹枪竟没入大半,竟狠狠暴了野猪的菊花!
“上树!”黑牛吼了一声,也不管平常被自己当成宝贝的三叉了,一个纵身跳起,上了树。
其他人只到吼声,也都丢了手中的战斗,没命地爬上了离自己最近的大树。
远远近近,二十来只野猪组成的群体,在密林里横冲直撞,个别身上还插着折断了的竹枪,血淌得到处都是。
被走了后门的野猪正是这群野猪的领头,在群体中它的个头最大,也最凶猛,入体之痛让它狂性全发,身后拖着竹枪和三叉,在野林子里横冲直撞,对树上的人却是不管不顾。几只没来得及躲闪的母猪小猪便被它拱得一身上血,纷纷逃窜。
野猪头领先是绕圈圈,但身后的竹枪木棍一碰到边上的树木,便疼得它越发疯狂,过了一会儿,竟然一冲直直地撞向一株大树,倒在地上哼哼。众人看去,下面几十丈内的灌木杂草居然被又推又踏地移平了!血更是流得到处都是。
大野猪倒地,它治下的小的们除了几只被拱死倒地的,其它全不见了踪影。林子里一下安静下来,只听到断断续续地哼唧声。树上的众人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准备再观察一下就下树去收拾今天的所得。
“啊!蛇!”树冠藤蔓中,张文一声惨叫,便直直掉了下来,一条手指粗细的竹叶青依旧咬在臂上不肯放开。他刚要站起来,原本倒在十丈开外红了眼的野猪已冲到跟前,用生命力的最后一次暴发,又将他送上了七八尺高的冠顶藤蔓网中……
***************************
一座破落的小院,张文被放在院子中间的长木桌上,脸色发黑,四肢浮肿,一动不动。周边站着一圈乡民,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郎中翻了翻张文的肿胀不堪的眼睑,又检查了渗出清血的口鼻和咬伤处,长长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
人群中为首的是一位五十出头的老人,连忙问道:“沈大夫,怎么样?这孩子……”
沈郎中摇了摇头:“难……看天命吧,我也束手无策了,只能开些消炎去癀的药,撑得过撑不过都是造化……你们……早些料理后事吧……唉!”
说完从药箱里取了些配好的药递给老人。老人将诊金付了,他便慌然离去。也不能怪这朗中不尽职,古时中国,医师的技术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名气,治好的病越是疑难,名气便越能提升,而相反的,如果治过的人死掉的越多,那就越说明这个医师技术很有问题……百姓平时所接触的基本上都是些名气平平医术平平的医师,那么他们所能打听的关于这个医师技术水平的信息,便是“无事故医疗比例”,而不是遇到什么不治之症……
朗中跑得快,其实也就是为了挽住自己那么一点点名气,众人也都表示理解,并没有出言相留。
“呕……”案桌上的张文一阵抽搐,续而便是呕吐,吐出来的却只是白沫,腥臭难耐。
众人围着一阵叹息,却无可奈何,这样的事情连着周边几个村子,每年总要发生几次。除了无奈,他们也只能希望伤者走得不那么痛苦,也祈祷自家人不要发生这样的悲剧。
“唉!天公啊,救救这孩子,别让张家绝了后呐!”老人抬头喊了一声,头顶的万里晴空似乎感应到了他的呼唤,竟然凭空一道炸雷响起。附:漳水、九龙江都是同一条河流,也就是现代的九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