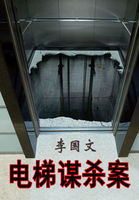干我们这行的,一下地就等于把脑袋栓子裤腰带上,走过的路,走过的地方总会习惯性的做上标记,,地宫复杂也算为自己留条后路,在宁夏的那回我就是跟在一只蜡笔小新后面才逃出生天,到现在我对蜡笔小新都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可现在墙角的那个图案却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怎么回事,老四,这是条死路。”我没搭话,把那个埋在一半埋在墙里的五角星只给她看。
“你确定,这是你画的?”阿红的声音微微发颤。
“我不知道,但是不是我画的都不重要。”
“怎么说?”
“现在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那个五角星是我十五年前画的,现在它一半在墙里就证明,有人或什么力量把路给封死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之前那些标记我们依旧能找到,因为他的目的并不是毁掉我的标记,而是把路封死,至于盖住我的标记那纯属巧合。第二种情况,”我顿了顿,看了看阿红,接着道:“那种力量是针对我们的,所有的标记都被改过了,我们从踏入甬道的第一脚起,就中了它的圈套,他把我们引到这儿肯定有什么目的,唯一可以庆幸的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似乎并不想或者不能害我们。因为如果他真的有智慧去改标记的话我们就在甬道里死几百次了。但不管那种情况我们都不能再往前走了。”说完我只觉得头皮发麻,问伙计要了根烟蹲在墙角抽。
“那怎么办,已经退不出去了,要是迟了就只有死。”
我猛抽几口,把烟屁股往墙上一摁,道:“雷管儿,过来看看。”
雷管儿姓徐,大号叫什么没人知道,但玩儿炸药在我们这行可是响当当的。古塔来客没少费我银子,这人看着忠厚老实,实际上油的很。之所以雇他来,并不是因为相信他,只是够了解他。我知道他想要什么,忌惮什么。我给他他想要的,又有他所忌惮的,这样他才不至于反我。暗地里我们互相防备,明面上他照样称我一声“铁爷”,我道他一声:“兄弟”,一旦下了地这种关系才是最牢靠的。生死攸关的事儿谁说的准。老爷子有句话说的对:你信任的人才有伤害你的机会。
“铁爷,成了。不过这墙的厚度我估摸不准,得炸一次。”
不管怎么说雷管儿这小子干活你挑不出刺来,不到二十分钟就把炸药引线都倒腾好了。
“我不懂这个,辛苦兄弟你了。”我笑着递给他支烟。
他笑道:“瞧您说的,兄弟我也只会干这个。”
雷管儿的收益没的说,爆炸范围控制的很小,没有对甬道造成太大的损坏,麻烦的是这堵墙似乎很厚,一次没炸透。
正当我跟雷管儿合计着要不要再炸一次,阿红冲了过来,脸色在苍白的道:“小杰……小杰不见了!”
听后不由得攥紧了拳头,问:“冷大当家呢?”
“也没见,现在你还有心思管他,怎么办,回去找找吧。”
“不用,那个八级智障走了我反倒省心。”
“**的开什么玩笑,小姐还是个孩子,虽然傻了点儿讨人嫌了点儿,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冷炎跟他一起,有什么好担心的。凭他的手段,小杰就算是想上吊都找不到绳。他带走小杰应该另有目的,小姐最多苦逼一点,不会有性命之忧。”我他娘的怎么把这个瘟神给忘了,看来我还是小看冷炎了,他知道的事恐怕不比我们少,我也是犯浑,小看他就是造孽啊!”再说,去哪儿救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小杰,而是我们。”我指了指那堵墙说。
“铁爷你看,顶上有盗洞。”一个伙计对我道。
果然头顶上有个圆形盗洞,估计原来被人用砖墙当着,这一爆炸把掩着的砖给炸了下来。
“上去看看。”
一个伙计踩着雷管麻利的翻入洞中,过了半支烟的功夫他下来对我道:“铁爷,盗洞大概有四米长,上面是一个甬道,我看了看跟这没啥差别。”
“那你上去,放根绳,我们上。”
“你确定要我们要走这条路?”阿红问。
“我们什么时候说过假话,这是直觉。”我没告诉阿红的是我闻到了那股味道-----那股充满甜香的危险的味道。
果然,我在甬道的墙角,找到了另外半颗五角星图案。
“怎么回事,空点错位了吗?”阿红脸色很不好看的问。
要是空间错位就好了,这次的行动不会容易,至少不会比十五年前容易,我后悔了,早知道就去拜拜如来佛祖玉皇大帝那一家子了,说不定他们在打麻将聊八卦时突然发现又饿公共粉丝,一高兴就把我给救了。
“出发了。”我笑道,对阿红说。
接下来的路途相当乏善可陈,一样的甬道就是他娘的走不到头,唯一的变化是两边的砖墙变成了整幅的壁画,描绘的是一些生活狩猎的场景,从衣着和习惯来看不是汉人的东西,刻工也很粗糙,只是单纯的在石头上刻出线条组成图案,可我老觉得这壁画不吉利。不光是画,整面墙都让我不舒服。
可又找不出哪儿不对。
等等,让我看看。
原来的甬道是用砖砌的,这儿的墙壁则是一整块儿石头,妈的,总算让我找到哪儿不对了。
“老四,你来看。”暗红颤抖的转过我的头。
我顺着她的手电光看过去。瞬间悲伤的白毛儿都竖了起来。
一只滴血的眼球正死死的盯着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