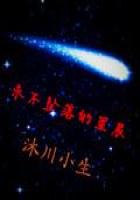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中没什么可怕的事,不知为何我出了一身冷汗。
醒来后我什么也不记得,只记得一个人、一句话。
梦中有位黑衣男子,像从水墨画中走出来一般,黑袍灰带,狭长眉眼如墨,翩翩迎风而立。
他一转身,回头轻笑:“你若觉得时候对了,便可来暖凉山找我。我嘛,还是很愿意成全别人的愿望的。”
我醒来以后,以为这是有神灵托梦,喜不自胜。只是不知那位公子姓甚名谁,身在何处。
我兴致勃勃地把这件事讲给云锦,云锦也颇感兴趣,说:“普天之下,愿这样助人为乐,莫不是传说中悬壶济世名扬四海的巫医谷凌白芷凌公子?”
“那你可知道凌白芷长什么样子?”
“我可没见过。”云锦笑笑:“据说面容清秀,眉目如画,年纪轻轻医术高明,刚刚继承了巫医谷神医水月无音的衣钵。”
“这……”天下之大,梦中其人,实在不能仅凭这些判断。我托着下巴,鼓起两边的腮帮,愁上眉梢。
云锦笑道:“云笔,同你说着玩的。梦里的哪能真做数呢?或许你梦见的是天上的神仙,午夜恰巧路过你家的,你也跟着去天上不成?”
我一想她说的也是,回家前还问了她一句:“你可知道凌公子所在的巫医谷,在什么地方?”
“这你都不知道?巫医谷呀,很远。在风都与雪国的交界处,暖凉山。有顽疾据说到那里没有医不好的,可是那又远、路又难走,有几个人能拖着顽疾走到那呢?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云锦抬手拂过我的头发,突然神情里顿了一顿。
我没注意那微小的细节,只听得她说“暖凉山”三个字,欣喜异常。本来是死的心,真是随之又活了过来,迫不及待想哪天拜会一下这位公子,也学一门医术的好手艺,回家有个谋职的行当。我才不想继承爹娘驿站的活计,日复一日,了无生趣的。
然而,福祸相依。我回家之后,推门迎上娘的笑脸,她身边是一位胖乎乎的婆婆,穿得很是花哨。胖婆婆脸上带着一种驾轻就熟的笑容,很令我觉得虚伪厌恶,但世间的事儿莫过如此,你越讨厌什么,什么往往越迎着你来。胖婆婆见我回来,还没等我娘开口,一步上前拉住我的手,说道:“好呀,这丫头好呀。文儿,姐姐给你保证,这桩亲定能结的成,你日后能享福了。”
娘难得笑得顺心,嘴里客套着:“还得请花姐在老爷前给多美言几句,这丫头,疯得很,性格像个小子。不过该会的肯定是不缺的,她爹惯着,读书读到现在,也算是知书达理的。”
我撑着没撂脸色,待着那婆婆走了,问我娘:“您这是干什么?”
我娘依旧是千年不变的端起茶杯,脸上一扫笑容,以往日的威压对我说:“做什么?你年岁也不小了,早日给说个人家。我和你爹在驿站做了一辈子,如今这镖局总镖头的公子,也科考回来,虽说早了点,可总镖头就这么一个儿子,娘还得是尽早为你谋划打算。”
我本想挑个良辰吉日跟爹娘说我的人生谋划呢,不过猜也猜得到,刚才那媒婆已经动身,于是我直截了当的对娘说:“娘,云笔自有打算。我想嫁给城中櫂月家……”话一出口便后悔,觉得底气实在是不足。
娘像听了个笑话:“你懂什么?那櫂月楼开在暮云村,能有什么前途?你嫁过去就知道,成日里盯着账本,看着丫鬟,凭你这马虎功夫?哪有当总镖头的媳妇轻松?再者说了,那櫂月同你年岁相当,要他娶亲,且不着急,我听都没听过有这么个意思,你自己跑来跟我讲,简直是笑话。”
我做梦也想不到娘能讲出这种话,事实上,给女孩说人家本该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惜爹叫我读了这么些年书,许是本该女子无才便是德,我生生是生了反骨。“我不要,除了櫂月哥哥,云笔谁也不要!”我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取出彩綾凌空一抖,抽得红木桌边一张椅子呯地倒地。
娘见的人多了,对我冷冷一笑:“张云笔,这事儿说来也由不得你,你满意不满意,你花姨娘再过几日说成了,你爹便去同总镖头喝那一杯结亲酒,日子定了你等着便是。跟你一年到头不见的师傅学些混账玩意儿,也学不出个名堂。玩玩的事儿,劝你还是别当真格的。你那彩綾是能卖艺混口饭吃,还是真能出师独步江湖了?成天不见你练,倒只会拿出来玩儿。我跟你爹,没个家底的,在驿站做了一辈子,别昏了脑袋不经事了。”
娘见我眼泪不住的流,也觉得话似乎是说重了些,话锋一转,道:“你说你要跟櫂月,平日里东家长西家短,我可真倒没听说过,倒是云锦她娘跟櫂月娘总是走得很近的,人家櫂月娘也希望能在暮云村做大的,跟咱这些镇上混的结亲家也没什么看头。张云笔你别怪娘的话不好听,以后你便明白了。”
我夺门而出,月亮刚升起,天色已经晚了。刚从云锦家出来,眼下要是再回去,古怪得紧,还是找櫂月哥哥的好。我心下不知为何,非常的慌乱。只能不停安慰自己最近总是慌乱,过阵子自然就好了。一路上磕磕绊绊,我又拿出彩綾来借一丝微光。令我欣慰的是,练了一阵借风借水,虽然无所成,但彩綾居然已经有了颜色的变化,是很浅很浅的蓝色。我认为终于离师傅又近了一步,我所修习的也并不是娘嘴中的街边杂耍。可惜这样的事还没来得及说,就被娘的话泼了一头一脸的冷水。此刻只想找到櫂月哥哥,平时矜持着面儿,从来和他都好好的,这次说什么也要扶着他大哭一场,跟他仔细说说我的心底事。
眼见着还有几步就到櫂月楼,我忍不住加快了脚步,一拐角就能看着那迎客的微光了——之间三步之外,一个熟悉身影正不紧不慢地走去。定睛一看,不是云锦又是谁?
云锦还是刚刚见我的一袭衣裙,走得很慢,似乎犹豫不决。但她还是走到了櫂月楼下,我们常来此处玩耍,驾轻就熟的,她却抬头望了望那块题着櫂月楼三个大字的牌匾,生怕走错了似的。
她一直没说话,我却也似乎明白了什么,然而,我却一直不肯信。我对自己说,听了娘太多世故的话,我也跟着把人想的太坏了罢。不可能的,我的心思,云锦是知道的。
然而。
门口迎客的丫头鸳鸯,脆生生地招呼了一句:“云锦姑娘,你可来了,我们少爷候了多时,还以为路上出什么岔子了呢。”
我远远站在门口,看云锦移步进去,櫂月哥哥,我的櫂月哥哥,迎着她站在门厅里笑,笑的比那日月亮下更加好看。他就如同云锦时常对我做的那样,轻轻抬手抚了云锦的发鬓,插上一朵茶花,眼睛里满含情意。而云锦呢,我记得不久之前,我还拖着她跟她说我要如何如何,她还含笑笑我冒失。我看着云锦,她面色平淡,没有笑,也没有拒绝,而是抬手在櫂月脸上摘去什么,盈盈一侧身坐下了。
那一刻,似乎是有师傅的冰刃,无色、无声、无形,生生插进了我心口里。
世上还要待我如何?我同时失去了娘,云锦和櫂月。
我一侧身跑开了,敲开了妖卷卷的大门。卷卷揉着眼睛,看我眼睛泪如泉涌,吓得顷刻醒了。他问:“云笔?你是在哭?”我只说:“你有多少银票,全部借我。”
他定定看我片刻,转身回去,拿了三张一百两和一把碎银塞给我,我说:“你哪里来这么多?”卷卷说:“偷我娘的。”
我也没客气,说了句:“妖卷卷,你信我,我这辈子欠你的,肯定能还给你。你记着,今晚你也没见过我,日后……日后我一定……”说着我跪下了。
卷卷趁我膝盖没落地一把把我拉起来,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看着我。我死死地看了他一眼,转身跑了。我自己没有任何积蓄,此刻我心如死灰,也不需有任何留恋。我向着商山直奔而去,拼了命在晚风和寒鸦啼叫中爬上山顶。好在不高,爹娘每日翻过此处去驿站也没那么久。我跌跌撞撞,差点滚下了山坡,终于第一次以一个十分狼狈的姿态踏进了安城桃源镇,我四处打听着,在夜色黑得快不见五指之前找到了一家小驿站。这和爹娘就职的地方不同,此处没有固定的时间和线路,只要你开个价钱,恰好还有车,就可以走。
我先用碎银在旁边买了张饼,接着我问其中一个人:“最远可以去哪里?”
那人长得瘦小结识,一口黄牙,他看了我一眼,不屑地说:“只要老板钱够,西天都去的哟。小妮儿这夜里胡跑什么,快快回家去罢,莫要添乱。”
我拿出一百两,问他:“暖凉山,你去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