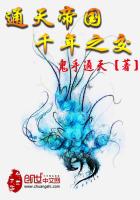宋朝末年,蒙古铁骑入侵中原,少林寺高僧玄慈禅师为汉人宗教派系奔走,得以说动蒙古成吉思汗宽待汉人宗教,元朝统一天下后,诸代元帝皆谨遵祖上圣谕,不得侵犯汉人佛道等寺院,道观。而玄慈大师更是得天下教统一职,视为汉人教宗大幸。
而少林寺更因此名声大振,河南行省一代平民百姓无不是佛教信徒,香火延绵鼎盛。
少室山下,刘家村。
“大师,真的太感谢您了,”一位手杵着拐杖的老人颤音说道:“要不您的良药,我家阿牛还不知何时能够醒过来。”
近些年北方涝灾又开始频繁,黄河两岸百姓皆深受其害,此时正值秋收之际,元廷却调拨河南行省汉人百姓修筑河道,生怕两漕盐场被黄河泛滥之水冲垮。却不知百姓的命根子田地日日在雨水中浸泡,已经颗粒无收。
刘家村能拿起锄头的都被官府押走修筑河道去了,老人的独子阿牛便在其列,后来阿牛在黄河沿岸日夜赶工修筑河道,心中却一直挂念着家里那六亩田地,急火攻心,加上连日下雨,身中寒气,两相逆气相冲导致阿牛在河堤倒地不起。被同村的给抬了回来。
要不是路过刘家村的少林寺师徒二人,老丈家唯一的独子阿牛恐怕就撑不过今晚了。
老丈家徒四壁,根本无长物报答这师徒二人,说着就要下跪行礼。
却被身前一位少年伸手扶起。
少年笑道:“老爷爷莫要行礼了,这方圆数十里地谁不知道我师父最愿意为村民排忧解难。”
这位少年面色还显稚嫩,看起来年纪应该不大。身着打着补丁的灰色袍服,脚踏着一双藏青色的麻布鞋。好像因为衣服过于肥大少年腰间还扎了个黑色的布带,显得身材更加瘦弱,后背还挂着一个快压垮他身躯的竹篮,头上光亮俨然是一位面容清秀的小和尚。
“阿弥陀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贫僧只是举手之劳,何以得老丈如此大礼。”
说话之人身形相较小和尚更是消瘦,一身黄袍有如挂在了竹竿上,估计此人便是小和尚口中的师父了。
别看黄衣和尚身形消瘦,说话却是中气十足,双手合十更是隐有宝相庄严之色。
拄拐老人还想多说几句,身边小和尚又先开口了。
“师父,太阳都快落山了,咱们再不快点赶回去,山门就要关了。”小和尚说话很着急,好似想赶快离开这一般。
黄衣和尚转过头瞪了一眼小和尚。
“至真,把你竹篓里面藏的苞米拿出来。”
“这.........”被唤作至真的小和尚一听师父的话,瞬间变了脸色,小声道:“师父,我......”
老丈人一听赶忙解释道:“大师,莫要怪罪小师傅啊,这棒苞米是老头子看小师傅饿的肚子直叫才给他的。区区一棒玉米而已,给这位小师傅吃了吧,他也饿了一天了。”
“阿弥陀佛,”黄衣和尚摇了摇头,看向屋檐外的大雨,轻声道:“此时又正值秋收之际,本来正应该抢收粮食,可皆因连日大雨导致黄河之水泛滥,朝廷生怕涝灾影响盐场收成,居然一己私欲让千万百姓离开家园修筑那所谓的两漕盐场。可气那万千亩庄稼眼睁睁烂在地里被雨水冲走。怎可知这粮食才是民心之根本!!”
“老丈,这一棒苞米放在往日自当没什么,如今正是缺粮之时,我少林寺子弟万万不可收此等贵重之物!”
说罢,黄衣僧人喝到:“至真,快把粮食还给老丈!”
小和尚至真年少不懂事,怎知一棒玉米还有这等重要,赶忙把玉米从篮子中拿了出来,郑重的还到老丈手中。
自感羞愧,跪在黄衣和尚跟前,低头认错。
黄衣僧人一声叹息,没再做他言,只是抬手从至真背着的竹篮中拿出一柄纸伞,踏入了雨帘中,小和尚一看师父已经出门,忙向老丈告辞,快步跟了出去,师徒二人的身影逐渐被雨水阻挡。
“我这是在哪儿?,水,我要水,”屋内传出了一阵虚弱的声音。
还站在房檐向张望远处的老丈一听,急忙拄着拐杖快步走进屋内,边走边哭喊道:“我的儿啊,我的儿啊,你终于醒了,吓死爹了。”
屋内床上之人便是身中寒气的阿牛,他已经恢复了神智,但因身体虚弱,只能倚靠在床头,此时他一脸疲惫,看着走进屋内的老人问道:“爹,我不是在盐场修筑河道吗,怎么回来了。”
“儿啊,你身中寒毒,要不是少林寺高僧正巧路过咱村出手相救,你早就一命呜呼了。”
阿牛一听,亦是一脸后怕。
老人继续道:“趁着这几日修养,官差不会再来强抓你去赶工,咱家快把那点粮食收回来,好给少林寺送点过去。也算是尽咱们的一点香火心意。”
阿牛深感为然,点头称是。
此时外面依然大雨滂沱,出村的路上隐隐有人影浮动。
正是从刘家村出来的师徒二人,山道泥泞不堪,加上暴雨倾泄狂风不止,纸伞早就被刮烂,两人僧袍都被浇透,脚上的布鞋也被泥巴弄的面目全非,但师徒二人面色却很平常,好似这种情景经常遇到一般。
出村后,至真就一直跟在师父后面,
至真从小在少林寺长大,性格踏实本分,小小年纪就负担起了师父和师祖的生活起居,从未惹过二老生气。
今日黄衣僧人发怒,让他的心中七上八下的。
此时他思量着怎么开口求父原谅,
正想着事,手脚就迟钝了几分,往前踏步的左脚一下踩空了山路上被雨水冲刷的碎石头,身体瞬间失去重心向山路一旁的深沟栽去。
眼看就要被深沟暴雨泥沙冲走,一只大手抓起他的僧衣领子,把他拽了回来。
至真瘫坐在石头上,脸上也不知是汗、是雨水还是泪。
黄衣僧人此时亦是一身狼狈。
至真望着师父低着头小声道:“师父,徒儿再也不敢了,请师父回寺责罚,不要再生徒儿的气。”隐隐约约已经带着哭腔。
看着徒儿低头认错的样子,想到这么些年在他身上所受的苦难,师父坚石般的心有了一丝松动。
至真从小被黄衣僧人带大,自己徒儿的秉性,他最清楚。虽然至真年仅十岁,但却十分懂事,要不然也不会毫无怨言的跟随他下山修行,有时甚至不能吃饱饭,还要忍受着风吹雨淋之苦。毕竟他也只是个孩子,想到此处,黄衣僧人轻声回道:“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说罢就拿起至真弄倒的竹篓,将还没有冲走的包裹收了起来,起身赶路。
至真一听,师父这是不生他的气了,赶忙擦干脸上的泪水,整理下身上的衣服,一瘸一拐的跟了过去。
“师父,竹篓给徒儿来背吧。”
黄衣僧人摇了摇头,道:”“大雨寒气慎重,莫要多言,抓紧赶路。”
“知道了,师父”至真开心应道。
通往少室山泥泞的山道上,一黄一蓝,一高一矮两个身影在雨中影影绰绰。逐渐消失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