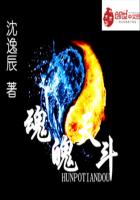“老伍,听说你昨天一天衰得很啊,被堂主臭骂了一顿,呵呵。跟大家伙说道说道,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少收了一个村子的份额?”
“甭提了,踢到硬点子,两个客卿去都栽了。”
“唬人的吧,昨天在外郊镇场子的是易客卿和那个最狠的狼千蜂,能在一个破村子里栽到哪去,堂主都不信你这套。”
“你们是不在现场,不知道……唉。”
伍六齿叹了一口气,他昨天栽了跟头也算是大开眼界了,可惜两位客卿自然不会闲着没事给他帮腔作证,他们的身份可比堂主还高呢。所以他和兄弟们的说辞只被堂主当成交不齐份额的借口,狠狠克扣了一些月响。堂主当然不会认为近百个人都在撒谎,只是有些事情太大条,他一时无措,找个由头,发泄下怒火而已。
先前说话的人见伍六齿吃瘪的表情,一笑而过,把话锋一转。
“我刚听说堂主今早天还没亮的时候就收到一封信,信上说上头的大人物今晚要齐聚观月楼开大会哩,大手笔啊,观月楼顶上三层全给包了。”
“扯吧你,堂主的信你还能看到,吹的什么牛皮。”
“啧啧,不瞒你们说,收信的丫鬟翠儿这几天刚成了我的人,谁叫哥们我膀大腰粗,丫鬟姐姐一看就知道咱有一副好肾!”
众人又是一番起哄,只有伍六齿面上的笑容有些欠奉,他是此间唯一知道上层开会原因的人。
接下来渔鼓帮一伙聊的就是一些不堪入耳的少年禁事,萧山疾耸耸肩,知道再听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转头对怜生说道:“看来渔鼓帮内部出了什么事,竟然包了观月楼顶三层,去的人应该不少,张如庆肯定也在其中。”
渔鼓帮内部出的大事当然是罗晋明死了,萧山疾知道这一点,不过宋先生没有开口,他也不会和怜生主动提起这些事。
怜生将碗里剩下的豆浆一口饮尽,说道:“这么说今晚去观月楼蹲着,铁定能逮到张如庆了?”
萧山疾心想这是什么用词,怎么好像张如庆是一只铁定会撞在柱子上的兔子。不过这么说也不算错,他略沉吟一会儿,就点头道:“应该可行。”
怜生嗯了一声,说道:“那咱们先回去吧,找先生说说。”
两人抬脚刚想走,就被卖豆浆的小贩叫住,小贩也是个暴脾气,不客气地说道:“喝碗豆浆都不给钱?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萧山疾摸了摸全身,真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有点尴尬。
再看一穷二白的怜生,这家伙连衣服都是借方掌柜的,被方艾裁了点才勉强穿得合身,此时的怜生摸都懒得摸了,直接拿求助的眼神可怜巴巴地望着他。
萧山疾瞥了眼后边渔鼓帮那伙人……幸好没引起注意,于是对怜生说道:“你先走,我自有办法。”
……
在渔鼓帮一伙的谈话中得到线索,找到了一条明路的怜生此时心情颇好,他沿着来路返回,想快点回到客栈里和先生讨论一下。
晨光大亮,街上行人也渐渐增多,怜生挠了挠头,发现竟有些忘了来时的路。说起来这才是他到流韵城的第二天,没人带路,行人一多的情况下实在有些迷糊。怜生挠头间,打算随便找人问一下韵来客栈,忽然眼角瞥过一抹白色的身影。
怜生定睛一看,发现是一只白马,再细看时,那白马身宽体胖,富态十足,可不就是连绝公子的那匹大白马吗。
怜生好奇心大盛,可能是因为后山岭的那只胖虎的关系,他本就对胖乎乎的事物兴趣十足,或者说颇有好感。他慢慢走近那只在小巷中缓缓踱步的白马,四下望去,并没有发现那个连绝公子的惊艳身影。
“嘿!”怜生忽然从后方跳出,问道:“你的主人呢。”
和动物说话,若有旁人看见了,肯定会觉得这个少年脑袋有问题,其实这只是怜生在后山岭和那些猎物打交道时留下的习惯,他当然无法和动物交流,只是觉得这样很有意思。
大白马被骤然吓了一跳,马嘴微张,瞳孔放大,一只蹄子举在半空一时没有落下,它似是有极好的教养,没有失声叫出来,只是回过神后用马眼瞪了下怜生,又抬步向前走去。怜生看它的步态优雅,像个公主,和三合镇那些大户的马匹完全不同,十分有趣。
再看那圆鼓鼓的肚子,随着步子波浪一般起伏……
怜生眨了眨眼睛,情不自禁就伸手摸去。
真的,好软。
这下白马彻底惊了,四蹄被吓得同时一跃,惊恐地看了几眼怜生,然后嘶吁一声,像一个被非礼的姑娘,飞也似地往前逃去。
“咦,是只雌的。”怜生的手还伸着,保持着猥亵的姿势,他有些尴尬地自言自语道:“我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
流韵城的高墙足有十余丈,除了城中的第一高楼观月楼,所有城墙都远远高过其余的建筑,使得那些建筑仿佛都是沙盘中的模型。城墙中只有南段这一处稍矮,大概是南边不出几里就是沧澜江,俱是无法铺陈攻城器械的码头和滩地的缘故,南墙看起来并不像是城防,而像一处观江的高台。
连绝正准备登台,抬眼发现正在城中散步的大白马惊恐地逃了过来,一点也没有平时的优雅。
他准备登阶的步子又放下,几步走到还在惊魂未定的白马身边,摸摸它的马鬃,柔声说道:“大白,怎么如此慌张。”
他此时的声音空灵清澈,竟是像一个女子。
俗名大白的大白马驹在主人手心蹭了蹭,平复着心情,忽然听到后边有动静,吓得赶紧藏到主人的身后去。连绝有些单薄的身影挡不住大白的庞大身躯,大白就将马首低下,不敢看追来的人,看起来有些滑稽。
怜生不知时刻在想些什么东西的脑袋决定要追上那只大白马道歉,当然,他可不管后者能不能听得懂。
他全速奔行的速度很快,竟没有比白马慢上多少。然而他一直追到南墙的时候,首先看见的却是连绝充满敌意的眼神,那只优雅的大白马此时正缩在主人身后,低垂着脑袋。
“呃,连绝……公子。”
“你想对大白干什么!”此时的连绝满脸怒容,用清朗的声音喝道。
怜生十分尴尬地笑着,甚至有了几分畏惧,他的脚不由自觉地退后了一步,说道:“我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它。”
连绝眯眼又睁眼,一手缓缓抬起,遥指怜生,说道:“这样?那你也过来给我碰一下。”
看着连绝抬起的白皙如玉的手,怜生忽然想起那根轻轻戳在他的背上却把他痛个半死的纤细手指,赶忙摇了摇头。
“你过来!”
“不过去。”
“难道你还要我过去?”
“你可以过来,呃……试试。”
“没人敢这样对我说话!”
两人隔着十步之距,却都不想往前一步,一个出于自卫,一个出于自矜。
连绝只觉得面上有火烧,似乎每次遇到这个小子都能轻易让自己动气,乱了心境,他深深吸气,平静说道:“那好,你可以不过来。”
怜生刚想松口气,忽然一股罡风扑面而至,仿佛沧澜江无匹的溯浪,将自己掀了好几个跟头,吃了一嘴灰尘。他再起身时,风劲还不止,身后牌楼招牌旌旗啪啪作响,如奏乐鼓。
连绝面上有了几分得意,收了出掌动作,目光和表情又回复到平淡如水的模样:“再有下次,决不轻饶。”
怜生自知理亏,哭丧着脸,吐了口尘土,嚷嚷应道:“知道啦。”他拍拍满是尘土的可笑脸颊,又将屁股上的灰尘拍打干净,有些幽怨地看了一眼白马,再看了一眼连绝,作揖告辞。
等到怜生的身影完全消失在巷子里,连绝才“噗嗤”一声笑出来,揉揉身后白马的马鬃,说道:“就是一个蠢笨得有些可爱的小子,有什么好怕的。”
大白发出“呜呜”的声音,摇尾乞怜,十分委屈。
……
怜生本就不熟悉回去的路,又跟着大白马跑了一圈,似乎愈发的离客栈远了,他只好边问人边找路,竟不知不觉把半个城池都逛熟悉了。
太阳日上三竿,再下三竿,等怜生回到韵来客栈,已是日头西斜。
客栈里还是没什么生意,掌柜和宋毅已经索性在大厅里摆桌喝开了,见到怜生回来,面上两片醉红的宋毅有些责怪:“你这一天都跑去哪里了。”
怜生耸肩,没有回答,反问道:“小萧回来了吗。”
萧山疾此时恰巧捧着一碗素面从后厅出来,看到怜生,笑道:“我还问先生说要不要出去找你呢,他倒是一点都不关心,说你自己折腾够了会回来。”
怜生问他:“小萧,你后来怎么付钱的?”
萧山疾说道:“付什么钱,那小贩态度那么差,我直接撒腿跑了。”他吸了一口面条,解释说:“我让你先走是怕你拉不下脸做这事,我玄……我学艺的时候老师常说一开始行走江湖最可以不要的就是脸皮。”
怜生的表情有些羞红,他当时想的其实就是逃账,只是怕小萧面上过不去才没有说出来,他在三合镇没跟宋毅学到多少东西,但逃账的本事却学的直追不落。
夜幕降临,烟火升起,又是一个狂欢的夜晚。
怜生用过晚餐,又去看了眼还是没能睡着的侠奇正,喂了后者一碗稀粥,嘱咐他好好休息,叹气着出了房门。
大厅里宋毅醉倒在桌子上,面有醉红,许是几日未开酒瘾,和掌柜的喝上了头,没收住。而方掌柜被方艾扶着往后院去了,萧山疾还在后厅里收拾着碗筷酒瓶。
这大半日已摸清观月楼位置的怜生轻轻打开客栈的大门,出门,再转身悄悄合上。
“怜生……这么晚了呃……要去哪啊。”宋毅突然含糊地说道,分不清是醉话还是梦话。
怜生一惊,再看先生已喝成的这副模样,还是决定不说出来,随便应道:“出去玩玩。”
“早去早回……”醉态百露的宋毅挥了挥手,“不要玩的太疯哦……”
……
连绝站在南墙高台,背倚沧澜江,看着城中升起的第一束烟火,神情有些闲适。
几名黑甲士单膝跪在他身后,看不清面貌,只是肃声说着。
“巡捕房已经出动,二十一处窝点俱在运营,戌时突入必能找到违律铁证。”
“烽火营,神弓营随时待命,公子令下便可入城。”
连绝摇了摇头:“戌时入城即可,不需我再观察。说是十万帮众,其实不过一班乌合之辈,在正规军士面前不堪一击,即使发生冲突,最多十几条人命之后他们就会投降。”
他遥望城中,说道:“精兵入城只是给巡捕房底气,让他们放心办事,所谓流韵城的第一大帮在我大周铁军面前哪敢有什么异动……其实若不是我赶时间,根本无须调动这两营士兵。”
等了一会,连绝突然说道:“侍五、侍六呢?”
身后黑甲士回答道:“五卫、六卫还在徐大人处,一些案情似乎有了新的情况。”
连绝点点头,将卫士散了,独自赏着烟火。
或是烟花盛景不夜天,或是满城灯火照无眠,连绝忽然有了一股面对盛世的豪情,他想起了那个已经过世的伯公曾写下一首颂词,就是写得沧澜江。
兴之所至,她清朗的声音颂道:
雪山饮净渠,家国水流年。
不知沧澜奔东海,此去经何山?
孤欲乘浪追觅,又惧千礁暗屿,湍处逆水难。
将夜起惊涛,不休语长江!
执此舵,扬此帆,过峡关。岂能有恨,沧笙踏歌无须还!
人皆朝生暮死,水难奔流复返,自古无西川。
豪气未尽,背后却有两道身影落下。
那两黑甲士落地后方才察觉似是打扰了主人的雅兴,迅速跪地,不敢言语。
连绝面上有红晕掠过,他深深吸了口气,说道:“有事便说。”
“……是,徐大人一天一夜未眠,将关于渔鼓帮的所有案情重复翻查,发现了一些新的迹象。诸如帮中犯事的客卿,堂主之前的身份,以及帮内贩人一事等等,都与城中另一处府地有着若有若无的关联。”
“……何地。”
“威灵府。”
连绝沉默着,慢慢地,他的眼中有些看不进那些烟火,看不进那些灯笼,看不进满城繁荣。
焰火升空的嘶鸣声听起来有些刺耳,凄凄的夜风也莫名多了几分躁意。
他终于念出那颂词的最后两句:“惟愿水长流,入海忘阑珊。”
即使是不懂诗词歌赋的两侍也觉得公子念词的语气有了些变化。
连绝摇摇头,厌倦地骂了一句。
“这座肮脏的城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