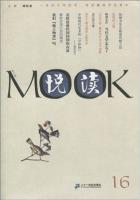燕来楼,是圣都最着名的**花坊,没有之一。和所有同类的高级“服务行业”一样,这个地方从来都不缺乏一掷千金的豪客。香车宝马自然是数不胜数,但是像林默兄弟二人这样施施然走路过来的还真是少见。
当然,也不乏那些有才华的寒门子弟受到邀请为那些名妓作词作赋而后春风一度。但是这两个家伙……小的那个就不说了,八`九岁的年纪就算是想要干点什么也做不成啊。而那个年长一些的,虽说相貌英俊,但是这个肤色……
事实上林勋也算是一个翩翩美男子,但是由于在边关长期风吹日晒,早就将皮肤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虽说这在林默眼中才是真正帅气的男人应该有的肤色,但是在其他人眼里就很是不同了。
“二位请留步。”虽说已经在心中将这两个家伙定位成了穷光蛋,但是作为门迎的两个青衣小帽的侍从依旧态度良好。“二位公子,且慢且慢。您二位可知这地方可是何处?”
“不就是燕来楼吗,莫不是以为我二人不认识字?”
“不敢不敢。小人只是想提醒一句,这燕来楼可不比一般的**会馆,里面的各位姐姐可以说各个是国色天香,但是这价格……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的。请两位公子三思。”
“老哥,你被人小看了。”林默哈哈笑道。虽说这个下人是在说自己二人是两个穷鬼,但是人家的态度良好,甚至是是在为自己着想,的确也挑不出什么毛病。而林勋闻言也是哈哈一笑,随手扔过一块的银子,也没看多少。那下人急忙接住,只感觉入手沉甸甸的,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块二十两的银子。虽说这燕来楼迎来送往的有钱人不少,但是这样大方的却也是不多。那青衣小帽心中责骂这两个家伙这么有钱还装作一副穷酸相,害的人险些误会,一边脸上陪着笑将一大一小两位公子迎了进去。
不得不说这燕来楼不愧是高级的**,所见所闻和林默所想象的完全不同。进了门,耳中首先听到的不是那些淫言秽语,而是悠扬的古琴声。虽说林默对此没什么研究,但是也听得出来这琴师必然是有些功夫的,要不然自己老哥也不会摇头晃脑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走了几步,便是大堂了。没有那些大红大紫,一切布置的分外清新素雅。在大堂的最前端,有着一个不算很大的舞台,轻纱缭绕之下,倒也有着几分薄雾迷蒙之感。林默点了点头,对这份布置很是满意。虽然比不上自己那个世界绚烂的舞台效果,但是在现在这个连纸张都没有发明出来的时代,能够有这样的创意已经只得赞扬了。
青衣小帽的侍从将林默两人引到了一个相对僻静又很靠前的座位上,随即几个打扮干净利落的侍者便上了一壶茶水,几样小点心。点心做的精致,上面的花纹栩栩如生。不得不说无论是哪个世界,国人在吃上面的造诣都是无人可及的。
“不知两位公子需不需要姑娘作陪啊?”
“暂时还不用,我兄弟二人……自有别的事情。”林勋笑着说道,搞得林默一阵迷茫。来**不就是干那个事的吗,难道还能到这里来赏风景?不过他倒是也没多话,只是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而那个青衣小帽眼睛一转,笑着说道:“原来公子是为了那镜心姑娘来的啊,怪不得。这镜心姑娘今日梳笼,想要拔得头筹的可不在少数,不过小人见这位公子您风度不凡,必将讨得镜心姑娘的欢心,做那入幕之宾。”
“多谢多谢。”林勋拱了拱手,也没怎么表示,搞得那青衣小帽一番想法也都落了空,只得悻悻地离开了。就着茶水,啃着桌上的点心,林默吃的倒也是分外开心,他这次只是来长见识的,若真要他做什么也是力不从心,只是老哥为什么……
悄悄地问了林勋一句,结果得到的答案让他很是无语。“你老哥现在口袋里面可没钱了。”
“啊?那你还给那个家伙那么多赏钱?”
“人活一口气吗。”林勋尴尬地说道:“要不,小弟你借我点钱?”
“我靠,有你这样的老哥吗?嫖`妓还要自己弟弟掏钱?你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喂喂,江湖救急啊。咱们可是亲兄弟啊。”
“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林默摆出一副“宁死不从”的架势,搞得自己的哥哥一阵苦笑。而在这时,邻座的一个年轻人施施然走了过来,对着林勋一抱拳:“小弟国子监岑敬仁,这位兄台看上去颇有些面生,不知兄台高姓大名,在国子监哪位先生门下?”
“哦,我不是国子监的学生,我是戍边军……”
“原来是一个丘八啊。”没等林勋说完,那个叫岑敬仁的年轻人立即换上了一副倨傲的姿态:“这燕来楼可是一处**雅地,尔等庸人还是速速退却了吧。”
“你这人,什么毛病?”林默斜了那个年轻人一眼大声说道;“你又凭什么说这地方不是我们能来的?”
“尔等这些无才无德,只知道杀人放火之辈,有什么资格来这种高雅的地方?”
“无才无德,你就是说我们没有文采喽?”
“正是。”岑敬仁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丝毫没有发现林默嘴角那一抹奸计得逞的笑容。
“你,也配和我谈文采?”
林默的话说的异常嚣张,鼻孔朝天的样子简直就是用自己来诠释“不屑一顾”这个词。岑敬仁闻言火冒三丈:“你这个黄口小儿,也知什么叫做文采?”
“我自然知道什么是文采,如果你不服,现在可以和我比试比试,现场赋诗一首。”
“比就比!题材你来定!”
林默心中笑的颇为得意,若是叫他与这个家伙玩什么奏对,楹联亦或是什么经史,林默是必败无疑。但是如果比赛作诗,哼哼,华夏几千年的文人墨客就是自己最大的后援,他自然是不怕的。想到这,他眼珠一转,坏笑道:“你这个叫岑……岑什么玩意的家伙,可敢与我比试,做那一首有关如厕的诗文?”
“什么!”岑敬仁一瞬间嘴巴张的老大:“如……如厕的诗文?这可,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