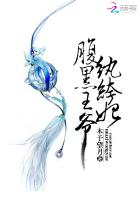白遽岚在朝中独揽大权多年,在宫里遍插耳目,任何风吹草动很快就能得知,这自然也包括昨晚在“曲梅亭”里发生的一切。
自他将文萱献给宁岱后,十六年间对她说的话,算起来也只有三次,那还是他跪拜谢恩之时。文萱的眼神每次都是既不避他,也不看他,仿佛他像空气一样存在。
他原本打算等宁岱一死,宁湮登基,就和文萱重修旧好再续前缘,但当他看到她对自己万年如一的冰冷态度,就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毕竟无论是谁遭遇文萱那样的命运,都不会再对利用自己的人产生什么幻想。
“可是就算她不会原谅我,她往后的生活也应该是看着儿子登上皇位,自己做个端庄稳重的皇太后,享受着臣子们的尊敬和贵妇们的艳羡,然后在几十年后一个雨夜安静离世,从此躺在山陵中与华贵璀璨的珠宝器皿永远相伴。”白遽岚这么想。
“可是现在竟然还有别人去扰乱她的生活!”白遽岚一想到卢南卿昨晚与文萱的亲密举动,就头痛欲裂,既是愤怒,更是嫉妒。
他刚认识文萱的时候,就听别人说起过她和卢南卿的往事。那时他虽有些吃醋,但毕竟文萱就在他身边,并且决心要和他共度一生。因此他渐渐地不再去想这件事情。
十年前卢南卿进京为神武军效力,白遽岚如临大敌,派手下跟踪监视了他很久,确认了他的真实来意后才放下心来。
谁料在这个节骨眼上,竟然发生了这件事。他都对文萱说了些什么?
白遽岚的密探担心被卢南卿发现,不敢靠得太近,因此听不到二人谈话,不然也不用他如此伤脑筋。
他边走边想,来到书房前,推门进去那一刻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人在自己的领地总会不自觉地将心中压抑的情绪释放到表面。
这时便听一个人笑道:“天底下居然还有能让白大人叹气的事,这回我可算是没白来。”
白遽岚一惊,抬头看去,赫然发现国子监祭酒张腾正坐在桌边,手里端着自己的茶杯,像是在悠闲的品茶。
他只好又叹了口气,进来后转身把门关好。他知道,如果有人能在不被觉察的情况下进入自己的书房,那么在这人面前,是谁也逃不掉的。
白遽岚冷冷道:“没想到祭酒大人还有这般身手。”他虽然素来心计万端,但也颇不喜欢别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因此不太想和张腾兜圈子。
张腾低下头,仔仔细细打量了自己一番,笑的声音更大了:“我这头大白肥蛆,哪里有什么身手,即便是白大人现在要宰了我,我也是毫无反抗之力啊。”
白遽岚也打量了他一番,忖道:“他平日倒真是个酒囊饭袋、毫无用处的模样。”
“你这府第,我虽从没来过,但它有几间房子,房上有几颗铆钉,铆钉是哪家打的,倒是粗略知道些。我要来,自然也有人带路,有人奉茶,只可惜茶是好茶,就是凉了点。”张腾说着,又喝了一口茶,然后眉头一皱,从嘴里抠出一片茶叶抹在袖子上。
白遽岚顿时面色如土。他没想到,张腾竟是一个隐藏的巨大威胁。
张腾的身世众人皆知。十七年前,他还是夜鸢城市井中的一个无赖,身形瘦小,终日无所事事,后来不知怎么被宁岱的妻子尹洛赏识,收同龄的他做了“干儿子”,宁岱自然就是他干爹了。宁岱登基称帝后,张腾虽不能成为“皇子”,但凭着这层关系,成了宁岱的亲信,当了国子监祭酒。别人都当他是个酒囊饭袋,没什么出息,他也乐得逍遥自在,不去计较。
哪知他竟是个隐藏的大人物。也不知他在暗地里做了多少事,如果真像他刚才所说,尚书令府中尽是他的亲信,那么这京城里,可真是没有能够瞒住他的秘密了。
能做到这些的,只有传说中的神秘组织“夜盏”了吧。白遽岚对夜盏知之甚少,只听闻它热衷于操纵天下局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世间一切人都可成为其棋子,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其卖命。
难道张腾竟是夜盏的人么?若果真如此,夜盏只怕早已在京城中经营多年,甚至现在的局势都是夜盏培植的结果,而自己那个“精妙绝伦”的计划,可能也在它的掌控中,被它了解和利用着。
白遽岚尽管一向以镇静自若著称,此时也止不住的冒冷汗。他越想越怕,索性闭上嘴一言不发。这才是目前最保险的方式。
张腾又喝了两口茶,看到白遽岚的脸青一阵白一阵,浑身微微颤抖,于是关切地问道:“白大人气色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也难怪,一顶绿帽子戴了十六年,换作是谁,也不会感到舒服的。”
白遽岚这才肯定地认为,张腾必是知道有关文萱和宁湮的秘密了。但他还是一言不发,因为张腾吐露出的信息还不够多。
双方一起沉默了一会儿,直到张腾快要把那壶茶喝完了。只见他拿起茶杯,对着窗户瞄准了一下,用一个夸张的姿势把它投掷了出去,口中还“嗖”地一下配了音。然后地面上传来了杯子碎裂的声音。
如果家丁们听到这样的动静还不赶来察看究竟,那他们不是死了,就是真如张腾所说,这里早已被外人控制了。
白遽岚相信是后者。因为张腾的举动意在告诉他这一点,也提醒他,躲躲闪闪是没用的,是时候谈谈“生意”了。
“不知祭酒大人光临寒舍,所为何事?”白遽岚开口了,把这么一句本该很有礼貌的话说的毫不温暖。
张腾又笑了:“白大人可真是磨叽。这句话若是早些问,我们就还能省下点时间。救命的事情,可分毫都耽搁不得。”
“救命?救谁的命?”白遽岚一脸“糊涂”。当你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时,装糊涂装到底,总没错。
张腾诧异道:“自然是救白大人的命。”
“救我?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救我?”
“犯了这么大的罪,任谁也不会活得好好的。”张腾很有耐心。他好像十分享受和别人耍嘴皮子。
“不知白某犯了什么罪,竟让祭酒大人如此担忧。”
“过不了多久,白大人的亲儿子宁湮就要登上皇位了。到时候白大人是当太上皇威风八面光宗耀祖呢,还是继续向自己的儿子三跪九叩,鞍前马后口呼万岁呢?真是个幸福的烦恼。”张腾说完,嘴里“啧啧”不断。
“祭酒大人,这等捕风捉影之事,你也说的出口。不怕我奏明皇上,将你千刀万剐么?”尽管张腾洞知事实,但白遽岚也不会那么轻易就认了。有时即使走进了死胡同,也还有翻墙逃走的希望的。
张腾也不气恼,接着说:“前两天我派人从绮绣城接来个老大夫。他老人家已经七十六岁了,记性已经差到忘了昨个早上吃的什么饭的地步了。不过他带来几十本账册,上面写着他所有病人的就诊记录,最早的在五十年前,最晚的是十天前。我就那么随手一翻,赫然发现皇后娘娘的名字就写在上面。等我看完名字后面的内容,我就愤怒了,这个老匹夫居然污蔑我们贤良淑德的皇后娘娘在沉域元年七月就怀孕了,谁都知道我们的宁湮太子是沉域二年五月出生的,这样算来岂不是在娘胎里十个月吗?我不知道你们正常人的情况,反正我和宁湮太子都是怀胎八月出生的,我一直引以为豪。现在这个老匹夫要剥夺我这份荣耀,着实可恨,岂有此理!我等下就把他交给皇上,把他五马分尸!”他说的义愤填膺,手舞足蹈,如果白遽岚是第一次遇见他,说不定就真以为他是个白痴了。
他是在讽刺羞辱自己。但白遽岚并不放在心上,现在他心里只有后悔:当初文萱只是告诉他她有了身孕,他却没有想到文萱是去看了大夫的。不然那个大夫岂能活到今日?
文萱断不会告诉张腾此事,而张腾竟仅凭文萱在绮绣城时已怀孕这一信息就找到了当时接诊她的大夫,他掌握的或者说他背后的力量不可谓不可怕。
白遽岚终于问道:“你们想要什么?”他知道如果张腾把人证物证都交给宁岱,那就一切尽毁,大势已去了。所以倒不如“敞开胸怀”聆听一下对方的需求,说不定会产生弥补的办法。
话说到这一步,就谈的差不多了。当对方主动问己方的要求时,说明他们已经做好了满足己方的准备。
于是张腾笑了:“我自然是非常乐意看到白大人大业达成,得偿心愿。我要的也很简单:宁湮登基后,宣布放弃江南,恢复‘卢国’灭亡前二十年的疆界,承认卢氏后人为帝。”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白遽岚还是大吃一惊。张腾所要求的卢国疆界,差不多占了整个宁朝版图的五分之二,人口占二分之一,赋税收入更是占了五分之三以上,若承认其独立,无异于在南方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敌手,再过三五十年,宁朝是否还能保有中原,也是个未知数。
但如果不答应这条件,等待白遽岚、文萱和宁湮的,怕就是身败名裂,身首异处,到那时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了。
更何况,胃口这么大,也正符合夜盏的名头。而且事关重大,对张腾来说是个漫天要价的良机,如果他要的少了,白遽岚反而会产生更多的怀疑。
“我答应你。”白遽岚说。
张腾伸了个懒腰,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抖落身上的茶叶,说:“那我就坐等白大人的杰作完成了。”
他走到门口,正要出去,突然又扭头说:“白大人准备怎么处置那个小插曲?”
“小插曲?”
“卢南卿和文萱。”
白遽岚心中又是一阵颤栗。他们果然什么都知道。他脑子一时混乱,索性说:“还请祭酒大人指点。”
张腾轻描淡写的说:“两天后,会有西北边关急报,西胡族和北夷族大军二十万人围攻朔风城,你奏请宁岱派卢南卿率京西四镇十万兵马增援。在他从夜鸢城去京西四镇的途中,派几十个好手把他杀了,问题就解决了。”
“他若是不去呢?”
“一是军令如山,他不得不去;二是,你忘了他父亲在朔风城的失败了么?他可是时刻记着的。”
白遽岚呆在原地,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这等计策,他平时也是能想出来的。但此时他震惊于张腾所说之周全。他们那些人,不但能获悉大小机密,还能捏造军国急报,真好似在下棋般,步步都算计好了。
自己如今受到他们挟制,往后会是什么下场呢?他们想要的东西必定远超过提出来的,但自己也只能任其宰割。真个似雄心壮志奋斗十数年,到头来发现是清秋大梦空一场。
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张腾已经走了。他急忙跑到窗子前,往下望去,发现张腾晃晃悠悠,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尚书令府。
无论是家丁还是卫兵,没有一个上来拦住他的。
白遽岚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栽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