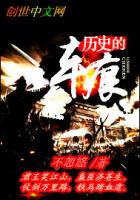令狐楚果然喝多了,但没有醉到人事不醒的地步,是红霞将他扶回了帐篷。
帐篷里亮着灯,令狐楚醉眼扫过,他看到了自己的行李,自己的长剑,弓,箭袋,地毯上的铺盖,还有角落里跪着一个少女。
“她是干吗的?”令狐楚半醉半醒地问。
“她是派来服侍你的女奴啊,这可是大首领的安排,”红霞将令狐楚放在了毯子上,吩咐女奴将炭火盆挪近,“你是我们的客人,还是大首领的好朋友,突厥人向来礼待朋友,会派自己最漂亮的女奴侍奉客人的。”
“我不需要,让她回去吧,我能照顾自己。”
“你最好到碎叶河边去照照自己,跟一只醉猫一样的,还照顾自己呢,好好歇息吧,我还要去看看大哥呢,他也喝了不少,”红霞的语气有些幽怨,然后吩咐那女奴,“阿奴,好好照顾令狐公子,”然后转身就要离开。
“等一下,”令狐楚出手迅速,一把抓住了红霞的手,红霞的心猛地一沉,他醉了,他要干什么?
“什么事,子羽兄?”红霞觉得自己的脸迅速地升温,呼吸开始急促起来。
“今天大家都在高兴,都在喝酒,都喝了不少酒,妹妹,别忘了大首领的大帐,这个时候更不能放松,去查验一下他的大帐侍卫,我下半夜去换你。”
“不用了,”红霞的呼吸均匀起来,心却一直沉了下去,“你一路鞍马劳顿,太累了,还是我带人去值守吧。”
红霞说完,挣开了令狐楚的手,大踏步地出帐去了。
望着红霞的背影,令狐楚觉得嘴巴里又干又涩,“难道我真的犯红?”一转脸,他看到了帐门口的小女奴,于是向她招手。
小女奴小心地起身过来,来到他面前又跪了下去,“公子有什么吩咐?”
“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奴婢叫阿奴,十六,公子您要喝点什么吗?”
令狐楚无力地点点头,阿蛮就赶紧又起身,为他倒了一碗羊奶,令狐楚几乎是一饮而尽。
“我要睡一会儿,三更时叫我,”令狐楚说完,将自己的长剑放在了身边,拉过毛皮被子,躺在了毯子上,外面的风声似乎大了起来。
“公子,让奴婢来服侍您吧?”小女奴显得很紧张,小心翼翼地试探,“这是大首领的吩咐,奴婢不敢违抗。”
“不用了,你就在那里,记得三更叫我,”令狐楚指了一下另一个角落,然后不再说话,不多时,沉闷的鼾声响起,另一个角落里,阿奴象一只小绵羊一样偎依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令狐楚猛地睁开了眼睛,帐篷里的火把还在燃烧着,他的手摸到到自己的剑,立即翻身坐了起来,角落里,阿奴已经睡着了。
“那个,”他努力回忆这个女孩的名字,哦,想起来了,“阿奴,阿奴,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阿奴醒来,揉搓着眼睛,“我,我不知道,对不起,公子,我睡过去了。”
“三更过了没有?”令狐楚急了。
“三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三更啊?”阿奴的话顿时让令狐楚崩溃了,这里是碎叶川突厥人的营地,哪里来的更鼓呢?
看到令狐楚着急,阿奴吓坏了,赶紧跪倒在地,叩头不止,“都怪阿奴,都怪阿奴睡着,请公子鞭打,请公子责罚。”
令狐楚在收拾自己的东西,将自己的长剑背在身后,将匕首别在腰带上,“好了,阿奴,不怪你,起来吧,别害怕,啊,没事了。”
看到阿奴恢复了正常,令狐楚难得地笑了一下,然后一挑帐帘,走出了帐篷。
碎叶川的夜风很大,将他的帐篷抖得很厉害,象一只黑夜里挣扎的鸟。风吹在脸上,就象有很多小鞭子抽打一样的生疼。这风,吹得骨头都在发冷。
所有的醉意都在风中全部消散了,令狐楚向娑葛的大帐走去。
去年那个冬天,他守护在娑葛的营帐前几天几夜,那是一个特殊时期,而现在,看似一切都平安了,可谁知道这漆黑的夜里隐藏了什么杀机呢。
彪悍的突厥卫兵象石人一样站立着,一动也不动,手持长矛,腰挎长刀,还背着弓箭,忠实地守护着他们大帐内的首领。
令狐楚到的时候,并不是红霞一个人,红霞与苏禄正在和马龙悄声说话。
“子羽兄,你怎么也来了?”苏禄很惊讶,他以为娑葛的这两个朋友喝了不少的酒,加上路途劳累,起码要休息一夜呢,没想到这两个汉人居然半夜起来了,希望并不是所有的汉人都是神弓鬼剑这样的。
苏禄坚持让令狐楚和马龙回去休息,理由很简单,客人,朋友,加路途劳顿,还有保卫首领的职责也应该由自己担当,令狐楚和马龙也就不好再勉强了。
“马大哥,令狐大哥,回去歇息吧,不然我兄长就被我们吵醒了,”红霞很顽皮地劝导着,看到令狐楚和马龙对视一笑,知道他们同意了。
突然,马龙抬起了手,示意大家都安静,同时开始侧耳倾听,“有人在靠近。”
令狐楚立即警戒,眼睛眯缝起来,搜寻着黑夜里的每一个角落。
苏禄和红霞也紧张了起来,手放在刀柄上,也跟着他们去看,可黑漆漆的夜色里,什么也看不到,除了风声,也什么都听不到。
“谁?”红霞紧张的鼻子头上都开始出汗了,她还是什么也看不到。
“他没有杀气,”令狐楚突然冒出了一句奇怪的话,“我过去看看,你们继续警惕。”
“我跟你一起去吧,”马龙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那张强弓,弓弦上扣了一支雕翎箭,手上还捏了两支备用箭。
“不用,他不是敌人,是冲我来的,”令狐楚没有了那份紧张,“子骏兄,回去休息吧,”说完,他大步走进了那片黑暗。
那条黑影在前面走,令狐楚跟在后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出了营地,走向了河滩的一大片空地。
“许久不见,公子一向可好?”那个身影并没有回头,令狐楚看到了那对弯刀。
“晚辈拜见鹿叉师傅!”
“公子急匆匆召见老夫,所为何事?”鹿叉的语气就象这黑夜里的寒风,冰冷彻骨,完全不同于上次两人在碎叶川的相遇。上次,在乌质勒的葬礼上,悲痛欲绝的鹿叉用短刀划破了自己的脸颊,留下了一条深深的刀疤。
“拜师!”令狐楚的语气非常坚决。
“老夫是公子的手下败将,公子的武功已经是上乘,何必向一败将拜师学艺呢?”从鹿叉的语气里,不再是简单的置疑,难道冬天里发生了什么事,让鹿叉发生了某些改变,不再与他切磋武艺了。
“在晚辈眼中,没有胜败,只有武艺,前辈的双刀快而狠,左右技击,最适合以一敌众,上次因老首领葬礼,未能与前辈学习,所以一直未能释怀。”
“想切磋一二又有何妨,老夫在羯丹山潜心研习刀法,尤其是对公子这样的长剑,已有所得,今天就如了公子的心愿,你我再较量一二!”
话音刚落,那条黑影就扑了过来,黑暗中两道寒光直扑令狐楚。令狐楚不敢怠慢,赶紧侧身翻出,躲开了那两道犀利的攻击,落地后一个翻滚,长剑出了鞘。
灯下,令狐楚打量着手里的这对弯刀。
这和大唐的刀、突厥的刀都不同,是弯刀。没错,大唐和突厥人的刀剑都是直的,从汉代的环首大刀到唐代的横刀,刀身都是直的,真正的弯刀来源于印度,后来经阿拉伯人的征服战争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并最终取代了直刀和剑在军队中的标准装备。
刀柄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木料,外面有一层鱼皮,并有细小的铁钉,顶端是一个圆疙瘩,格挡处是十字,在火光下闪烁着一层金光,也许是铜的,也许是金的吧,令狐楚并不关心是金是铜。刀鞘是黑色的,很象少女修长的腿。
刀从鞘中抽出来,很亮,与直刀不同,它有着优美的曲线,象大漠中蜿蜒的河流,没错,流水一般的曲线,令狐楚的手摸着刀背,顺着那条曲线起伏着,突然在刀的前端出现了刀刃,顿时鲜血滴落在了上面。
“该死,这刀的尖部怎么是双刃的?”令狐楚吸了口冷气,将手指放到了嘴巴里,不料却惊动了一边的阿奴。
“公子!”阿奴看到了滴落的鲜血,惊呼了一声,“您没事吧?”
“没事,割破了点皮而已,不妨事。”
令狐楚将刀握在手里,横砍,竖劈,前刺,后撩,都很合适,这刀真是好刀啊,之前自己一直使的是长剑,以刺为主,以砍为辅,长剑和横刀的道理差不多的。
长剑,对啊,自己的长剑,那是父亲留给他的剑,古朴,简单,黑色的把手和格挡,看上去就是铁的,只是剑身锋利,把手很长,足够使用者双手握持,不管是前刺还是左右挥砍都很适宜,尤其是在马背上战斗。
令狐楚把长剑放在了双刀上面,刀,剑,也许之间并没有什么障碍吧,无非还都是那些动作,劈砍而已。
他端起了那碗放置了很久的羊奶,之前阿奴给他倒了满满一大碗,被他喝得剩下了一半,然后就去研究弯刀了,此时已经凉了。
“阿奴,来,添点,”他向一边的少女发吩咐,看到阿奴拿了装了羊奶的皮囊走过来,就连同那半碗羊奶也递了过来,“倒满。”
“公子,”阿奴抬起头,“您应该把碗里的倒掉。”
“为什么?”
“盛新奶,必须要倒空手里的碗,”阿奴很认真地看着他。
“哦,这又是为什么啊?”阿奴的观点引起了他的兴趣。
“您想喝新奶,就应该把碗里的凉奶倒了,一个空碗才能装最多最新鲜的羊奶,不然,就不会是最新鲜的,也不会是最多了。还有,学习也是一样的,”阿奴咽了一口唾沫,似乎有些胆怯了。
令狐楚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回头看看那长剑,再看看那弯刀,又转过头来看阿奴,“你想说什么,没关系,不管对错,请直说。”
“阿奴以前学汉话时就这样,必须忘掉自己所有会的突厥语,就当自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婴儿,从最简单的说话开始,现在能和公子这样的汉人流利交往,就是例子啊。”
令狐楚放下了碗,一拍脑袋,“我明白了!”说完高兴得一把就将阿奴抱起,“哎呀,阿奴,你真是上天派来点化我的贵人啊!”
阿奴的脸顿时红了,“不,阿奴是大首领派来服侍公子的。”
令狐楚放下她,拍了拍她羞红的小脸蛋,“好,你服侍得非常好,我很满意,”说完,他端起那半碗羊奶,走到帐篷口,将羊奶泼在了外面,又转身回来,“来,阿奴,再倒一碗新鲜的羊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