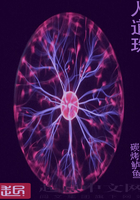“你全是道听途说。据说是有这么一对婆媳,媳妇为了给婆婆充饥,竟然割自身的肉喂婆婆。至于那个干娘,那是他一次乞讨饿死在路边,少妇用乳汁救他。他躺在少妇的怀里感到了圣母的恩泽。醒来后知道她有一个难以教养的儿子,就立誓当了这孩子的先生,从那天起四处流浪,四处从教。再后来为了感谢这位少妇,认了干娘,并给了她十亩地。”杨圣德支撑着身子站下来。
“柳泉,这个不孝子孙,还大义灭亲来批判杨柳公,亲自调查,得到的结论是:杨柳公是一个以‘骡背先生’为保护伞到处募捐办学,被当时伪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伪政府服务的大地主。现在三圣县城内外都在批判,您老就别在糊涂了!”
杨圣德不再说话,他说什么呢?他知道杨柳公没有斗争,去私塾偷听读书声而遭到熟师的呵斥。五岁丧父,姐姐做了童养妻。六岁随母要饭,十七岁给地主做工三年,分文不得,被打得头破血流,赶出家门竟然在破庙里昏睡三天。往往“正常”的人都会感到困惑,他为什么不上山造反?为什么不参加革命?连鲁迅的阿Q都知道革命党好,向那些欺压他的人和阶级复仇,把那些曾经压迫他的人踩在脚下,可以把所有富人家的孩子赶出学校,因为他们的父辈曾剥夺他受教育的权利,让曾经的仆人成为主人,让他们的孩子坐在教室里。话说过来,办学而没有参加斗争,但至少他没有反对农民起义,是那个社会造成的,绝对不能由杨柳公来挨棍子。一些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们围着杨柳公的死灵魂穷追猛打。这些寻常人不懂,当然也不必去懂。而杨圣德却偏偏要弄明白,却要保护那祠里的泥像—不知道是他的哪辈祖宗!“不管办什么学,谁动了杨柳公我们不欢迎,擎天杨送客!”杨圣德说着又咳嗽起来。
“其实,柳海鸣说的很有道理,我们不能为了一个杨柳公,就永远让望天杨的子民当文盲。”擎天杨听柳海鸣也极力反对父亲,错误地认为柳海鸣是真心来支持他办民校,便倒了一杯水,让柳海鸣帮助他动员父亲。
“办不办民校,那是擎天杨的事情。批不批杨柳公,那是上面的事情。我这次来就是想取走擎天杨拿回来的柳燕的嫁妆钱。”
“怎么回事?月仙梦来说,我认为她一个妇道人家胡折腾;现在你海鸣叔来,又提起大洋,擎天杨!你说。”杨圣德咳嗽得越发厉害,那张黑脸变成紫脸了。
擎天杨不再解释了,他怕父亲病情加重,他不能没有父亲。父亲是他唯一的亲人了。他知道父亲气一阵子就会好一些,他去给父亲倒了一碗热水,加了点儿槐花蜜。这是父亲最爱喝的,每当咳嗽最厉害的时候,父亲喝了便止住了咳嗽。
这一次,杨圣德没有喝,咳嗽得更加厉害,好不容易喘过气来,就对着擎天杨大声呵斥:“你认为他柳家大院会为教育慷慨解囊?土改工作中,柳老太迟迟不交大浴河滩,说是送儿子抗战,良田全交了,只剩下这荒滩了!这是什么,给党的政策唱反调。我们办学校是有点儿困难,可我们有广大的人民群众啊!柳泉拿大洋和教书来收买你,而柳海鸣又来想要回大洋,他们壶里装什么药?你懂你奶奶个头?”
“柳老师让我在望天杨下办学堂不是坏事!柳燕想读书也不是错事!你不想教柳燕,不想让她到咱家也罢了!你扯这么多干什么?爹!”
杨圣德坐在床沿上,几乎是喊,“你快把大洋取过来!还人家!”
“为什么?爹!”
“你不是做了噩梦吗?梦里的女孩不是花静杨和柳燕,也不是仙女或女鬼,而是三位圣公化作红骡子来到人间三公祠里告诉你,你不要和柳燕来往了!”
擎天杨到里间把大洋袋子提到父亲的跟前,“这不是柳老太和柳泉的意思!要还你还,我答应人家的事情不干了!是男人吗?”
“把柳燕请到家里让我教,要什么民校?你那先生也别当的丢人现眼!只是—你和柳燕没有定亲,凭什么要柳燕的出嫁费?”杨圣德大怒了,颤抖的手指着那个袋子,“还不把大洋抱走?我不想见你柳家人!”
柳海鸣疾走几步来到床前,提起袋子就走。
擎天杨一把将他的腰抱住了,说:“父亲!这大洋的确是柳老师给我办学校的啊!”
“这是小妹的出嫁费。你也不洒泡尿照照自己,一个赶骡子的骡背先生。我妈,我大哥凭什么给你啊!”柳海鸣死死抱住不放。
“爹,他一定会把大洋给杨圣德的,杨圣德比柳燕大了二十五岁啊!”
“柳海鸣你把大洋放下,我和你一起去你家。”杨圣德站起来,来到柳海鸣身边。
“爹,柳燕才十五岁,你忍心她嫁人啊!”擎天杨的话很凄凉。要不是柳海鸣在,擎天杨差一点儿给父亲跪下。
“没出息的东西!她嫁人关你屁事?你要是敢和柳燕来往,被人家打断了狗腿,别怨你父亲没说。我看你那民校别办了。”
“办民校那是没办法的办法。我想杨柳公能活在今天,他也需要建教室啊!”擎天杨看父亲情绪稳了下来,就动员父亲把大洋留下,好好地办学。
坐在一旁的柳海鸣霍地站起来,“大洋,给我拿走;不给,我也拿走。”然后气冲冲来到爷俩的跟前。
“等等!”杨圣德挡住了,“我们和你没有任何牵扯,钱是柳老太给的,还是擎天杨送回去!”
“我不放心!”柳海鸣说。
“你不放心,这钱我送!”杨圣德从柳海鸣手里接过袋子往外走,柳海鸣紧跟着出了院子。
擎天杨想想父亲的激动和身体,怕父亲和柳老太闹起来,几步蹿出大门外,突然发现柳燕蹲在地上掐着喉咙往外吐。
“你都知道了?你看父亲,他这一去还不和柳老太闹翻,这书我恐怕教不成了。”擎天杨的心像扎了一下。
“嗯!”柳燕点了点头,又矢口否认,“不是这,因为那个—”她想起擎天杨那一窝蛋儿鸟儿的,脸红得就像东南方三圣山上红彤彤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