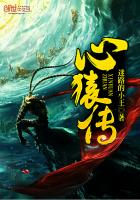元旦本该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但之于我们这样一个群体,却几乎是这个季节忙碌的开始,没错,我们仍在工作。
我并不是要抱怨,因为几年下来我也已经习惯,而且不知从哪一天起,节日之于我再没有多少期待了。
每年的今天都差不多,街市的灯都特别亮,音乐特别响,人也特别多,总是在夜幕来临的那一刻,仿佛全世界的人都被“放”出来了似的,比肩接踵的压马路。
当然,城市的今天也特别脏,特别乱,问题特别多,并且每年都一样!
佛曰: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是非,但他忘了有人的地方也就有肮脏!
在元旦的前夕我们只是休息了半天时间,然后在这接下来三天甚至五天的热情隆重的节日氛围的包裹下,我们也忙碌了三天甚至是五天,我也再一次见识了群众摧毁一切的力量。
我很庆幸这天下不是大胡子的天下,不然以我们S公司区区几条小生命——主要是我、王青松和钱家骏,恐怕早已为清洁事业而献身。具体细节我也不多赘述,大家都懂得!我也不多抱怨了,毕竟已经习惯了,也已经习惯了不抱怨。
命中注定你该忍受的事情,如果你说受不了,那只能说明你懦弱,而我不能再懦弱下去。
当我跑完最后一个业务拖着疲惫的身子最终爬到公司门口的时候,我已经累的胃都开始抽筋了,在我跨入公司的那一瞬,我听到一声尖叫——
“啊——”
我的脚直接被一个硬物给绊倒,我踉跄了几步借着这瞬间的惯性直接跌到离门最近的一个座位上,大脑神经的一阵抽搐也让我瞬间清醒。
什么状况?
我耸了耸晕乎乎的脑袋,低头一看,才看到门口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钱佳俊,一时僵在那里。
不会吧?真有人先我一步而去?
“钱佳俊?”我试探性地叫了一声,因为嗓子干哑,声音低得连我自己听着都费劲。
“钱佳俊——”我加大了声音,支撑着小心翼翼地朝他走去,实际上,我是扑过去的,并非是我激动,而是我的双腿此时已经使不上半点儿力气。
我伸出一根手指,小心地探着他的鼻息,也许是我感觉失灵了吧,但我觉得说是我大脑失灵了更恰当,因为我感觉不到钱佳俊的鼻息,手指碰到他的鼻尖居然是冰冷的。
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抓起钱佳俊的肩膀,使劲儿地摇晃,一边大喊道:“钱佳俊,你醒醒啊——老钱,醒醒——来人啊——不好啦,快来人啊——”
听到我的喊声,王青松只裹着条毛巾一下从洗澡间冲出来,“怎么回事?”
看到眼前的一幕,王青松立刻会意,拥上前来,扶起不省人事的钱佳俊,也跟着使劲儿摇晃着,“老钱,醒醒,醒醒啊!”随后他向我示意,喊道,“快,快打120!”
“好!”我掏出手机,几乎是手指颤抖着按动着键盘,第一次打三位数的号码,我却好似拨了好久,“1——2——0——”
我一咬牙,在手指即将按向拨号键的时候,一只手突然搭在了我的手机上,我有些不解地望向王青松,“你怎么——”
王青松也满脸诧异地望着我,随后顺着这只手我俩的目光同时移向钱佳俊,他咳嗽了两下,含糊不清地说道“不用了。”随后若无其事地做起来,看着我和王青松,不满地嚷道,“我好不容易打个盹儿,都快被你们晃死了,忙了一天你们居然还这么精神!”
我和王青松互相看看,只愣了一秒钟,明白个中缘由,随后我们一左一右将原本扶着他的胳膊使劲地向地上一甩,一口同声道:“你活该!”随后不等钱佳俊反应过来,我们分别进了一左一右洗澡间。
钱佳俊还在外面叫道:“别啊,轻点儿,我都快散架了——”
俗话说,同事三分亲,这一次,虽然我对钱佳俊颇为不满,但也算是这个劳累的节日里唯一一件值得交流的事情。
后来的事情很奇妙,我们三个单身老男人相约一起聚餐,说是聚餐,其实是我们在外面买了些啤酒熟食零食之类的拿到公司里喝酒聊天。
我们之所以如此大胆,一来是考虑到大胡子夫妻才刚团圆今天是断不会出现在公司——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二来,这个点大家应该都各回各家,各自参加活动去了。
毕竟,这是节日的最后一天,毕竟,我们也连着忙碌了好几天都没有准点儿吃过饭,如果不是搭档跑业务,相互之间彼此见面的机会都少,更别提聊天了。
最重要的是,毕竟这是节日,虽然只是个尾声,我们也该享受享受片刻的欢愉。
落地窗外的城市依然灯火辉煌,办公室内的我们却很安静,彼此吃着熟食喝着啤酒,也许真的是累了饿了,起初的十分钟我们只顾着狼吞虎咽,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我们酒足饭饱把酒言欢,追忆似水年华,王青松甚至还兴奋地唱起了歌。
直到我们如同喝水似的喝完两打啤酒之后,这种疯癫的状态才因着一个问题而归于平静。
王青松一边拆着新的一打啤酒,递给我和钱佳俊一人一罐,一边状似随意地问道,“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和钱佳俊几乎是同时愣在那里,钱佳俊叼着一个鸡翅,我刚向嘴里扔进去一片薯片,我们俩互相看看,好似都哽咽了,一时都没有说话。
老实说,在这里的几年里,我最怕的就是别人向我问到这些将来以后之类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将来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是怎样,对于这个明天如若不按部就班便一片混沌的我,你说,我该怎样来打算?
我想钱佳俊肯定也明白这其中难以启齿的东西,但他显然比我豁达许多,他愣了一下,啃着鸡翅,随即看着手中的鸡骨头,笑道:“以后?就这样!”
王青松笑了笑,随即与钱佳俊碰了碰杯,好像是明白了钱佳俊的意思,道:“这样是不错——可是我不能!”说后半句话的时候他扫视了一下四周,眼神转换间流露出一丝忧伤。
钱佳俊应该是没有听到他的后半句,他刚拆开一包零食的包装袋,弄出一阵响声,否则的话他应该也能看到王青松眼中的“忧伤”,而以他如此豁达的心态,肯定能在此时安慰安慰这颗潮湿的心。
可是我不能,我没有那么勇敢,也没有那么洒脱,我深知我不能在感同身受的情况下去安抚另一颗心,我明白那种导致深深的忧伤藏在心底淡淡的忧伤显现在脸上的东西,是责任!
任我再怎么不思进取,我也不能有一人吃饱、全家无忧的想法,因为我有我想照顾的人,我的身上有我不能忽视的责任。
我喝了一口啤酒,目视着王青松的眼睛,心中回道: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但我不能永远过着这样有一天算一天的日子。这是我想说的话,我觉得我现在足够清醒,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话说出口就成了这样,我说,“我不知道——我不能——”
哲人说,永远别向别人诉说你的软弱,因为别人不是你,他根本不能体会,也无暇关心。
尽管如此,我也相信眼前这两个伙伴是真心实意的关心我,也应该能体会我心中的悲哀,可是我还是说不出口,毕竟,宋青说的对,我是个男人,有些事,我得学会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