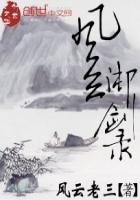“这个豆腐是她炒的,”男孩指了指女孩,脸上带点儿狡黠的、油油的笑,“连盐都没有。”男孩笑了笑,把一盘豆腐放在茶几上——茶几上的杂物已经全被清除干净了,宽大的茶几不比普通的饭桌小——女孩向他丢出一个轻蔑的眼神:“我给你炒菜吃,你不感谢我就算了,还嫌弃,真是没良心。”说完把一盘白菜摆在茶几上,抬起头去叫利朵:“还有几盘菜在冰箱里。”利朵正端着一盘肉丝走来,听到了吩咐,先停了一会儿,似乎是让大脑计算分析一会儿。得出了结论:先把肉丝放在茶几上在折回去。男孩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夹起一根肉丝:“你看,”他眼睛朝坐在沙发上的男子迅速看了一眼,引起男子的注意,右手指着肉丝,“这哪是肉丝,分明是肉条嘛——我跟你说,他切肉丝怎么切的:一刀没切下来,第二刀前后搓呀搓,把肉扯那么长(他比着长度),一头宽,一头窄,”他说着,一仰头把夹起的肉丝放进嘴里,认真地嚼了一下,“咸得要死,还有点糊了。”
“有本事,你自己炒几个像样的。”女孩不服气地说。但是不知道是她说得声音太小还是话太短,男孩仿佛没听见似的,依然站在沙发前面滔滔不绝地讲着:“最可恶的是这盘白菜,竟然没——熟,是生的!”
“啪”的一声,女孩在男孩的屁股上拍了一下。男孩子受到了惊吓似的立刻转过身来:“你就知道打我,说不过我就打,你是心虚了吧。”
“你再说,我就不是打你屁股了,我撕你嘴巴。”女孩扬起手做出要撕男孩嘴巴的架势。男孩先退缩了一下,然后脱下拖鞋,跳上了沙发。现在比女孩高出不少了:“你撕呀,你撕呀,”他在沙发上踩了踩,“你撕得着吗?”女孩变撕为打,一股脑拍打着男孩的腿。男孩连连后退。但他只顾着看女孩向他打来的手,没有看后面。一只脚踩空了,身体往后一倒,翻身倒在了男子的身上——男子坐在短沙发上——男子接住了他。他呵呵地笑了笑,扭过头冲男子说:“叔叔,快帮我打她,”男子一脸无辜地呆呆望着,男孩继续愉快地、调皮地笑着,“我可是请你吃饭了,你要报恩哪。”男孩继续说。
“这菜可是我炒的,”女孩说,“你要搞清楚。我炒的时候,你只是在旁边捣乱。”
利朵从冰箱里端来了两盘菜:炒猪肝、海带丝。
男孩在男子身上滚了一圈,落在地上惊叫起来:“这猪肝你也敢端出来,是人吃的吗?”
“又没要你吃。”女孩说。突然发觉男孩正弯着脖子俯视茶几上的猪肝:时机来了。她眼疾手快,伸出手去捏住了男孩的嘴角,男孩“哦、哦”地叫了起来。“你跑啊,我看你往哪儿跑?”女孩说。男孩手忙脚乱地推开女孩的手,转身敏捷地跳上沙发。利朵说:“菜都拿来了,可以吃了吗?我肚子都快饿扁了。”
“你没吃晚饭吗?”男孩站在沙发上说。
利朵点点头。男孩又说:“那你快吃,吃完了继续帮我做作业,”他说着又转向男子问,“叔叔,你会写字吗?”
“我?”男子感到莫名其妙地说,但又隐隐约约感到有些不妙,“我只读过小学,好多字都不会写了。”
“没事,”男孩说,“只要照着抄就行了,”他脸上带着谄媚的笑靠近男子——蹲在沙发的角落上,面对着男子,“帮我抄作业好不好?”
“可我不会写字,早忘光了。”男子有些为难。
“正好、正好!”男孩阴谋得逞了似的笑着,“这样你就会写得很丑了,才接近我的字。”
“某人脸皮三丈后,”女孩说,“人家又不认识你,凭什么要帮你呀?”
“屋子里有姓某的人吗?”男孩抬起下巴说。女孩和利朵不约而同地望向男子。男子一脸无辜地抬起头来,眼睛里是一片茫然。似乎刚刚回过神来,就无可奈何地陷入了这奇怪的气氛之中;愣了一愣。在三双眼睛的凝视下,再沉默木然的脸也会紧张地活动了起来。他微微动了动嘴唇,显得略微忸怩地挤出几个字:“你们别这样看着我。我原本不姓某的。”
“那为什么后来姓‘某’了?”男孩好奇地问。
“这事说来话长,”男子说,“我懒得说了。”
“切——,”男孩把端正地向男子伸着的头缩回去,失望地说了一声,“真是扫兴。”
利朵埋下头来吃着饭。他一边夹菜,一边眼睛往上瞄,观看着男孩与男子之间的对话。他眼睛往上瞄的时,线条流利的下巴微微偏转向男孩。马上又迅速转回来,像只麻雀一样灵活地转动着脑袋。听到男子说话的声音后,他虽然仍然埋着头,但是转动着下巴。尖而圆润的下巴微微向右边翘起来。“你叫什么名字?”男子问男孩。
“光宇,”男孩淡淡地说。似乎想停下来,突然又想到了什么,精神奕奕地指着女孩说:“她叫红梨。很难听吧。“男孩说完之后胜利似的笑了起来。
女孩轻蔑地瞥了男孩一眼。对男孩的话已经麻木了似的,已经不屑一顾了。男孩突然问利朵:“你叫什么名字?”
“柒零?利朵。”利朵抬起头来,望着蹲在沙发角落上的男孩。
“好奇怪的名字。”男孩说。说完淡淡的笑容又轻轻切过脸颊,切出淡淡的、可爱的笑纹。他把腿伸下沙发——只需要把屁股往前一挪——双腿伸进拖鞋里。弯腰去拿桌上的橙汁瓶:“喝不喝橙汁?”
利朵摇摇头。男子咽下去一块面包,一时没能从喉咙里发出声音来,弯曲着脖子挤了挤喉咙,但还是没来得及说出话来,只能用摇头代替。等一会儿才透了一口气,问:“你爸爸妈妈哪儿去了?”
男孩脸上浮浮的笑容突然沉寂下去,脸上收缩着皮肤的笑纹慢慢松弛下来。乍一看脸上安静了许多、干净了许多,只剩两只眼珠还在灵活地转动着:“我爸爸出差了,”他抱着橙汁瓶,脸上像被微风吹过似的,有些苍凉了,但是眼珠还能反射出亮亮的较为灼灼的光芒,在空气中碾来碾去,有点儿退缩地在男子和利朵的脸上碾来碾去,后来停在了茶几上,把肚子里的话藏在了俯视里。
“那你妈妈呢?”男子继续问。男孩俯视着,迟迟不肯把头抬起来,把橙汁瓶抱得更紧了;身子微微左右扭着,像在用身体碾碎什么东西似的。“你妈妈不爱你,爸爸也不爱你。”女孩忽然嘲笑说。男孩飞快地稍稍抬起头来偏向她,脸上含着一丝生硬的笑容。虽然脸上多了一丝笑容,但脸上还是冰冰的,没有感到温暖。眼睛里的光芒更加亮了,油油的像油漆是的:“别胡说八道。”男孩语气很微弱。
“就是的,看你爸爸给你买的东西都是便宜货。”女孩继续取笑着。
“切——。”男孩微微反驳一下。可是声音很轻,好像很无力似的,。这个拖长了的音到了,末尾软了下来。他把头埋向一边,然后又觉得不自在似的,把头仰着靠在沙发上。静静地仰望了一会儿,又仿佛觉得不妥,端正地坐起来,眼睛越来越亮了起来。这次的亮和之前的亮不太一样,这次是微微湿润了,是内眼角里越来越膨胀起来的泪珠在反着光。女孩瞅了他一眼,语气软下来说:“你可别哭啊,免得让人家以为是我欺负你。”男孩听了之后,眼睛眯起来,磨了一磨牙齿,摆出一个沾着泪光的微笑:“切——,你以为我有那么好欺负吗?”他把橙汁瓶举到空中,透过倾斜地切过塑料瓶的黄色橙汁,看着灯泡:只在橙汁中间看见一个模糊的圆影子。他突然警惕地放下瓶子,侧耳倾听。似乎还有一丝怀疑爬上眉头,把眉头轻轻压着;听到了轻轻的脚步声,他皱着眉头说:“等一下,有脚步声,”他望着楼上,声音就是从那上面传来的,“糟糕,我奶奶下来了,怎么办?”
女孩站了起来,思索了一下,扭头对利朵说:“就说你是光宇的同学。”
“那个某叔叔呢?”男孩插嘴说,忽然机灵地睁大眼睛,接着笑了起来,“就说是利朵是爸爸。”利朵吓得马上抬起头来但是呆呆地望着男孩,没说出话来。男子担忧地说:“你奶奶不会报警吧?”
“你装作是利朵的爸爸,不会被发现的。”孩说。正在说的时候,耳朵里传来下楼的声音。步子缓慢,但是在安静的环境下,每一步都清晰地传出来。男孩急忙转头望向楼梯。迎面飞来一阵苍老的、像碎裂的爬着裂缝的铃铛的声音:有点儿嘶哑,又有点儿软绵绵的,力气不足似的,话飞到半空中就开始往下垂落下去;虽然眼睛里明明带着惊诧,但声音依然疲软:“他们是谁?”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奶奶扶着楼梯旁边的扶手走下来:头发花白,盘在脑后。鹅蛋脸上垂着许多松弛的皮肤;皱纹并不深,浅浅的,但是繁多,像筋脉一样蜿蜒在松弛下垂的皮肤上面。身体还算硬朗,虽然走得不快,但是稳当,不一会儿就走到了楼下。她穿着一套白底印花的睡衣,上身披着一件黑色的外套;皱着眉头——两只淡淡的、几乎光秃的眉毛努力挤在一起,似乎有些近视——眼睛眯起来又睁开了,然后不太确信似的继续眯着眼睛。这一系列的动作使额上松弛的皱纹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他们是谁?”她边眯着眼睛,一边往前走。快走到沙发旁边的时候,男孩忽然说:“他是我同学利朵,”他指指利朵,然后又把男子指给老奶奶看,“他是利朵的爸爸,”说完瞧了瞧老奶奶的脸色。见老奶奶的脸色上还有疑虑,又加了一句:“利朵给我讲作业,”男孩本来要指指作业本的,可茶几上全是饭菜,他伸出去的手指不好意思地蜷缩起来,在脸上发出敷衍似的的笑,“奶奶,我们饿了,先吃点宵夜,吃完了再继续做。”
老奶奶把眉头皱得更深了。忽然又伸展开来,扬起一只左眉,看看利朵。利朵连忙礼貌地喊了一声:“奶奶好。”老奶奶听了之后点点头。又走上来两步,找个好角度看着男子。男子连忙向她鞠了一个躬。老奶奶上下打量了一下他,准备转身的时候看见了被撬坏的门,她嚷了起来:“这门怎么回事?”眼睛往地上一扫,看见了地上的工具袋,扳手的头部露了出来。她指着地上的工具袋问:“这是怎么回事,这袋子是谁的?”
“嗯……”女孩先发出一个鼻音,拖住老奶奶焦虑的情绪,想了一会儿,指着男子说:“他是修理工人,那个是他的工具袋。那个门有点坏了,我叫他帮我们拆开了,看看有什么毛病。”
老奶奶挑起一只眉毛盯着男子。男子显得有点儿局促地站起来,接受着老奶奶的注视;睁大着眼睛,似乎想努力摆脱脸上露出的不安和局促,目光慢慢游离到女孩脸上,看见女孩在一个劲地给他使眼色。他吧目光游离回来对准老奶奶注视着自己的眼睛,轻轻地收缩面颊,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微笑:“是的,我是一个修理工。”
老奶奶把眉头松开了又连忙皱起来,深入地问:“你是修理什么的?”
男子把嘴唇紧紧地闭了一闭,睁大着眼睛,两只眉毛蚯蚓似的钻来钻去,钻出一些细细的皱纹;看了看旁边的利朵——正呆呆地看着他——他把闭起来的嘴唇无可奈何地打开了:“修理……水管的。”
“对,介绍一下,”男孩突然活跃起来,“这位(他两手伸向男子)就是本市优秀的管道修理工。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曾获得过三年的技术标兵、市级劳动模范,CCC国家免检、国家强制认证……额,我词穷了,”男孩一鼓作气说了好多,到最后词穷了,转向女孩,“还有什么表扬人的词?”
幸好老奶奶没有理会男孩这一大堆的话,认真地对男子说:“修水管的?”男子点点头,但表情还是有点儿愣愣的;老奶奶继续说下去,“刚好厕所的水管有点漏水,你能帮忙修一下吗?”
男子眉头紧皱,犹豫了一会儿。但是在老奶奶灼灼目光的注视下,他不得不迅速将眉头展平,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没……问题。”
“多谢了,这里来。”老奶奶转过身走上前去,在前面领路。男子在三个孩子担忧的目光的注视下,慢吞吞地离开沙发,慢吞吞地跟着老奶奶走。老奶奶突然转过身头来,眉头又皱了起来。男子看见她突然皱眉头后,有点无措。看见老奶奶张口了:“你怎么不拿上工具袋?”她指指地上的工具袋。男子恍然大悟:“哦,我忘了,忘了。”连忙转过身去,把工具袋拎上,再次经过了三个孩子担忧的目光。三个孩子的目光一直紧跟着他。他走回来取工具袋时,三个孩子的目光向右移,为了移到最右端,头也跟着往右偏。他提起工具袋向老奶奶走去的时候,三个孩子的目光整齐地向左移,移向最左端的时候,脑袋往左偏。最后目送着他跟随着老奶奶走进了一楼角落里的卫生间——从楼梯下面进去,几步就到了。摁开光的声音。灯光从角落里倾泻出来,泻在楼梯下面的地板上,把地板照得黄灿灿的。地板上细腻的花纹染上了金色的光,仿佛要兴奋地跳动起来似的:其实那只是光亮的微微流动;光不仅泻在地面上,还有光辉往墙面上扫去。但这些光辉大都是被物体遮挡了一部分,光亮不足,而且混杂着深浅不一的物影,照在墙面上有些灰暗。被灯光放大的、显得奇形怪状的物影在上面一印,墙面从灰暗变为了朦朦胧胧的。但是墙上有抹光亮——像刀划出的一痕似的——特别亮。卫生间里接着响起了老奶奶和男子低低的交谈声。隔了一会儿,老奶奶走了出来,男子一个人留在了卫生间里。
卫生间里先沉默了一会儿。正当老奶奶觉得奇怪的时候,突然传来“嘭嘭”的声音,好像是在敲着什么,声音好像微微颤抖着、震动着。在空中短暂地颤抖了几下才消失,好像在敲打着什么有弹性的东西。老奶奶和三个孩子诧异地睁大了眼睛,三个孩子面面相觑。“嘭嘭”的声音又传了出来,再次把三个孩子好奇的眼神吸引过去:伸着脖子往前探了探,往前偏了偏,仿佛想寻找一个能看见里面的角度,可无论怎么看也看不到里面的情况。老奶奶像受惊了似的,猛地睁睁眼睛,像突然从梦中醒来似的,眼皮颤抖了一下。卫生间再次沉默下去。等了一会儿,“吱吱咯咯”的声音又跑了出来像在拧动着什么东西似的,像是啮齿动物在噬咬着什么似的。又敲了一下除了“嘭嘭”的声音之外还有另一个越来越大的声音把“嘭嘭”的声音淹没下去,它突然变得极响,像脱离了束缚似的向着空气冲刺——“刺刺”的声音。又听见男子后退的脚步声。“刺刺”的声音还在继续。又是“嘭”的一声,好像撞到了门。门被弹了一下,在空气中发出微微颤抖的声音。水雾从门里喷了出来,喷洒在墙上。墙上湿了一大块,墙面更加灰暗了。贴着地面喷出来的细小的水雾在地板上轻轻跳跃着。迎着光亮,这些丝丝的水雾在地板上闪闪烁烁。水雾一层一层地往地板上面覆盖。“刺刺”声渐渐地小了下去。水雾也少了许多,正慢慢地向卫生间里收缩,应该是被压下去了。老奶奶和三个小孩受到惊吓悬起来的心渐渐放下去。可是他们又听到“嘭”的一声,不知道又是什么东西脱落了,他们的眼睛马上又瞪了起来。接着听到了汩汩的流水声。汩汩的流水声出现几秒之后,突然变得尖锐,变成了“刺刺”声。水雾像折扇似的在门口逐渐展开,展开成一个扇形。扇形的末端顶着墙壁,水雾喷洒在墙壁上。水雾在墙壁上积聚起来,凝成细细的水流。墙壁在沐浴着,水流沿着墙壁蜿蜒地流下来。水流漫上了地板,像一条透明的蟒蛇一样慢慢延伸出来,越来越肥了,越来越蜷曲,最后在楼梯下面盘踞起来。光亮照在上面,把“蟒蛇”的身子切割成黄灿灿的一块和黑漆漆的一块。照着光亮的那块身体在轻轻往前蠕动着——睡在慢慢往前流着。扇形的水雾变得浓密了,变成了水帘。水帘上面反射着熠熠的、粼粼的光亮。突然这水帘收缩了,收缩成一大股冲向墙壁。水帘的边缘还没有完全聚拢,它们切割着空气,时而宽,时而窄,像展着翅膀似的;发出了“嘶嘶”声音,像蟒蛇吐信子。这还没完,水的冲击声骤然猛烈起来,卫生间里充斥着水柱扫射墙壁的声音。蓦地尖锐起来,“哐”的一声——玻璃碎裂的声音。男孩惊讶地张开了嘴;女孩脸上表情僵硬;利朵手中啃了一口的面包从嘴巴上掉下来;老奶奶说不出话来。
男子突然筋疲力尽地叫喊着从卫生间里冲出来:“哎呀,哎呀。”外面的四个人都惊呆了:男子衣服湿透了,湿透的衣服皱巴巴地粘在身上,大条大条的裤褶子向左歪着向右扭着;短短的头发现在立了起来,像刺猬一样,而且根根都闪着亮光,发隙里也荡漾着细小的光亮——它们好像从头发里往外钻似的——这大概是因为他在往外跑着吧;眼睛红红的,倒不是哭了,而是水大量地溅到他眼睛里造成的;脸上也全湿了,一滴水从鼻尖上旋转着拐下来,拐到鼻腔里;鞋子灌饱了水,唧唧地响着,一踏在地上,就会有水从鞋面上渗出来——脚印成为了小水滩。他一抹脸上的水,抬头一望,望见四双惊讶不已的眼睛。四双惊讶不已的眼睛像在空气中组成了一面屏障,阻止了他的往前。他已经往前迈出一步的腿收了回来。面对如此肃穆的气氛,他露出了傻傻的笑容:“我歇会儿。”可是卫生间里水流的声音凶猛地继续响着,漫出来的水越来越多,面积也越来越宽阔,它们蜿蜒迤逦地延展到客厅里来了。老奶奶呆立在原地。男孩看不下去了,跑上前去,利朵也跟着前去了。踩在漫出来的水上面啪啪作响。男孩说:“糟糕,我的鞋子进水了。”“我的鞋子也湿了。”利朵说。
打开了半掩着的门,水花“刺”地一声冲出来,看这方向要冲到男孩的胸前来。男孩“哎呀”地叫了一声,身子及时偏向右边,强劲的水花擦过肩膀冲刷出去,冲到墙面上响起一片细细的零碎的嘶嘶声,像小虫子口器发出的声音。男孩看了里面的情况惊叫起来:“卧槽,惊人的壮举啊,英雄哥!”看见男子弯着腰,用手堵住水管,但是凶猛的水还是从指缝里蹿出来,“刺刺刺”地往空气里喷洒着水雾。在脱落的水管前面十几厘米的地方,还有一节水管脱落了,剩余的水管往空中地伸着,剧烈地左右摇晃着,水柱从管口中喷出来,往男子的身上冲刷着,冲到衣服上面散成圆形的水帘。水帘的边缘出现了锯齿状的水雾,正在颤动着;一会儿勇敢地伸出来,一会儿畏缩地往内蜷缩,仿佛在慢慢旋转着。男子抬起一只手臂阻挡撞击在衣服上散成的水帘往自己的脸上洒去,但还是有细微的如尘埃似的水雾往头发上掩去,头上的细小水珠在一惊一乍地跳跃着。男孩的视线已经被漫天的水雾给模糊了。往前迈出一脚,踩到了什么东西,发出“吱吱”的声音。这东西是硬邦邦的,男孩在脚上加了一点儿力,脚下踩的东西竟然往前滑过去。“什么东西呀?”男孩往下一看:在模糊的水雾交织成的水网里面,有一些绿色的东西。水网忽然一疏松,露出了一部分清晰的视野,看清了地上的东西原来是碎玻璃:“哦,你的人品就像这玻璃一样——碎了一地。”男孩玩笑着说。
“别说风凉话了,”男子被水冲刷着的脸歪曲着,“快来帮忙哪!”
“可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男孩郑重其事地说。
“让我来。”利朵忽然说。男孩把目光转向利朵。利朵从男孩身旁挤进去,对男子说:“你也不用这么夸张吧,你装装样子就行了,”他抬起头望着男子,大量的水雾趁机扑上面颊来,他连忙把眼皮闭下来,嘴巴不受影响似的继续说着,“你还真把自己当修水管的了?”
男孩忽然沉思起来。有一股扭着身躯的水柱,在扭转的过程中冲到他的腿上来,把他的睡裤淋湿了一大半。“哎呀!”他提起腿抖了几抖,仿佛想把裤子上的水都抖下去。弯下腰,一把拧住湿得最严重的地方。拧出的水顺着脚踝往下滑——细小的一股,轻轻地贴着皮肤。太轻,甚至感觉有些痒痒的。痒痒的感觉往下画着曲线,像只小毛毛虫在爬着。踩水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快要靠近他的时候,声音特别清晰,可以听清楚水什么时候往上贱,什么时候往下落。他先扭转着脑袋往身后看——一双手仍然拧着裤腿,微微隆起的背部像拱桥一样——看见蓝色的裤子,知道是他表姐。直起身子来:“表姐,怎么了?”
“你爸爸打来的电话。”女孩拿着手机说。
“手机不是摔坏了吗?”男孩奇怪地问。
“我也不清楚,”女孩说,“我刚刚把电池重新装了一下,就能开机了——虽然屏幕花了,但还能用。”
男孩把湿漉漉的手在身上的干衣服上擦了擦,踩着水,接过了电话,靠在耳朵上,一边听着,一边继续往前踩着水。“嗯,”男孩对电话那头的人说,像在答应着什么似的;声音低低的,老老实实的,“嗯……为什么?”他走出了漫水区,鞋子在地板上留下一串水滩;一串水滩在地板上缓缓地转了一个弯。房门开了,它们就转进房里去。“我不!”男孩反抗地把声音加大,然后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疲软下去——刚刚的那一声就像一根尖锐的针吧——泪水在眼角处凸了出来,亮晶晶的;悬在眼角里,一时还没有足够的分量坠下来。卫生间里嘈杂的声音从楼梯下面爬出来,转着弯穿过了客厅,再转一个弯,钻进了房门,在他身后飘荡着。他对这些声音置之不理,仿佛他们存在于两个不同的空间里。嘈杂声经过波折,飘到房间里的时候已经很微弱了。像山边传来的回声似的,虽然只剩淡淡的话语的痕迹了,但是轮廓完整,还能听得很清楚:“怎么弄成这样?他到底是不是修水管的?快拿拖把来。”老奶奶终于叫了起来,似乎能在脑海里看见她愁眉苦脸的样子。“能不能把水先关掉?……什么?关不了?唉……那个,那个……爸爸。”利朵的声音。“什么……额。”男子有些反应过慢。“啊——,我都想放弃了,你怎么能把好好的水管弄成这样呢?”利朵有些烦躁起来。“好好的?本来就有点儿漏水好不好。“男子不肯承认自己的过错,狡辩着。
“我知道了,”男孩的心情仿佛有些好转了,那两颗欲落未落的眼泪渐渐缩小了,不知道是被风吹干了,还是被眼睛吸回去了,眼泪变成了淡淡的一点儿泪痕粘在眼角上,现在只能看出一点儿湿润的痕迹,“但是,我一个在家,晚上有些害怕,”男孩说。听了电话里传来一阵嘈杂的——至少旁边听的人,感觉那硬硬的、突兀的喇叭声是一种嘈杂声——声音,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那好吧。”男孩等了一会儿,挂了电话。侧耳倾听:竟然没有了喷水的声音。他觉得奇怪,走出门去,看见利朵、女孩和男子在拖地和扫水。他带着怀疑和惊异的表情走上前去:“修好了吗?”他问。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修好了。”利朵抬起头来,左手撑在拖把上面,右手叉腰。
“你真是厉害呀!”男孩又惊讶又羡慕地说。突然注意到利朵全身都湿透了的衣服,目光往利朵衣服上凝视了一下,一缕微笑像小刀子一样轻轻切开了嘴角:“我去给你取干衣服,”本来要转身,看见浑身湿透了——像被沉重的水压弯了腰似的,弓着背,膝盖微微弯曲着,趿着灌了水的鞋子,活像一只落水的公鸡——的男子,利朵呵呵地笑了起来,“某叔叔,我去取我爸爸的衣服给你换上吧。”他这次真正的转了身,迅速地跑进房间里,以至于连男子那声无力的“谢谢”都没听到。
十几分钟后,水拖干了,衣服也换好了:利朵穿了一件灰色的薄毛线衫,上面编制着卡通的图案;一件蓝色的长裤。男子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一件灰色的休闲长裤。
老奶奶叮嘱了男孩和女孩几句,就上楼去了。走到了楼梯中间,突然转过头看了看男子,似乎想说什么。迟疑了一会儿,又把说话的目标换成了男孩:“他们什么时候回去?”
“马上,马上!”男子迫不及待地说,边说边站起身来,往门外走去。利朵也随后站了起来,望望男孩。男孩望了望利朵,又望了望老奶奶。老奶奶的凝视从楼梯上压下来。利朵不知是犹豫着,还是在沉思着,低着头默默地往门外走去。男子根本没有等利朵的意思,出了门就急匆匆地走了。利朵到了门口,男孩忽然叫住了他:“利朵,等一等,”把利朵叫得停住之后,又转向老奶奶哀求着说,“奶奶,让利朵今天就睡在我们家好不好?我叫他给我讲作业。”
老奶奶皱了皱眉头。皱着眉头的时候,她的眼睛失去了焦点,仿佛在沉思。一会儿又把眉头松开了,目光的焦点重新回到男孩身上:“好吧,早点睡。”
“他是怕鬼,不敢一个人睡。”女孩笑着说。男孩皱着眉头,瘪瘪嘴角瞥了她一眼,但没有回话。瘪了一下嘴角之后,有把嘴角轻轻地扬上去,挂着不在乎的微笑。
“你的作业,我做完了,”女孩说,“要记得谢谢我。”
“切——,”男孩做出不耐烦的样子,“我刚刚不是让着你了嘛。”
“懒得跟你扯了,我睡觉了,明天还要上学呢——明天早上记得叫醒我。”女孩说完走上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