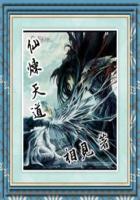十三
瞅这一段的天气儿,也确有些怪哉,这一连数几日的,都这么不晴不雨,无风无响的。满天的浮云更是重重叠叠、密不透些气儿,就象有一口无限硕大的大铸锅紧扣那儿,严实隔断了天地间的气息,直要叫了人郁闷不已的。
却说自打那日晨王凡的‘新型农合’挂牌之后,这洪仁轩的心里间,也就一如这时下的天气儿,虽说也无乐无喜,没怨没忿,却又总觉是,就有某种难描难言的心思紧布于心头,且又挥之而不去。
想这过去时刻里,他曾有切切楚楚望人诉有这么一段‘苦’:说在这孤岛一般的小洲上,在这过去前后几十年时间里,他这里的,确也像模像样做几回人来的;然而更多时候,他却又是在被迫着做成‘驴’、甚至是‘鬼’、的模子呢。他那里本来也不愿意去这么做的,谁爱动不动就去扮作恶人的样子来,可他又说他不能对不住老祖宗呢;再者又说了,这千斤重的担子,总归得有人去挑不是。而稍得慰藉的是,这无论是逢了哪样的年月,抑或有了这大小的事儿,其左右乡亲,却最终都还能理解到他,支持于他,致这洲里的景象等,也因此而稍让人心里满意、满足的------
可要瞧了这近年间的情形,这近年间的情形,则又会让他倍感这世道之艰难呀。现实一刻缘于这上方政策策略的一步步放松、转变,有些人特别是许多年轻人的思维思想,就一如这脱缰的野马,都在那随意驰骋了甚至胡奔乱闯一气来。谁说不是么:就说说去年秋末的那起砍伐古柳的混事吧,初一时谁能就想到了,这耗儿等伢儿几个,愣就是一声不吭,斧子砍刀齐上,就生生把那大碑树砍倒了一棵下来。就那一刻里,倘若不得他洪某人沉着冷静,急中生智并及时极力地从中斡旋,则怕而今这小洲某旮旯里,早添有几个残胳臂瘸腿的娃儿了。至于会留于外道人的笑谈,则不用细说了。
还有前不久这董家二虎子霸滩霸塘的事儿。瞧瞧了,就自个儿于那相磨相磨,再望那插一面小破旗,或赶上头牛犁个圈圈,这一切就都成你的了?这塘以前没咋拾弄不假,可赶到年底了,大家伙人各多少能捉些鱼虾啥啥的。就这你也好意思的,还不让别人撇一担水去。就是村后首那道河滩儿,也是大家经商量而说好了的,却是要留待大家伙共同牧牛牧羊用的。你犁便犁了,却还容不得别人说个一句两句来,人要一提就喷饭。这都是于哪学来的规矩呀,这眼里还有没有大家了?
还有这秦妍枝和运来娃子的事。以现眼一看,双双都得有理、有理的。一个要娶:你有言在先呢;一个不肯嫁:我娘大病未愈,我如何能丢下她一个------这似乎都情有可原、能说的过去的。可倘若拿话说回来了,若这两边人家里,要有一方能严守于理于礼,都不会落成如此之僵局的------
还有这王凡、和他的‘新型农合’,不好说,一时还真的不好如何去说的。瞧过去这国家各业‘合’了几多年了,现好不容易实行分包了、分田了,大家伙都说是大获民心、大快人心哪!可才几何时,也不知这小子都有哪根筋作怪来,却弄了个‘新型农社’在这摆弄开来。道理倒说有千千万,可你能离得了一‘合’字吗,离得了一‘合’字吗?瞅事物唯瞅其本质。现时的中老年各人等,可是听过了这‘合’字都会心烦头痛的。因以前‘合’了这许多年,就得一结果,就差些没把前胸前腹都‘合’进自己的后背里去了;除此而外,还落得些什么呢------可这王凡他就是要逆众而行、逆势而行;还一付矢志不移、不达目的而不休的势头呢。可王凡呀,你如此之思维,如此用事,就能真的无所顾忌的吗,你就不惧别人给你来一顶‘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大帽吗------
这些却仅仅还只为其一呢。就譬如、譬如这上方有召有示,尔辈即行呼唤奔赴,如‘办厂’、如‘围田’,虽变化万千,而充其量就算得个‘弄潮’之举呢吧;尽管是变过来又覆过去,可终也超出不了正常人思想思维的大圈子的,就算一旦有事儿出来了,却最终也好给调整、平复的。这王凡此来不打紧的,他却是‘启’了个大不妙的‘头’呢;倘若,——是说倘若,倘若这大家伙以后都似他这般样,以己虑为心,以己志为志;以己虑为心,以几志为志,那,有谁能予担保得,明日这洲间就不会冒出个‘理想之家’啥的,而后日又挂一‘自由国度’的呢?若如此闹腾起来,闹闹个不休,想此后这息龙洲之间,却不会从此就乱了套数了吗,却还能有一些宁日可守的吗?而事情要真是败落至这一步了,自己如何对的住乡里乡亲,又如何去见九泉之下的老祖宗呢------
乜斜着门洞间灰浑无尽的片天,洪仁轩还坐落在那把古色太师椅上,心里却七七八八,翻来覆去的转个一刻不休歇,而正虑到恳切处、恳切处,就见门洞里有人影一晃,跟着走进来小侄儿耗儿。“瞧你,这正想事儿吧。”耗儿即行开口道。
“噢,没啥、没啥的。得空养养神而罢。”洪仁轩立时调整了姿态。“坐。看你气定神静的样,是事儿都办妥了吧?他又问。
耗儿就回道:“妥了,也依您吩咐的,都送去老仓库里了。”
洪仁轩就道:“倒能够喘口顺气儿的了。”又道:“就坐下说话.”
耗儿就现一种得意之色,一时竟不肯落坐:“还是您想的周全呢!倒是凭谁都不及去想想了,这仁智老伯此一回的,竟能如此诚恳服帖的。”
洪仁轩道:“这事况行进到这一程了,似此运作,该是他最后也是最好的拣选了,却是下策亦上策呵。噢,就不知于秦妍枝那边的,可有些新消息的么?”
“就昨儿傍晚时刻,她大表哥倒有过来见我的;却说了,等事儿平静些了,就要来接了他小姨过去的。是时我刚有去见过老智伯来,也就给了个准信儿。估计就这一两天了,他就会过来接了他小姨娘过去的。”
“实在惹不起,就只有躲躲了。这也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对策吧。只是、只是她一家一旦真远走了,作为相邻乡亲的,大家又会一时过不去这坎坎的。”
“就象您刚说的,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不然又如何呢?”
“其实要细想想了,于这件事儿之间,我也有失察之过的。都是我老思想、老观念浓厚些了,就没能站住现代年轻人的位置替妍枝想想的,而又放任了你智伯一家的随心所欲,才最后铸成了这结果的。”
“您也不要把些不相干的糗事儿,都生生去望自个儿身上扯。就这事生成之前吧,我也有去找妍枝拉扯过的,可她就说一句:‘这都是命呵’,其他别无一语。却是叫人想去帮帮,也都无路无计呀。又或许,她想过就随命游去吧,只是到这最后一刻了,才陡然改变主意的。不撞南墙不头痛么。”
“说的也是呢。现实大家只有在这为她一家悄悄祝福了,这可怜可叹的女娃儿。”
“现今却还有桩难事儿,也不好如何决疑的。就昨儿吧,子权他几个做提议说,这去年间算是猛收一年的了,而这各家户的,就都有些积攒来;他等想发动大家伙凑一凑,也好先帮秦妍枝去把那笔‘人情帐’垫付了下来。这事若成了,或许就可疏解些秦妍枝内里的泔结了,也可略尽尽大家伙乡邻几十年的部分心意;只是,只是顾忌着这事儿呢,说大家一来未及与秦妍枝通个气儿,二来也不知这事儿一旦敷行了事,终极了却是妥与非妥的,因此还犹豫着。”
“这个念想却不差,一点不差的。只是这事就甭操之过急了。想想这秦妍枝那里吧,也一直没明白言于众,说她就一定一定不嫁了;而你老智伯那里的,也一直并没有去拿过钱来说话儿。所以这事宜从缓、从慎的好。”
“瞧您说的,道理俱在了。我回去就如实去望他们说说了。”
“就这么个理,宽想想就能明白的了。噢,这一段,这一段店里的情形还好吧?”
“店里的情形?一般般吧。”
见洪仁轩另题说话,耗儿若有所思道。
“一般般?就是说仍不见些回升的迹象咯?”
“想事实就是如此吧。”
“看来,看来。我们须得即时调整我们的思路方略了。”
耗儿闻言却报以沉默了,老一刻才闷闷道:
“这话说说倒容易了。叔,我现在才明白人说的:隔一行,隔一座山呵!明白这其中的一些道理了。其实这事儿我们也虑有一些时刻了,求路无门呀;最为可叹的是,直到目前了,我们却连独立的业务员、也一直虚位以待着。所以我们根本不了解现实的市场行情及走向。既是全然无知晓,又如何去做得改善、调整?我现在甚至在想了------”
“你现在想了,你在想什么了?瞧你这没精打采的样,你不会是完全丧失信心了吧?”
洪仁轩倒不愠不怒的,就定定地瞅住耗儿不放。
耗儿一时就有激动的样子,就搓一遍手,又憋住一股气儿道:“想这话我也只能于这跟您说说了。就这眼下而言,我所想已不是这有无信心的问题了。都有老一段了,我怎么就总觉着吧,就总觉着吧,可能我们于开始时刻,就有轻率盲动些了,或说我们根本就没作些必要的准备的。这边走边看,边看边走,万事就待去实践中逐次解决;似这种的行事作风,却只适合我们较为熟悉的方面的。是我们初时只顾了去赶风潮,就有些急不择路的了。”他一时哩哩啦啦、咬文嚼字的,至末了竟有些嘘嘘揪揪的了。
洪仁轩又显然极认真极认真地,静听着眼前耗儿的一遍诉说,还会不时点点头来:“这瞧你说的,不至这样吧!就想想了,这事儿大家酝酿也不止月余的时间的,是呢吧,所以一时虽不说虑无不周啥啥的,却也是经大家伙都拿话了才始启动的;所以就有些问题了,也应从我们实际认识水平方面找原因,不是么?而现时凭谁也不能保全的,保全自己仅在一回身之际,就能对一个全新的领域作出精准的判断而无点滴偏差的。现时可好了,就瞧了,作为这一小班的领头人,才遇有点儿小疑难了,你却都不积极努力去想些办法来解决,倒窝这里叽叽咕咕、挠耳搔腮来。哎,说你一向不是颇有自信,敢作敢为的吗?要瞧了你现实的模样,你叔我倒有疑问的了。”
“是我叫您太失望了,是吗?”耗儿就道。
“也算是了。不过我还想问问了,你忽一时就似此昏昏懵懵、萎靡不振的,是不是,是不是就受有其他外在的影响了,你所说的这些,又都是你个人的真实感受感言吗?”
瞧这话问的!耗儿就又激情道:“叔,侄于您这里说话,还需装模作样、学人口舌的呀,这话却问的我好糊涂了。”
洪仁轩就顿一刻,道“没有就好,没有就好呀。——叔我这里可有听说了,日前这王凡他那里的,就发有些类似的议论的,我就不辩这事儿的真假了?”
“噢,您说这个呀。不错,他是有参与过我们一些讨论的,”耗儿就来解释道:“但他所说的那些,都很有积极意义的,您是不是,是不是偏闻偏听到什么了?”
“应该不会吧,”他叔就道:“谁会在我这胡咧咧呢,是吧;可能,可能见你有反常,我就多想想了吧。”
“这不象您呢,叔。您不会近来就对王凡个人就有了哪样的想法吧。”耗儿迷糊道。
“对人起有想法?”他就略一怔:“这不好说,这个还真不好说。——噢,噢,我是说在对待于你们这一班年轻人在思想行为方式方面的,就象你刚所表露的的这些,却又不会叫人很迷惑很费解的么,不是么?”他盯紧耗儿道。
“可能,可能,我陷落进自己所挖的陷阱里了------”
他就道:“你能做这样认识当然好,不是么?其实,也不知你都有否想过了,就这眼下而看,但凡大家还有得想去干企业、从商道,也无论你都从哪一路做起了,而相对而言,我们所要面对的都将是一个全新的界面,全新的领域。我们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先学后用的,怕也无处可学呢吧。我想时下不独我们如此的,现时所有涉足于此一列的同道,其多数人,或急或缓、或轻或重都会面对上这一问题的。”
“那,现实之下,我们到底该如何面对才好呢?”
“瞧,叔才要问你呢。叔说了这么多,难道还不够的吗?“
“说了不怕您生气。一时之间,我怕是满脑空空,啥也想不了的。”
“哀大莫过于心死。如果连一点起码的信心都没有了,那如何能办成了大事?就象刚说的,大家既想着继续走下去,既是有那么多人在同一起跑线,那现时要拼的就是人各的意志和才智了,所以,现时看就看,看有谁能凭借自己的坚强意志和才智率先走出来了,走出来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奋斗之路,你说呢?”
“可,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见洪仁轩言词切切,越说激奋了,耗儿却道,“眼下我们却是不敢自诩为,就有那种胆气和聪明才智的。平步青云,谈何容易!”
“可人的胆气和智慧,又都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洪然轩却反唇相讥道“它们却都是经实践一点一滴撷取、积累起来的。我现在就想问问了,倘若,我是说倘若,倘若抹去过去的一切,或说化过去一切为零,而让你从新来过,仍干这一业,你倒说说了,你还能有勇气去做做的吗?”
“也只管去试试的了!“耗儿最后讪讪道。
十四
俗语有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时间总是以它特有的步履,悄悄而急速地流逝着。悄悄者,悄无声息也;极速者,转瞬即逝、回目惊心也。
这一大早的,王凡从遥远的省城一路返还回家后,也无意去补个觉来,或稍息一刻,就来坐于窗前的小书桌边,续接起日前未完结的刻写一些资料的活儿了。
听这钢笔尖划破油印纸的喳喳声,却是一阵一阵,一浪一浪,明快而有节律,清晰而不乏韵味儿;就象有谁正低音弹奏着一首激动亢奋的进行曲。他如此般认真、上心,却是正要去刻印一本《当前棉花生产新技术推广》的小册子,乃是他多次于外地参观、学习的经验的总结;他想将它们刻印装订成册,分发给了大家,以便于大家随时去学习和掌握应用的。
而伴随着这阵阵曲音的勃发与飚升,他面前的钢板油纸之上,也立时显现出了几行明晰而整洁、又刚劲有力的楷体小字。他瞅一眼,不无自得地点点头来,随即又投入于紧张的刻写中,片时眼前已是被翻过去一页,又一页------
忽儿就有一阵轻风缓缓吹过来,挟着初春的料峭寒意泻进小窗,又扑到他双手,扑到他微黑的面庞间。他一下就感受到一种少有的,柔柔绵绵的凉爽和清新,就不由搁住手中笔,复扩扩胸,意欲去饱餐一顿老天大自然的灵臭和光华。可才一抬头,早见有二人前后拾窗前台阶斜步行来。定定睛,却见是耗儿和洪运来。
王凡一时就被弄的有几分糊涂了。瞧这洪运来洪三娃子吧,自那日轰他走离出去后,他王凡却一直都并无有机会,而去与他对上一二句何等的话儿的。哎,这样的货色,不理也罢,不理也罢!——就不知到这眼前了,他却又是咋的啦?瞧这威势不减,二次登门,还劳动了耗儿过来。
思虑厅房中一时没人,就顾不得细揣细想,王他赶忙抽身来迎二人。
“瞧,这果然在家呢,也省得枉跑一遭了。”
耗儿劈头道来,也流露出一时的一份躁然之情。
王凡就含笑道:“枉跑了?这都瞧瞧你说的,象我这地儿就是方冤枉谷了不是,连多来一回都要起报怨的。不知我这儿还省了去挪椅挪凳儿的呢。”说着左右手各递过了一把小木椅上去。
耗儿自知情急语失,赶忙赔笑道:“那里那里,这都说哪里话呀!是我才刚正忙活呢,我三哥说有见你回了,非要粘上我,就要我陪他上你这走一遭来。”
“噢——!”王凡一时却不甚解,瞅瞅耗儿又瞅瞅洪运来:“是运来兄有事儿过来寻我么?”
耗儿就抢前道:“是这样。也没啥很紧要的。他就是念叨着这前些日子,他一时情急,就于你这逞舌逞强了,还耍了手段来,由是心里就过不去,特后悔,说要亲来给你叨叨的,就请饶他这一回了。却是这样吗,三哥哥?”
洪运来见说,就望怀里摸一摸,却摸出来两张拾元钞票:“王凡,那日对不起了。这是我应给的赔偿。”
王凡就道:“事情早过去了,还提它干啥呢。况且,这事我也没放意下的。”
耗儿道:“你是你,他是他呢。你不能就让你去标示你态度,而不许他人来表表曲衷吧。”
王凡道:“这话就重些的。其实大家若肯及时退让一步,互不计较就是了。”
耗儿道:“可姿态归姿态,责任归责任。咱现就废话少说了。你若受下了损失赔偿,就表示大家都得谅解了,通过了,你觉得呢?”
洪运来就上来道:“凡子兄弟,我运来生性鲁莽,又没些学问的,就说不来一句好听些的,但耗儿刚说的,却都是我运来心里话。”
王凡道:“瞧你们说的。——若你俩非欲如此的话,我就受下十元得了;10元。有谁还跟钱有仇呢?
他果就收得十元钱在手,就再也不肯的了。
耗儿见着道:“好了好了,也算大家意思都到了。”
王凡道:“怕都是你的点子吧。”
他就微一笑,转语道:“刚就话跟话,也不及问问了,这一回上省城的事,办的都还顺利吧?”
王凡就道:“够顺利的了,就可能还欠些数量的。”
“欠些数量,却还有解决的门道吗?”
“看看吧,孙教授倒给有个路数的,让我们去找找县里的。”
“教授都发话了,你肯定没问题喽。”
“也不一定的,一层归一层么------”
就见洪运来有不得自在之色,耗儿就道:“这样,我一刻还有事儿呢,这事儿挨晚上过来时,我们再细聊可好?”
王凡道:“我这儿就随时欢迎了!”
谚语云:浪子回头金不换。却说这洪运来经耗儿撺掇,而要亲来王家登门谢过,已是十分不易了。竟不知这洪运来妥事偕耗儿离开王家后,还真象了却得一桩莫大的心事了,满心欢喜,一脸自得的。竟也顾不上去望耗儿道声“谢”,就悠悠晃晃,晃晃悠悠地随路走去了
这要予细说了,其实一如这现实的某些人一样,这洪运来并非生来就偏爱蛮行莽闯,逞性妄为来的。他也曾有想过了,要堂堂正正做个人,做个好人来。他的上人们曾这么诫勉于他,他的家庭也这么要求于他。他上二下三六姐弟,就他一个是男儿,这一大家的希望都在他身上呢。可偏偏,他一个却天分不足不实的:他生来就笨手笨脚笨形容,资质也不甚佳;过七八岁了,还说不出来一句囫囵话,反是连吃喝拉撒也还得要人伺候着,就更别说出去念书,啥啥的。
不过要说他个人真正的悲哀,也不是全在这里面的。头笨手笨、省事嫌迟等的也不是现实中绝无仅有;可他却有一个极好强又极迷信的老娘亲呢。
这女人三胎而得子,本就视如活宝来。极小则不然,及至稍大时刻,对儿子些许弱项,她这里根本不看也不想。直是临了他五、六岁头上,瞧也一直无长进,她才生出些急慌了。可她一不去求医,二不来循教,却悄悄背他出门,去寻某‘仙师’去了。却不知待那老先生观摩一番,却道他虽貌似昏憨,而实有富贵之根,属吉福之像。说将来必成大器的。毋庸说了,这正是那女人所暗暗期待的,闻过自然是深信无疑。也就是打这事之后,她逢人便要说说了,说自己儿子却是薛仁贵再世,是高天里某星宿落胎呢!无需去说了,过去她儿子方方面面不及于人,邻里街坊的各种议论说法都会有的,她却是见不得,有人就于她儿子面前说这到那的。
却也是自此之后,她更拿自己儿子当稀奇宝贝了。若平时在家、或出门玩耍,直至稍省事后入学放学的,都会用专人接送看护。那阵势,真个是‘衔在嘴里却怕溶化了,捏于手心又怕飞走了’。她一心只在默默盼望着,她儿子开顽化愚,訇然出众的那一天,盼望那一天能早些个到来。
也真还可怜可叹了,这女人对儿子的一片良苦用心。而相对于这番情景,这做儿子的这儿,却只是身在福中,一直都并没有很好地去感悟体验一下的。有道是种瓜得瓜,种豆收豆。由此儿子唯是于心中养就了一种优越感、自豪感,这就是人家能有的他尽有,人家都没有的他也有,而且只要是他可意的,他能想得到的,他老娘就没什么不给满足的。那情形,那壮况,仿佛老子天下第一呢。
他这儿却还有一小秘密呢,即是这故事开头所述的,他有个病根啥啥的。其实不尽然的。说这小些时候,他确有这个鬼毛病不假的,但不过十五、六岁时,这病就渐渐断根了;只不知别人都视病如魔、如洪水猛兽,而他于中所体验的,却是一种非常的趣意和欢乐。这却并非纯粹笑言的。因在他那里,一时极小的病痛和极其的被关注、被宠爱,孰轻孰重他却是感受得十足了的。也是在一些无心的挑逗和诱导之下,他开始在一些背逆和不尽如意时候,尝试起那种实可憎的表演了;说白了,他这之后绝多时候的病态,却都是他存心、而装扮出来的------
可想这儿子虽憨些可恶些了,也总得有慢慢开窍的时候的。在懵懵懂懂走过一段人生历程后,这娃子心里忽然就感觉出了某种不足:瞧瞧这洲里与之同龄的的娃儿们,他们一个个或早或迟的,都交有女朋友了,有的还有成下亲了,左右望过了,却就他剩一个是孤雁独身了。或许这以前什么都依赖于老娘,向她伸手习惯了,那日里他突然就逼住他老娘,说是要她赶快给讨一个‘相好’------
这下子让那女人就猛地一下惊醒了。想这许多年来,她都没有盼来儿子大器晚成、出人头地,就总觉他仍是那么娇憨、幼小,琢磨许是时辰未到呢。岂知这年光岁月不饶人,儿子已是二十过半,身子骨壮壮硕硕,是该去给他寻一门亲事了,无论如何的也该去寻一门的;好吃的梨儿挨不过当夜去,过了这一村,怕就寻不出这么个店的了------
当日晚趁着东上的月牙儿还没出头呢,这女人就悄悄出门去了。她要去托人为儿子牵线去。却说托这早年的红运,她一家还能有些人缘的,所以才刚过了数日,就见有几个婆子分头来回话,跟着就要相亲、相亲。哪知这一回却叫这女人大不称意的了。原来她先自暗地里连望几回,所见却不是癣头就是撇嘴,一个个丑人堆里挑拉出来似的。她最后不由将众婆子好骂一阵,都给赶回去了。她能谅知,她们都将其宝贝儿子视做哪般的人了。她可容不了她们,宁愿儿子一刻不娶的。还有呢,她笃信那卜卦先生的话,就寄希望于那个将来。
你等就等着瞧------
这一下只苦着了这为儿的了。其实若仔细说说了,他不过生得笨头笨脑,又省事过迟,缺乏必要的教养罢了(也是那女人等恣意放纵的结果吧)可时至这如今了,他那里却是天鹅肉摊不上,丑鸭儿又不让动的。他心里真是又苦又急,越急越苦,最后竟至于去耍无赖,对同辈女娃儿耍无赖,对路人去耍无赖,有几回还险些闹出事儿来。
可幸可叹了,就有得耗儿洪仁轩等辈高风人士,不嫌不辱,不厌不弃,又总及时耐心地予以纠拨、导引,这娃子才险一步没有误入曲途了。而至这眼下来,这眼下来,他已有发愿之后要行己以礼、以理,知廉耻,做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