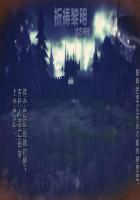一进家门,和站在门口欢迎他们的儿子和小外甥打过招呼,李健直奔卫生间,简单洗漱过,就躺下休息了。
晾在一边的李秋燕忐忑不安,不知道李健是心里不舒服还是身体不舒服,回来的路上几乎没有说话,要么闭着眼睛迷糊要么睁着眼睛远眺,就连晚上吃饭的时候,和肖雨他们说了几句话,也是兴致不高,无精打采的。
李健不是那种眼皮朝上的人,如此反常的对待自己的同事兼朋友,李秋燕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鞭子抽打过,嘴上强颜欢笑,心里却一个劲儿的打着圆场,可能是那天晚上喝了太多的酒,一直头疼,才懒得说话吧?一定是的,唉,但愿是吧。
李秋燕在心里一遍遍地念着"阿弥托佛,菩萨保佑。"
想想事情的始末,真是节外生枝啊,好好的野炊,都怨自己得意忘形,看不出个好赖脸来,非较真不可,那时是哪根筋抽了?肖雨在旁边一个劲儿的使眼色,自己愣是装看不见,现在想起来,真想抽自己一嘴巴子。
逞什么能?在家里说得算说得不算,那都是关上门自己家的事儿,非拿到台面上掰扯,有意义吗?整得李健下不了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汗都下来了,还不住口,嘞嘞个没完,结果就乐极生悲了。
要不是几个人看出李健脸色越来越不对,简单麻溜脆的结束了野炊,改为自由活动,才缓解了当时尴尬不已的局面,要不是阮青山拉着李健躺在藤椅上晒太阳,还不知会怎样收场,要不是,哪来那么些要不是啊?唉,被痛斩蛇精的喜悦冲昏了头脑,得瑟大了,结果就是这么悲催。
李秋燕呆呆地坐在沙发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四处望望,黯然神伤。
儿子和小虎早就嗅出气氛异常,关了房门再没有出来,家里出奇的安静,安静的心里发怵。
卧室里没有开灯,凭看熟悉的感觉就能找到床,找到自己睡觉的地方,只是看不清李健的脸,李秋燕大气不敢出,轻手轻脚地躺了下来。
即使有些冷,也不敢使劲地拽被子,以前不睦的时候,各盖各的被子,后来好成一个人了,也就自然而然地共用了一个被窝,可现在,揣摩不出李健的心事,李秋燕也就不敢造次,拽了被子,盖到哪儿算哪儿吧,冷就冷吧,谁让自己嘴欠?怨自己活该。
瞪着好看的杏核眼,望着黑暗中的天花板,只能看出吸顶灯隐隐的轮廓,直直地望着,李秋燕的脑袋空洞无绪,混乱不清。
怎么可以混到这个份儿上,在自己的家里竟然像个受气小媳妇,先不说别的什么大事,就说盖个被子这样的狗屁小事,都做不了自己的主,天呐,怎么能够沦落到如此地步?
看看现在的自己整天掂量着李健的心事,围着他的屁股转,活脱脱一个黄脸婆,真是的,我李秋燕打从娘胎出来,一直都是脑袋削着尖般不甘人后,到哪儿都是霸王,而今,竟然低眉顺眼做起李健的跟班来了,曾经的潇洒自如呢?难道真得是爱会让人变得卑微吗?是吗?
黑暗中的李秋燕晃了晃脑袋,越想越难受,李健已经打起了鼻鼾,要是平日里,偎着宽厚温暖的臂膀,听着低沉规律的鼾声,李秋燕会睡得香甜踏实,可现在,心里乱糟糟的李秋燕越听越觉得刺耳,越听越觉得烦躁,也越听越觉得孤单。
后悔,后悔,还是后悔,李秋燕恨不能缝上自己的嘴,口无遮拦,祸从口出,不就是用来说自己的吗?
李秋燕无法安眠。
其实,李健对待李秋燕没有变化过,
还是那个宠着爱着她的丈夫,只是因为贪了杯,加之近日血压不稳定,头疼头晕,胸闷气短,本想躺在房间里休息下,可是已经定好的事儿,不好扫了大家伙的兴,于是,硬着头皮参加了野炊。
虽说李秋燕确实过份,口不择言,挑她的理儿也很正常,可是惯着李秋燕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李健觉得没有和她计较的必要,何况还是在大家伙面前,夫妻之间的事私下里解决好了,就没有分辨什么。
望着一桌子的农家饭菜,却没有胃口,很难受很难受,想立即躺下缓缓,又怕大家伙担心,想到已经吃了药,应该没什么大碍,于是,就忍着,忍着,一直忍到回家。
进了家门,一下子卸去了伪装,一下子没了力气,李健只有一个念头,睡觉,睡觉,赶紧睡觉。
只是这些李秋燕都不知道,粗心的她更不知道李健不告诉她实情,是怕她担心,也怕影响了大家伙的情绪。
李秋燕还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恼恨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