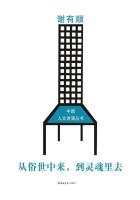黑色的房间里坐着一个女孩,散乱的头发披在腰间,她蜷曲身子望着窗外的点点繁星,嘴角的抽搐间落下了几滴晶莹的泪珠,不知为何,每晚夜里她总会有一个梦,一个少年拉着她走到一片墨绿的森林,森林里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指引着她走到了尽头,梦的天空繁星闪烁,森林的尽头只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骤然狂风卷起,沙漠中屹立着一棵高大的玫瑰树,少年走向前,为她摘下了唯一一朵玫瑰,娇艳而妩媚,她笑了,如同一个天使,但是迎来的却是玫瑰的凋谢。
花瓣落在她的脚尖,染红了她的脚趾,染红了金黄的世界,玫瑰隐藏了它的芬芳随之而来血的腥臭,荒漠盛开了腥红色的玫瑰花,弥漫着血的腥臭,她手中的玫瑰落尽了花瓣留下了一把光秃秃的匕首,上面印上了诡异的花纹,少年紧紧握住她冰凉的手,用她手中的匕首刺进了她的心脏。
我好害怕——
第二天。早上
清晨的阳光伴着雨露在窗台的蔷薇上舞蹈,韩苑苑梳理着她散乱的头发,垂着头努力不看窗前的自己,已经第4天了,夜里的每次惊醒让她睡不好觉,眼边的黑眼圈更深了,与她大大的眼睛成了对比。
咚咚咚。
古木的房门被敲响,低沉的声响在硕大的房间里起了回音,檀木的香味在房间里飘散,欧式的房间装饰让一个简单单的卧室变得温暖而又冰冷,青铜色的窗帘半掩着,细腻的阳光只能奔跑在房间仅有的角落,低沉的世界被敲门声唤醒。
苑苑换好校服打开了房门,门口站着的是斜背挎包的安苒,从小到大安苒一直是苑苑无话不谈的闺蜜,两人的性格相同,做事情大大咧咧,但对于苑苑安苒一直很细心,关注她许多不愉快,陪她哭陪她笑,就像她早已离世的妈妈一样照顾她。但高中以后苑苑变得沉默了,不再是光着脚丫雨中乱跑的丫头,开始逃避人群的一切,安苒很不理解,苑苑也不愿意对她说原因,两人的关系才渐渐疏远了。
“苑苑,你收拾好了吗?大巴车都来了。”安苒轻轻地说,仿佛手心里捧着一个玻璃杯,生怕她受一点伤破碎。
“收拾好了,我们走吧。”苑苑出乎意料地回了她大大而又灿烂的笑容,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语气不自然的轻快。
“苑苑你要是不想参加也不要勉强,这次的春游是去罗衫森林野餐的,我知道你很讨厌.......”
“苒苒走吧不要让大家等急了。”苑苑不等安苒话说完就拉着她的手离开了宿舍。
可能是安苒的错觉,她感受到这只及握住她的手冰凉,在微微颤抖,而苑苑的眼神注视着前方,眼瞳不断的紧缩,感觉像是在上一场不可能回归的战场,苑苑,你到底怎么了,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汽车的轰鸣伴杂着学生们的欢笑,聊天的声音丝毫没有打扰韩苑苑紧闭的双眸,她靠在僵硬的扶手上,身体微侧神态安详,以致所有人都认为她在睡觉。除了安苒。
什么时候,你开始了对自己的伪装,披上了黑色的外套,难道你要一直瞒着我吗?
苑苑洁白的脸庞上的惊恐,心里的脆弱到底是谁赋予的?
我不明白。
汽车行驶了一个小时才慢慢停下来,天空也慢慢变成了灰色,原本多彩的天际被几朵乌云污染,细雨蒙蒙的打在了车窗让,像泪水一样滑落在地上,冰冷的季节封印了她的笑容,她被怎样的乌云染成了捉摸不透的黑色,让别人走出她的世界。
韩苑苑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目光呆滞的望着她,她感受到了自己内心的恐惧,对森林,对黑暗,对死亡。
苑苑的嘴角上扬了浅浅的弧度,泪水悄无声息的划过,沿着泪痕消失了。她不可以告诉安苒她的一切,为什么会性格大变,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她甚至不敢与她说话,因为不知道那一天她会变成吃人的野兽,或者和妈妈一样被魔鬼杀害。至少在那一天到来之时,她唯一牵挂的人不会受伤。
她,就是吸血鬼。
终点站。
司机打开了门,同学们一窝蜂的涌下车,几位年轻的老师慌忙的维持秩序,车内拥挤着,却与安苒的心境成反比例,一路上,安苒一直在胡思乱想:苑苑该不会失恋了?被男友甩了?(外加脑补韩剧狗血剧情)
“喂!苒苒走了。“苑苑推了推出神的安苒。
”哦哦,去哪?“安苒回过神。
看着苑苑一脸看白痴的样子,安苒尴尬的笑笑,不好意思地摸摸头”这么快就到啦?哈哈哈..........“
罗衫森林
冰凉的雨滴打在雨伞上,滴滴答答的,轻快的响声是墨绿与灰色世界唯一的闪光点,导游举着小旗子带领着小队伍走在森林里的羊肠小路上。
”罗衫森林属于半人工半原始的杉树林森林,虽然是杉树林但是其中混杂的树木高达300种,许多反季节的树木也会在罗衫森林里面盛开出美丽的花朵,自然学家认为这与罗衫森林所处的地形有关,但是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说罗衫之所以百树齐长,是与罗衫的土有关,传说3000年前这里有一场残忍的屠杀,爱修罗正义之神与大祭司黑暗女神在这里为了权位在这里疯狂的杀戮,死伤无数,鲜血染红了整片森林,每一位死去的人带着仇恨与悲哀用自己的血洒在了自己脚下的土地上,用自己仅有的力量反抗着所谓的正义与邪恶,终于他们的血唤醒了他们的救世主卡萨帝爵,他的出现改变了这里的一切,用自己与人们的力量封印了爱修罗与大祭司,让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化成了罗衫的土地守护着这里的一山一木......“导游拿着话筒讲述着凄惨的故事。
苑苑冷笑着,她对转过头对着故事着了迷的安苒,用轻蔑的语气说到:
”所谓的正义,在权利面前也不过是一张躯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