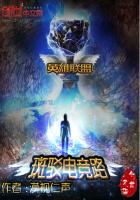自那日以后,陆翊充分发挥京都纨绔死缠烂打的本事,整日里跟在媚娘身边嬉皮笑脸,比吃饭睡觉还要殷勤。
饶是早知计划的媚娘,也不厌其烦,更何况是旁人。几个不知情的,把状告到了白若梨那里。
宁静午后,白若梨正在竹林静坐,给几个弟子讲她这些年的经历。
桃花坐在离她很近的地方,正在纸上快速写着什么。她是来为师父记录的。
白若梨已经记不起父母的长相了,她害怕有一天会连这些徒弟和那些曾经历过的事也忘了,所以找了偶尔会给说书先生写故事的桃花来帮忙记录下来她的生平。
水爱爱坐在她的对面鼓琴,用的是她那把最爱的小叶紫檀七弦琴,弹的是她新编的曲子,轻缓柔和,适合回忆。
林轻尘被桃花揪住,正在画白若梨记忆里的那些人,桃花打算把它们放在她写的师父的故事里做插画。
至于夏木生,他正望着手上的戒指发呆。
白若梨正讲到在凉川小叶夫人提了八宝宫灯亲自为她送行,语气里不禁揉进了几缕可惜。
她鲜少还能回忆起以前那些人的衣着和打扮,可是这个蜃妖的穿着,她记得一丝都不差。
几个弟子都有些吃惊,但最后却只有桃花嘀咕了一句,“能被师父记得这般清楚,也是不容易啊!”
焦海棠急匆匆跑过来,地上是经年累月的竹叶,她踩在上面发出凌乱的脚步声,打乱了原本宁静祥和的琴声。人还未等,抱怨的声音就已经传了过来,“师父!你把那姓陆的赶走吧!”
话音落,人已经来到了面前。
往日里,焦海棠总是笑着,一身的鹅黄或粉红,整个人散发出一种青春的活力。
可是今日,她只套了屠胭脂的一件灰色袍子,发丝凌乱,面色憔悴,脸上也是一副愁云惨淡的表情。
焦海棠几时把自己弄的这般狼狈过,桃花有些想笑,但还是厚道的忍住了,只是放下了笔,问道,“焦师姐这是怎么了?斯年哪里惹到你了?”
焦海棠看着她带笑的眉眼,就觉得她在嘲笑自己,于是口气很不好地冲她去了,“我差点就给忘了,那个姓陆的是你的朋友吧?你把他带到庄里来,现在也该把他带走了!”
他又不是货物,什么带来带走的?桃花不喜欢别人这样说陆翊,故而说出的话也有些阴阳怪气,“焦师姐这是安的什么心?人家说远来是客,哪有把客人往外推的道理啊!师父还在这里呢,哪里需要你来发号施令了?”
“我安的什么心?”焦海棠把眉毛一挑,竟然带上了凶煞之气,“这话我倒要问问师妹你了,你是安的什么心?这姓陆的都干了什么好事?整日里斗鸡走狗,是京都出了名的纨绔。你把他带回来,是嫌庄里不够乌烟瘴气吗?”
“乌烟瘴气?焦师姐真会说笑。乌烟瘴气也没见哪个被熏死啊!”
“你自己说说,自他来了这庄上,可曾办过一件好事?整日里跟在大师姐身后,不知道还以为是师姐养的哈巴狗呢!”
“什么哈巴狗?都是斯文人,怎么说话这般难听?人家那叫爱情!”
“狗屁的爱情!大师姐早就不厌其烦了,若不是还顾及着那是你的朋友,都不用我出面,大师姐也会把他赶出去。可是他倒好,没脸没皮的,人家烦他,他还上赶子往上贴!”
“大师姐不也没说什么嘛,焦师姐这是操的什么心?”
“今天晌午更是过分,我们都在睡觉,他倒好,在那就唱上了!就那声音,比泗水城城外的冤魂齐鸣还要难听百倍。他还满口的污言秽语,情情爱爱全都挂在嘴上!当这里是什么地方?若是平日里,我也就不管了,可我和姐姐刚从泗水城回来,抢救决堤的泗水河三天三夜没有合眼。这厢刚睡下,就给我们听这个?”
“什么污言秽语啊,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家那叫,窈窕淑女,女子好逑!”
“君子?就他还君子?我呸!那姓陆的就是一个登徒子,也配喜欢大师姐?”
“怎么不算君子?要我说啊,起码斯年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他既不是个断袖,怎么就不能追求大师姐呢?”
焦海棠目光一寒,就连水爱爱也在看不见的地方握了握拳头。
桃花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犯了众怒,但接触到夏木生投射过来的犀利目光,她还是硬着头皮继续说道,“要我说啊,大师姐生的貌美,身份尊贵又法术高强,端庄贤淑还温柔大方,怎么就不能有人喜欢了?今儿个这是斯年,明儿个指不定就是什么张翊赵翊了!你能赶走这一个,还能把所有人都赶走不成?”
焦海棠默了一下,虽然她依旧觉得陆翊很是不靠谱,可她不得不承认,大师姐一个人真的好多年了。既然夏木生无意,总归是要再找一个的。
焦海棠看的出来,大师姐虽说是不大看得上那姓陆的,可姓陆的大献殷勤的时候也没看到大师姐拒绝啊。她觉得,大师姐对那姓陆的或许也并不是完全无意。
焦海棠沉默了,桃花可就来劲了,“前儿个斯年同我说,大师姐送了他一个香囊,想让我帮着看看选个什么东西做回礼。这我哪知道啊?大师姐喜欢的东西,除了她自己,也就师父和夏师兄了解。对啦,夏师兄,你说,他送个什么好呢?”
夏木生腾的站了起来,没有回答桃花问的话,转身就走。
愤怒和嫉妒燃烧了他的理智,他没空去想媚娘为什么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他只知道她送了自己香囊如今又送了别人!
他不再是她心里的唯一!这个念头一经升起就压也压不下去。他需要亲自过去,当着她的面,问个清楚,她的心意真的轻易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