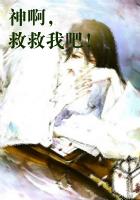砰!一声铳响。
“嗨!”擂台手列队站在神公石像旁。
砰!二声铳响。
“嗨!”擂台手喊出了“尚武德,保家园!”威武的口号。
砰!三声铳响。
“嗨!”擂台手齐齐围住了杨幺石像。
待得众人点燃香烛,供起祭礼,一座大坪塌香烟满了炉,烛火成了行,映得杨幺的神公也在烟气氤氲中散发出几分神气来,那个中年道士便扯开了嗓子:
“拜——神——公——”
杨二爷领头,众人一齐拜倒,先行了三叩大礼。
“诵——祭——文——”
主祭的戴二狗便起了身,立到杨神公像侧,展开祭文,朗声而诵:
“风流已去慨然长嗟,杨公英魄安在否?壮士悲歌未彻。烈酒豪情洒长空,狼烟举,沅水狼烟连角起,长庾当空,贼人当道又猖獗。沅水车船,霄汉豪气,欲换天河,当洗昏朝无数膏血。系甲胄,握长槊,摇橹蹄急征战迫,三尺清锋朝天阕。狂潮风急,战旗欲撕裂。急流碎石,怒涛卷霜雪。马惨嘶,人凄鸣,刀戈散落,弥漫荆楚淋漓血,血流成河。无奈东流水,几场风潮,共韶光憔悴,无限江山,杨公虽殁,英名长辞。”
众人便向神公再行三叩大礼,起身,神情虔诚至极。
中年道士便喊:“祭——水——神——”
为何要祭水神呢?
杨幺当年与宋朝朝廷对抗,主要得益于水中作战,启动车船,所向无敌,据说是得益于水神,杨幺每次开战前都要祭水神,水神能保佑杨幺旗开得胜。
这祭水神本有大讲究,那都是千年来代代传下来的辞颂,祭辞要威要猛要喊出气势,唤来世人崇仰的好汉英雄或八方神之威灵助威,才能唤得杨幺的忠魂醒,请得来助战的水神。。
领头赞礼的是乌云寨的后生伢杨晓军,杨晓军请的是五虎上将,便见他扯嗓门吼将出来,坪塌内坪塌外,众后生伢齐声应和:
“一根神公香木雕,三国英雄算马超。忠义两全关胡子,黄忠宝刀永不老。
“张飞喝断当阳桥,子龙救主逞英豪。五虎上将全请到,杨幺祖公本领高,一声炮响神出水,我划神橹船前飙——
几百个后生伢几百个嗓子汇作一处,粗犷雄壮地吼声,直震屋瓦,仿佛整座大坪塌都要在吼声中摇晃起来!
吼声之中,也不知是声音带起的,还是果真惊动了杨幺的神气,一股子荡荡之风便蓦然鼓入,吹得满坪塌烛火乱摇,烟腾雾起,吹出杨幺神像的浩然正气。
中年道士看神灵已显,便喊起了祭神公的最后一项:“挂——彩——”
戴二狗将一只早就备下的公鸡被一刀割断了颈,鸡血注入瓷碗内。
秦高凡摘下纱布巾,拜倒在杨二爷面前,高举起神公:“有请先生挂彩”
杨二爷提笔蘸上鸡血,神情凝重往上往纱巾上点了一下。
接着,其他的后生仔也依次摘下纱巾,请杨二爷挂彩。
据说,只要往头巾上点了彩,杨祖公就会降神力给他,保佑点彩的后生伢在擂台赛中至极发挥英武神功,如鱼得水地打完擂台赛。
一会儿后,戴二狗扯高了嗓子喊道:
“开——擂——台——”
接着,两个擂台手跳上擂台边拉开了红布帘幕,红彤彤的擂台露在了观众的眼里。此时,那些后生伢就手拿兵器,开通了道路,杨二爷就跨步向擂台下面的座位边走去。
王汉山他们真真切切感受到这个杨二爷着实了不得,一大堆本地乡绅、老板,外加十个寨子的寨首,个个人模人样看起来不是小角色,但站到他面前,却低眉顺眼,一个个大气不敢多透一口。
王汉山觉得面前是位真正的土地爷爷,提醒自己要恭敬礼让时刻多矮三分,见杨二爷客客气气请自己落座,他又礼让一番。但杨二爷素来礼仪规矩看得重,王汉山等人可是先生,哪有不先敬师的道理?杨二爷先不由分说,硬将王汉山按在座位上,这才四平八稳,在台正中的椅子上坐下。
杨二爷回头指起几张空椅子,就招呼着众人:“各位,坐呀坐呀。”
几个有资格靠前坐的乡绅就互相推让起来,就纷纷地讲您先请您先请,讲杨二爷身边哪是我坐的地方,我坐后头,您老年纪大,您老坐才是道理,您是杨二爷的本家本族,您坐才对喽……
正在这般客套推让得好像进了君子国,人群后头,却嘶哑哑钻进来一个声音:
“哎哟,都讲斯文啊?那,就便宜我这个不斯文地坐坐吧。”
几双手臂粗狠狠把乡绅们两边一扒,四个腰挎短枪后生伢蛮横地分开了路。
一个瘦干干矮矬矬孤傲地老人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踏着稳健的步子,大模大样走上来,一屁股就坐在了杨二爷右手边的空椅子上。
王汉山就看到身边的乡绅、寨首们悚然变色,看到几个挨得近的掌柜吓得当时就往后缩,看到杨二爷身边几个舵子兵伸手就按住了枪,看到一座台上好像突然撞邪闹了鬼,一下子吓心吓胆,人人屏气!
连杨二爷的眉心都压不住一跳!
“秦大扛把子?”
干瘦老人手一拱:“杨二爷。”
王汉山虽不晓得来的是个什么角色,但只要没瞎了眼睛都看得出,这干瘦老人来者不善。
杨二爷倒是飞快地恢复了平静,笑吟吟拱手还礼:“今天这是什么风,居然把秦大扛把子吹来了?”
秦大扛把子也满脸笑:“三月二十八,刮南风嘛。”
杨二爷就摆起一脸地惊讶:“秦人寨的人不是不问世事吗,南风刮得秦爷动,倒也怪了。”
秦大扛把子讲:“我才是桃花源里真正的主人,我秦大扛把子当然要来!”
杨二爷的脸上就起了红晕,显得极为尴尬地说道:“秦大扛把子莫非想坐坐总寨主的位置,如果你要坐,我就走开!”
秦大扛把子就哈哈笑:“杨二爷,多虑了哟——三州六府、远近百里,长了耳朵的哪个不晓得,你杨二爷才是这里的地头,您算山里土地爷,我是缩头乌龟,但缩头乌龟也要晒晒太阳。”
“你喜欢,晒就是。”杨二爷这才收了笑,“却不知大扛把子大驾光临,有什么贵干?”
“当观众。”
“当观众?”
“没错。不瞒杨二爷,我秦某的伢崽今年满十八,我是专门带他到桃花庵来当打擂台的。”
杨二爷就问:“却不知令公子是哪位才俊啊?”
“杨二爷已经见过了。”
秦大扛把子把手往前排一指:“看到没得,最前那个站着的扎纱布巾的,背上背着刀鞘的,就是我的伢崽。”
“哦,是吧?”杨二爷就讲,“果然是英气逼人呀。”
“用不着,我养的伢崽,我晓得。”秦大扛把子口气硬邦邦。
两双眼珠就相互对起看,两张脸就相互对起笑,笑得那么客客气气,假惺惺好像眼睛里头却装了根刺。
王汉山都呆成了一桩木偶,揣摩他们讲话为何这般口气,只觉得有盆冰水浇下来,浇得他心里激灵灵地一抖,浇得他的木脑壳里什么都清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