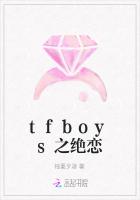午后,早晨还叫得欢快的蝉伏在树上,有气无力地喊一声不喊一声。阿黄四肢摊开趴在门前那棵苦柚树下,伸长了舌头装死。
“阿黄,阿黄!”朱富贵喊了两声,阿黄脑袋动了动,没有起身。
“你这只懒狗,懒死算了!”朱富贵又骂了两声,阿黄睁开眼皮瞅了瞅朱扒皮,扒拉着挪了个位置,将肚皮贴在更凉快的地方,又闭上眼睛一动不动。
天似蒸笼,笼盖四野。黏腻的闷热裹在人身上,浑身上下都不舒服。那乌云又压下一点,这会儿连气都透不过气来了,人比狗还难受。
朱富贵瞅了阿黄两眼,兀自也消停了,从柜台后摸了把蒲扇摇着,肥大的身躯窝在凉椅里,张着嘴喘了几口粗气,热气依然不能消散。眼前的八仙桌上就有个陶壶,里面装满了凉茶,伸手可得,朱富贵望着陶壶舔了舔嘴皮子,面上浮现出心满意足。
日头不知何时躲进了厚厚的云里,知了闭了嘴,阿黄的每一根毛发都须张着,在热络的空气里微微颤动。
富贵茶馆的两个伙计——肖五娃和赵六毛无精打采地倚在门边,两人都敞着领子,全身上下的每一根汗毛都竖立着,一滴汗都没有——都让这破天气闷干了。
肖五娃才十五六岁,赵六毛却三十好几了。按辈分,肖五娃要管赵六毛叫六叔,不过,他却常常口呼老六哥,赵六毛也不计较。赵六毛上面原本有五个姊姊,他爹非要生个儿子,家里又养不活这么多人,于是他爹就在生他之前把二囡到五囡都送了人,只留下可以帮衬活计的大囡和婆娘肚子里的老六。巧不巧,赵六毛的爹就叫老铁,大家都说赵老铁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生个男娃。待到十月临盆,赵老铁的婆娘果然生了个带把儿的,赵老铁高兴得敲锣打鼓,逢人就说:“瞧,我有儿子了!”
然而才过了半年光景,老天闹起了饥荒,赵老铁的婆娘身子亏,没熬过去。赵老铁瞧着襁褓里的老六,狠心把大囡卖给邻县的吴大户做妾,换了点米粮和薄钱。那吴大户年近花甲,仗着家里有几分田产,趁着这灾年想捞一把,几斗糙米就娶了个黄花大闺女,他当然高兴得很。大囡嫁过去每日受大太太的气不说,还要做工、倒尿盆洗衣裳,伺候完吴大户还得给一屋老小做饭。
人老了,那活儿自然也不中用,吴大户的三儿子瞧中了大囡的资色,暗地里霸王硬上弓占有了大囡。大囡晓得胳膊拗不过大腿,她不敢吱声,只得忍受着一切。日子一长,大囡有了,大太太这下不干了,咬定大囡偷了男人,吴大户的三儿子跳出来说看见大囡偷了长工,大囡气不过,喊来村中的徐员外为她主持公道,当着全村人的面吐出吴家父子的丑恶嘴脸后跳井自尽,一尸两命。赵老铁知道后自然不依,但人已经死了,再闹也无益,徐员外就做好人由吴家赔了赵老铁五吊钱,此事就这样了了。因为这档子不好的事儿,吴家的名声也渐渐败了下去,不久就举家搬迁到了别处。
赵老铁婆娘那边姓朱,有房堂哥姓朱名进财,家中略有薄产,好歹不歹开了个茶馆,还能糊糊口,瞧着妹婿可怜,便好心将赵老铁收来跑堂做粗活,还能均两口米汤给赵家的六娃,不过朱进财的独子朱富贵却自小就与赵六毛不对眼。
朱进财是个本分人,临死前交待儿子不得把赵家父子赶出去,朱富贵嗯嗯应了,老爹一死就把茶馆改了名儿——富贵茶馆,瞧,多气派!亏得他还有几分良知,没把赵家父子赶出去,不过赵老铁也快死了,朱富贵拎着一壶茶水去村尾看了看,还假惺惺地掉了几滴泪。
赵老铁虽然混沌了一辈子,但他还是一把屎一把尿把六毛拉扯大,有饭先给六毛吃,有水也先给六毛喝,幸好赵六毛知道他爹的好。赵家本来就家徒四壁,赵六毛把能当的都当了,好生葬了爹爹,每日天还没亮就去富贵茶馆开门打扫煮水迎客,每日半夜才回到自己的破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哪家的女娃看得上他,他也逐渐断了这分念想。
“呵——”肖五娃提提领口,指望扇点风出来,没想到这下更烦躁了。他瞅着苦柚树下起卷的地皮喃喃道:“再这么热下去,土地公公都要跳河了!”
“哗啦——”
“咚!”
“哗啦——”
富贵茶馆的后院里传来打水的声音,肖五娃听在耳里仿佛天籁。他忍不住朝赵六毛使使眼色,示意他去后院看看,赵六毛却跟没看到一样不动,肖五娃小声啐了一口,暗暗在肚子里骂道:“没用的东西,难怪讨不到婆娘!”
朱富贵似乎听到了肖五娃的诽谤,眼睛斜斜瞟了肖五娃一眼,肖五娃立即从地上弹起来,拍拍屁股大声道:“掌柜有何吩咐?”
“把桌子好生擦干净,一会儿就有人来了!”
“诶!”肖五娃欣喜地就往后院冲,朱富贵喊道:“回来!”
“掌柜的还有什么交待?”
“随便擦擦就行,昨儿才洗过,不用打水,啊!”
肖五娃好像遭霜打的茄子,瞬间就蔫了下来,在朱富贵两只圆溜溜的眼珠子的注视下极不情愿地走到桌旁,这里抹抹,那里擦擦,朱扒皮扬着头道:“擦干净,别留灰!”
“嗯!”
瞧着肖五娃的样子朱富贵觉得心里畅快了一点,不过嘴里的干燥却又令他心烦起来。死小子,偷懒不说还害他说了这么多话,看来不得不喝一口了,他又喊道:“老六——”
赵六毛应道:“老爷!”
“王大善人快到了,去烧壶热茶!”
“是!”赵六毛提起茶壶走向后院,肖五娃眼里闪烁着嫉妒。死朱富贵,死朱扒皮,死铁公鸡,一桶井水都舍不得!等老子发达了,老子也要盖一座这样的茶馆!老子要挖两口井,屋前一口屋后一口!屋前那口搞个栅子拦住,只要喊老子一声老爷老子就给他一桶水!
“咚!”
水桶掉进井里的声音是那么好听——
“哗啦——”
肖五娃想起朱扒皮的肥婆娘坐在澡盆里把水倒在身上的情形,心底更觉得燥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