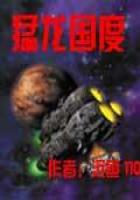郭五儿立在皇帝身旁,一只半透明的白蚕从他指尖爬到肩头,接着迅速膨胀身体,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只听“啵”的一声,白蚕肚子破裂,一缕青烟喷出。五儿深深吸气,将白蚕喷出的烟雾吸入鼻子,然后轻轻打个喷嚏。
“五儿,又有什么消息么?”皇上身穿月白纱绸睡袍,趴在龙案上看奏折,他的脸越发红润了,脂膏累积,膘肥体健,身子圆滚滚仿佛吃饱的蚕。
“皇上,落沙海王老虎有个儿子并没有死,上回侥幸逃脱,臣接到消息,这小子现在三秦州,与三弓、页尔等匪徒皆有勾结。”
“王老虎?你说王爱卿?说实话,朕不讨厌这老头儿,他死得也有些憋屈,不过……你说他儿子勾结匪徒?是否属实?若只是小打小闹,就任他去吧,也算给他老王家留个独苗。”
五儿道:“皇上,王老虎在朝廷内外都颇有势力,他儿子尚存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如果放任不管的话,怕别有居心之人利用他造反,而皇上威信必失、纲纪必弛。前后态度不一,亦非人君之道,望陛下三思。”
皇帝在龙椅上磨了磨屁股,纱绸质地透凉,屁股很舒服,他将精力集中在尊臀上,问道:“你的意思?”
“斩草除根!”
“也罢,还是你考虑周全,就这么定!”
皇帝翻了翻剩下的奏章,一面问五儿道:“朕让你寻得人怎样了?”
“已办妥,臣来之前刚将人送到陛下内寝。”
听得此言,皇帝龙颜大悦,对五儿神秘地挤挤眼,连声称好不停。
“好,好,好!好个仙家洞府!”
太一山的清晨让人神清气爽,王寂惺听到叫好声,推开房门,湿润而新鲜的山风顿时将他包围,同时将他包围的还有阿赖耶和羊刃。吃罢早饭,二人便把王寂惺拉住,让他跟着回页尔山。
“我与葵公子那娃娃订了约,只要你回去,页尔山头领的位置就是你的!”阿赖耶眉飞色舞,道不尽页尔山的好处。
王寂惺不明所以,被说得摸不着头脑。
“什么头领?什么位置?跟我哪门子关系?”
羊刃站着不说话,阿赖耶笑道:“好事好事!我来问你,你想不想报仇?想不想为罹难的亲人讨回公道?又想不想为薛月雪恨?”
“当然想!”
“那我问你,朝廷何其强大?三弓山何其蛮横?你一个人能做什么?俗话说‘墙倒众人推’,朝廷虽然腐朽,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力尚在。三弓山更是蒸蒸日上,门徒遍布,非个人所能抗衡。兵法有云‘借势’,若要达成目的,必须借人之势,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别摆出一副嗤之以鼻的样子,你老弟能有二十多年锦衣玉食的生活,还不是借你爹的‘势’!”
这话触动王寂惺的心弦,他突然伤感起来,莫名的有些厌恶自己,说到底,自己也是个寄生虫。
“页尔山头领又是怎么回事?”
羊刃本待发言,却被阿赖耶止住。
“寂惺兄弟,页尔山有意招徕你,这是个很好的机会,页尔山的‘势’乃是‘天下大势’,你若能主导之,必能澄清寰宇,重现盛世!”
王寂惺想了想,问道:“葵公子给你灌了多少黄汤?”
阿赖耶大笑:“来而不往非礼也,她给酒,我给人。”
“先生莫要玩笑!”王寂惺摇摇头,转身走开。
“站住!”羊刃黑着脸喊道,“既然头领决定了让你来接任,那你就必须服从!”
“无稽之谈!”
三人正争论不休,前边忽然有小道士高喊着跑过。
“山匪来啦!山匪来啦!”
众人惊疑不定,匆匆出门查看。
原来,今日清早,一队衣甲执兵的人马从山道走上太一宫来,约莫六七十人,步步逼近。为首的戴着长耳毡帽,蓄了鼠须,正是郭师爷。郭师爷因办事不力,被罗军师狠狠数落,于是瞒着罗文正,独自揽下“夺取”太一山的差事,想要将功折过。这日汇集了江州牧属下的官差,郭师爷领着一纸官文,就朝太一山进发。走到半路,心里打起了鼓,不知道王仙儿等厉害人物会不会在山上,万一又遇见可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自己手里攥着朱印官文,数十人的官差老爷跟随,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对方再厉害怕也要对官府忌惮三分,况且己方人多势众,胜算颇大。
郭师爷暗自满意,心中充斥义愤与激动,一群人浩浩荡荡踏上山来,但见龙蛇逶迤,甲光映日。
王仙儿和木下三郎站在上山石径的末路赏景,往下张望,不想一眼便看到郭师爷蜡黄色的“狗头”,郭师爷也正好瞧见了王仙儿二人。
师爷忙止住队伍,对领头的官差讲述山头那对男女如何的有手段,竟反倒惹毛了官差大爷,激怒了鲁莽小蒋,数十人非但不听劝阻,反而加速迎上。郭师爷暗自叫苦,心里紧张起来。
王仙儿柳眉倒竖,高声质问郭师爷:“你这狗头,又来送死怎的!”
木下三郎露出诡谲的笑容,直勾勾盯着郭师爷。
郭师爷顿时有些蔫儿了,支支吾吾答道:“官军——官军晨练,尔等莫惊!”
那官差的头儿虎背熊腰,满脸胡子,粗声粗气道:“你们两个男女,和那帮道士一伙儿的么?若只是暂住的香客,速速离去,不要妨碍爷们办差!”
郭师爷抹了一把冷汗,躲到人后去了。
三郎轻轻抚摸才长出的胡茬,对王仙儿道:“这群臭男人,简直就像一堆马粪!老远就闻到一股味儿!”
三郎又道:“官爷,我夫妻俩是实实在在的‘相克’,特来此山求个解法,众将骤至,不吉,宜速归,莫扰我夫妻清静,晚恐不保!”
众差拨面面相觑,没听明白,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相互簇拥着涌上去。王仙儿听三郎胡言乱语,心中恼怒,本想给他几耳光,不过箭在弦上,只有强忍作罢。
郭师爷在人群里抖出那一纸官文,指着鲜红的官印子,理直气壮叫嚣:“州牧手令,太一山道士经年盘踞山头,聚众烧香,为害一方,近日众道大闹州县,损毁州牧府,残害百姓,目无王法,气焰愈发嚣张,为重振纲纪,特命巡捕厅缉拿要犯,其余众道一概遣散,太一山地产房产收归官府,此令!”
老老小小的道爷远远听见郭师爷兴奋的朗诵,都开始慌张起来,小的团团乱转,老的急急寻找住持道长。
三郎微微一笑,突然不见了身影,树丛晃动几下,他又回到王仙儿身边。
“黄脸狗头,你拿的什么手令?还会动咧!”
郭师爷只觉得手里滑溜溜、冷冰冰的,侧目一看,几乎魂飞天外,原来手中官文不知何时变作一条斑斓毒蛇,正吐着鲜红的信子。郭师爷大叫着将毒蛇甩开,一旁的官差挥刀将其斩断,血液溅了一地。
三郎拿着江州牧的手令,瞧了瞧,叹道:“这笔意倒有二王的风范,但这心意却如蔡京般歹毒。”随手撕碎了,抛下山谷。
众差官气急败坏,嚷骂不绝,纷纷抽刀挺矛,冲向太一宫。
“好大的胆子!敢袭击官差,不想活了么!反抗之人,格杀勿论!”
王仙儿冷冷笑道:“狗腿子好大的官威!”
木下三郎于官差中往来穿梭,动手戏弄,而王仙儿真的动起刀剑来。巡捕厅的走狗武艺低下,仗着人多,把二人团团围住。郭师爷机警地躲到最外围。
青姑子道长闻讯而来,慌忙劝阻,可哪里止得住这一窝子虎狼猛兽,太一宫门前真如炸开了锅,千百年来,未尝如此热闹。
王仙儿的剑已染上鲜血,她杀得兴起,三郎亦玩得愉快。
济苍先生和海潮奔出大门,目睹此景,神色凝重。
刘济苍的头发胡须似乎更加白了,几日之间便显苍老许多。
郭师爷猥琐的样子引起老先生的注意。
“郭耗子!”济苍先生语调铿锵,“你三弓山又来捣什么乱!”
郭师爷斜睃着说道:“有幸拜会前教主!没想到便是你老先生!”
“玉莲教有你这样的人,简直是耻辱!”
郭师爷拉了拉长耳毡帽,露出黑黑的门牙,骂了声:“老古董!”
木下三郎拿着把小刀,专拣有胡子的官差下手,硬是将对方浓密的胡子齐齐刮去一半。
“娘子,你且歇息,让三郎我来处理这堆‘马粪’,别脏污了你的手!”
王仙儿充耳不闻。
济苍先生神色严峻,胸口发闷,跺跺脚,径直扑向郭师爷,伸手要抓他。郭师爷瞧科,不慌不忙打出一枚暗器,击中济苍先生小腹。老先生闷哼倒地,顷刻嘴唇乌青。
海潮大惊:“暗器有毒!”
木下三郎见起了变故,立刻钻出人群,来到老先生跟前。济苍先生意识尚明,指示三郎带他回客房取药。三郎回头看王仙儿处于上风,于是抱起济苍先生进了太一宫里间。
三郎一走,官差精神大震,齐声呐喊,猛扑而上。有十数人闯入太一宫大殿,肆意打砸,见老道士就抓,吓得修仙真人们作鸟兽散。
王寂惺、阿赖耶和羊刃三人刚从里面走出,先是木下三郎背着人闪电般飞过,接着就有差役模样的暴徒冲杀而来。
羊刃直接上手,先干翻两人,刚才憋的一肚子气全撒在这两个倒霉鬼身上。阿赖耶见两位官差老爷被打得鼻血横流、涕唾飞溅,仿佛脸上开了酱料铺一般。
“羊兄弟,够了够了,再打就不成形啦!”阿赖耶“好意”相劝。
海潮被裹挟进来,小光头已被敲了两个大包,王寂惺急忙运起“神足通”将海潮救下。
法隐大和尚四处奔走,寻找遭了殃的道长,送到安全之处,自己并不出手对抗官差。
大殿之外,王仙儿虽然战力尚可,但深陷泥潭抽不得身,又有数十人闯进太一宫,郭师爷也糊里糊涂被挤了进去。
阿赖耶心中打个小盘算,探手在虚空里抓了一把,竟然是十足的金锞子,他也不吝惜,随手朝官差老爷们撒去。
差拨们都是见钱眼开的老粗,起先还以为来了暗器,等看得真切,眼睛都跳了出来,争先抢拾,恐落人后。
郭师爷没注意,等官差佝下“神圣”的脊背,他便“脱颖而出”,好像鸡群中的仙鹤。
“是你!”王寂惺咆哮道,“又来作甚!”
羊刃暴喝而起,一招“兜罗绵”掌法,将郭师爷推到墙上,师爷的毡帽又落了地。
“奶奶的,原来是没有耳朵的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