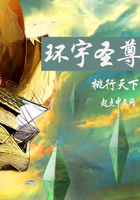三弓山,六甲坛,罗文正军师眉头紧锁,负手而立,一个老佣人正跪着擦洗地板上的血污。六甲坛东倾西覆,混乱不堪,地面淤了几滩血迹,四处印满无序的血爪印,莲座上咬痕宛然,滚落的供梨被踏裂了身躯,汁水四溢。这里发生了一场剧斗。
罗军师嗅了嗅空气中的血腥气,精神为之一振。这时小喽啰前来禀报讯息,他巧妙绕过地上的鲜血,盈盈拜倒在罗军师的脚下:“启禀军师,三秦州传来消息,有人在春风县、东夏县一带目击巨型猛禽,金翅利喙,体大如山,状貌似鹰,来去无踪。”
罗军师阴沉沉地盘算,久之,方问道:“郭师爷那里有什么消息?”
“郭师爷来信说三秦州教务可圈可点,堪称全教典范。”
“太一山拿下来了吗?”
“信中并未提及。”
罗军师来回踱步,三弓山上的云又开始变幻不定。
“这郭耗子,看来要本军师亲自去一趟了。”
罗军师将袖子一甩,准备去找曾大当家,刚要出门又叮嘱那老佣人道:“老宋,尽快清扫干净,你闻闻一屋子的狗骚味儿!”
“是!”
小喽啰悄声问老佣人:“老宋,刚才那畜生被打死了?”
老宋叹口气:“跑掉啦,虽未立死,却也身受重伤,凶多吉少!搜寻队都已经出发啦!”
三弓山后山石罅内,受伤的畜生蜷缩着,喘息粗重,他身上的血液流失了大半,染红了无名荒冢。
他没有后悔舍命来此,即便生为人身也在所不惜,何况自己是一副犬类的躯体。他就是小白,寒林雪狼,薛月的师兄。
小白在东北寒林被罗文正所伤,躲入伏藏石蓄养,因伤及头部,小白师兄陷入疯乱,丧失了理智。他一心挂念薛月,伤愈后四处寻找,凭着超能的嗅觉和灵性,小白师兄匹狼独入中原,不断搜寻薛月的下落,历尽艰辛,直到三弓山。
从东北狂笑寒林到三弓山,路途千里之遥,小白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三弓山下,浮浪子弟用啃过的肉骨头击打他的头,他忍耐下了。好心的村民见它饿得不行,给他一碗剩饭,小白感激而食。他似乎快忘了自己雪狼的身份,时常疯性大起,脑中只残存薛月的影像,固执的信念支撑他行动。
他感受到三弓山有薛月的气息,于是独自上山,人皆视之为狗,不曾阻拦。小白寻着逐渐淡薄的气味,来到三弓山后山的荒地。遗冢丛丛,幽怨横生,最熟悉的气息却出现在最陌生的环境。这里没有活人,只有故者。小白精神恍惚,眼前的“山丘”都在晃动。荒冢渗透出异界的讯息,黄土幻化成薛月的影子。
小白开始用前爪挖掘土堆,狼爪锋利,也经不住碎石的磨损。挖掘越深,他越是狂躁,狼眼红得像是泣血的珠。小白低嚎着,冢内疏散开的郁结怨气发出沉重叹息,潮湿的土壤解析出东北寒林融化的雪水。低嚎转为悲戚的长鸣。
薛月的衣角显露出山水,小白停住了。他肚腹上清晰可见的肋骨止不了哆嗦。
薛月的手指白得透明,鬓发依然青黑如旧,小白要的不是这个结果。
六甲坛传来曾大当家高亢的笑声,原来大当家亲自为罗军师传膳,让人抬了一桌酒席到六甲坛来。曾大当家揽爵立饮,先干为敬,豪迈的笑声一环接一环撞击罗军师阴沉的粗脸。罗军师强颜欢笑,勉强喝下一杯酒。“法仪重地不能饮酒啖肉”,天在上,地在下,罗军师敢想而不敢言。好歹送走大当家,罗军师吩咐老宋擦洗掉地面的酒痕和油腻,赶紧燃上三柱清香向各路神明谢罪。
小白听到了大当家的笑,嗅到了罗文正的味,他袭击了六甲坛,虽然力不及往昔,虽然好了伤疤忘了痛。罗军师很厌恶大当家对六甲坛的玷污,但好在雪狼小白的鲜血洗涤了此次不敬,来得及时。
太一镇,道法酒家,王仙儿等人刚打发了三弓山的匪徒,官差便碾轧街巷呼啸而来,济苍先生提议快走,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三郎笑道:“老先儿怕回春风县衙喝茶么?”
短暂计议后,大家决定去多罗寺见法隐和尚。王寂惺与济苍先生同乘一马,先头开路,王仙儿和海潮同骑,木下三郎一人一骑,沿着多罗大师的“足迹”迤逦奔向幽山古寺。
天色向晚,众人身陷于山谷丛林之中,多罗寺渺不可见。炊烟绝迹,鸟兽逡巡,苍苔碧油油未践人蹄,哪怕剪径的强盗都见不到影,空寂得让人害怕。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济苍先生吟咏出王维的诗句。
“先生好兴致!”王仙儿道。
济苍先生不好意思地说:“聊以壮胆,聊以壮胆!”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木下三郎轻拨琵琶,乐声远透山林,其音醇正清冽,应空谷而衍回响,令人闻之忘忧,没有半分轻薄之意。
天完全黑下来,王寂惺提议就地扎营,众人滚鞍卸马,生火造饭。
一夜无话,次日绝早,又备马投林。
王寂惺道:“只因我来去使用‘神足通’,一路没有山水阻碍,所以往来迅速。”
海潮奇道:“‘神足通’?那可是修行到一定境界才有的神通!”
三郎倒骑在马上,笑着说:“王兄弟的身手,在酒馆里就领教了!”
王寂惺略述缘由,王仙儿和刘济苍等无不惊奇。
海潮道:“三郎大哥,金翅鸟能不能载人飞行?”
三郎道:“能啊,不过大鸟自己不愿意!”
看看兰若在望,山路愈加崎岖,头口无法行走,众人只得下马步行,各将马匹拴在树下,任其吃草歇脚。身临精舍,窣堵波苍然孤立,寺内外悄无人声,找了半天,法隐并不在寺里。
众人有些失落,济苍先生忙打趣道:“寻隐者不遇,也是件雅事,对吧?哈哈……”
又等了一日,不见法隐回来。
“法隐大和尚既有言在先,定然不会走远,”王寂惺道,“有个地方我想去看一看,请大家在此等候,我去去就来。”
王寂惺迈开“神足”,飞也似的去了,倏忽已到三秦州首府。州牧江大人为其先父举办的“水陆大会”如火如荼,尚未结束。王寂惺进到江府花园,见乌压压一片道士和尚及玉莲教徒,诵经之声响遏行云。法隐和尚混迹其中,持珠念咒,一副心无旁骛的样子。
太一山道士在王寂惺失踪后彷徨无措,此时王寂惺忽然出现,让牛鼻子们诧异不已。王寂惺挤到法隐面前,挽着他的胳膊出了会场。
“师父,这么快就回来了?”
“还没去咧,也不用去了……大和尚,你怎么又来这儿了?”
“做法事啊!”
“你是得道高僧,凑什么热闹!”
“师父,话不可这样说,我见这会上诸人大半发心动机不纯,简直是误导亡灵,江州牧的老父亲在祭台上坐了一会儿就愁眉苦脸几欲离去,闻讯而来的饿鬼山精亦不胜喧闹愤怒异常,老僧若不引导一二,必愧对生灵亡魂。”
王寂惺点头:“且不说这个,我的朋友还在多罗寺等咱们,有东西要给你看。”
于是二人又撇了与会“道友”,不到顿饭时间,回到了多罗寺。
见礼过后,王寂惺取出薛月遗物“灰猴”,王仙儿拿出卜安的杯筊,法隐先看了“灰猴”,对王寂惺说道:“师父,请大家稍等,待我入定察看。”说完转入禅室,跌跏趺坐,深入定境,心中观想“灰猴”原主生死本末。
王寂惺有些坐立不安,忽然一只玉手轻轻放在他的肩头,王寂惺睁大眼睛痴痴地看着王仙儿关切的表情,心中涌起暖流。然而,她的手冰凉。
“嘿,搞什么鬼!王兄弟,男女授受不亲!”眼见香饽饽被别人染指,把三郎急得团团转。
等了许久,法隐开门出来,脸现疲惫之色。
“有结果了。”
“薛月现在何处?是否真的被人所害?”
法隐沉重地点头:“可怜的孩子,凶手是三弓山的罗文正……”
“罗文正?”王寂惺像跌落冰窟,顿时陷入痛苦之中。
法隐又道:“她的遗蜕现在三弓山。”
王仙儿和海潮同声安慰,王寂惺沉默不语。
三郎轻蔑地叫道:“什么螺纹正螺纹斜的?狗咬的杂碎!王兄弟别伤心,我木下三郎定斩了那杀人凶手,为你出气!”
法隐高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
王仙儿将卜安的杯筊双手递与法隐,法隐接了端详片刻,复回到禅室。
又过了良久,法隐皱着眉出来了,他抱歉地说道:“这器物……”
“大师,怎么了?”
“哎,恕老僧无能为力,这法器恐怕不是凡物,其主人必然有甚深修为,无法在禅定中窥见端倪……请收好。”
王仙儿呆了半晌,定定地直着两眼,一颗悬起的心重重摔在地上。
刘济苍忙问道:“老师父,断霜道长的下落能算到吗?”
“断霜道长乃是得道仙人,仙踪缥缈,深不可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