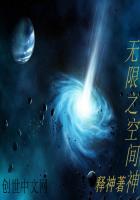宁雅的班里有个上进的好学生,可惜父亲早早去世,母亲抗不住艰难,把他扔给爷爷另找男人生活了,几乎不再回来看过这个儿子。
好学生和爷爷一起艰苦的生活,也许是老天爷的安排吧,让这个学生坚强而孤独,善良而敏感。当然,最重要的是学习是玩着命学的。
宁雅既同情又欣赏这个学生,所以,她决定帮助这个学生,当她有了三亿六千万的存款之后。
她找来学生和他的爷爷,非常温和而谦虚的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谁知爷爷和学生坚决的拒绝,那种坚决令宁雅动容,因为,如果他们接受了她的帮助,反而是在伤害他们。
“我能养得起我的孙子,养得起我!我还要供他读大学,我有钱,我有好几万块钱,别小看我,我挣的钱不比你老师低。”
“宁老师,谢谢你。”那学生在与他的老师分手时恭敬的鞠躬,眼睛里含着泪花。
是的,宁雅决定不再这事上纠缠,他们以他们的方式度过难关,别人再掺进去,反而是伤害。
三亿六千万,可怎么用呢?
捐款?不可能,宁愿全部烧到一张都不剩也不捐出一分钱给任何高大上的机构。
她想起自己来学校的路上,有二十个井盖不是缺就是破,那些井盖仿佛是用煎饼做的,用不了几天,都被车子压得露出黑漆漆的洞。
可是,距离那个日子还剩下九天了。怎么完成这个任务呢?
宁雅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好事,她要出一口气。
因为那些破洞害得她每天上下班提心吊胆的,特别是晚上自修回家时,路灯昏暗下,骑着电动车的她不得不放慢速度。这还不够烦恼,最烦恼的是下雨时,路面全是水,把那些坑洞全掩盖了。
年轻的宁雅的人生没有多大的为难之事,令她最大的烦恼就是那些洞了。
所以,她找到一个施工队先预付部分工钱,然后叫他们去测量那些井盖大小,吩咐他们把井盖做足五寸厚,下面装有卡销,而且一装上去就别想拆出来,除非敲碎,而宁雅又已经叫施工队把井盖做得异常结实,钢筋,水泥都非常充足。
施工队哪里明白这个年轻女子的狠毒心肠还以为是市政工作人员呢。
管她是谁,给钱就办事,而且要办得超级好,因为工钱真的TMD太高了。
高得像医生动手术那么高,带头的对他的伙计说。
工人量好尺寸当即做模,同时把相应的机关埋进水泥预制块里。
不用一天时间,接近二十个井盖做好,只等保养几天后拉去盖好。
宁雅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这条自己上班的路上那些被各个单位挖得坑坑洼洼的地段全部填了,TMD的都填好,浇上最合理的混凝土,做得三百年都不破一丁点儿。
“我不信,这种工程要多大的技术含量,只要下足料,不会做不好的。”宁雅对那个施工头头说。
头头心里很纳闷,从来没见过这种官员这样做事。
第三天,宁雅对头头说:“凌晨三点钟,把那些井盖全盖上。”
头头很想问为什么半夜施工。宁雅又每人给两百元钱算是加班费,堵住了他们的好奇。
“我要让天亮时人们上班看到新面貌而大吃一惊。”宁雅说。
当宁雅看到经常恐吓自己骑电动车的坑洞消失时,兴奋的骑着车从井盖上而滚过。
“哼!终于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宁雅说,“快我的心。”
不过,直到第九天,她上班下班的路的那些坑还没修整铺好,她把预算的钱当着全体工人的面全部给了施工的头头,说现在有事另外去忙了,以后有工程还会找他们的。
头头接过散发着这个高雅美女的气息的钱,放在贴心的口袋里,觉得自己温柔了些。他刚才很想趁在接过钱时碰一下美女的手,可美女的手非常灵活,好像事先就知道他的意图,收手得很快,但是很自然,还给他一个甜甜的微笑。
这微笑,使头头晚上下班回家看老婆非常不顺眼连饭都没心情吃。
没心情吃饭的还有一个温媛儿。
她已经连续四天没心情吃饭了。没心情吃饭不代表不吃,而是吃得不甘心,吃得不爽。
别看她已经有八百三十万的存款了,可她依然执着的不忘张依海的三十六亿,陶光的十八亿,宁雅的三亿六千万,都TMD的上亿啊。我怎么那么笨呢?我随便喊个数字都比五千强吧?出个“万”字口死得了你?温媛儿?
她恨,恨,恨所有人,包括冷杜丁,甚至包括零夏,别看她的钱少又给了自己五十万,说不定她心里在笑自己呢,说不定她已经勾上了张依海陶光中的任何一个,跟他们要钱了呢。
哼!
连续四天吃不好睡不好更没法玩好,幸好,她的神经非常强大,虽然把自己弄得头发乱糟糟的,一开口就是几天不刷牙的臭味,可竟然没有憔悴,依然恨意饱满,不肯减了半分。
一下子得了三百多万的零夏喜不自禁,跑到商场大买特买化妆品衣服,尽管她大概知道离开地球时这些衣服可能都不怎么用得上,但禁不住自己,也不想控制自己。
不想控制的还有吃,连续好几天,她叫上同学们进出餐厅迪吧,放开了吃,放开了玩。
“哪儿来那么多钱?傍上谁了?”她的同学这样问她。
“傍上一个最富最帅的哥,整个地球的财富加起来都没他那么多。“零夏看着天空说。
她在想,十天内怎么花完这些钱。
一分都不要留下。
她的家族有的是钱。
她还把一个和她很亲密的男生折磨得差点这辈子不敢亲近女人。
她要了又要,她要够,她要任性。
“夏,我想买辆车。”那男生见她浪费惊人,心疼那些像水一样流出去的钱,还不如买样东西踏实。
“好呀,那你就去买呗。”
“你知道的,我没钱。”
“没钱买什么车?跟我说买车?问你妈要钱去!”一脚就把那男生踹下床。
那男生嘀咕着穿上衣服,一脸怨气的离开了。
“MD,果然我看错了人。”她期待那男生扑上来和自己打一架,然后又要,那倒有可能买一辆车给他开开。
日薪五万的罗星明一肚子的闷气,这几天也为自己的一千八百万难过,这些数字和其他人相比太远了,三十六亿的张依海,十八亿的陶光,三亿多的宁雅,就连凌峰都有三千六百万。
倒数第三,顺数第五,问题是第四的凌峰都比自己的财富多一倍,多一倍。
不行,这个差距一定要拉近,或者想法超过他们,瞧他们那***样,哪像是有钱人的样子?
罗星明站在镜子前,仔细打量自己的五官,研究气色,什么上停中停下停之类的。
气色是不错的,就是眉头皱了点,嗯,想开些,机会很多,只要做得好,获得冷杜丁的赏识还怕财富不会超过所有人吗?
所有人都在为钱的事费神的时候,凌峰却坚定的认为那三千六百万不是自己的。
多年来,他一直刻苦的练习爷爷传给他的技击术,他爷爷说过,轻易不要让外人知道他在练,也不要轻易和人交手,不能用技击术去打架,除非受到威胁。
“没有实战哪能提高技击水平呢?”凌峰一直在想。
爷爷远在家乡,凌峰作为广东私立学校的一名小学体育老师多次叫爷爷来和自己住,可爷爷说在家乡呆惯了,不想出门生活。
凌峰没爸爸妈妈,当然,他不是石头里嘣出来的。
据爷爷说有一次赶圩时看到路边有一个包袱,好奇使他走近观看,谁知里面躺着一个满脸疙瘩的婴儿。爷爷把这个婴儿抱到民政,没人愿意处理这事,爷爷只好抱回家。
爷爷种有一个山坡的果树,果树中间就是他的家。
凌峰是在果树下长大的,他的童年快乐无比,又失落无比。
快乐是爷爷很会玩,很疼爱他,失落是当和别的伙伴在一起时,便知道这世界还有“爸爸妈妈”这种家庭成员。
野孩子,野种,垃圾仔,等等称号伴随凌峰长大。
“你要忍,最好当作一种修炼。”爷爷说。
当凌峰意识到自己与从不同时,他已经十三岁了。
他的与众不同是:他天天练习爷爷教的那些奔跑,跳高,使棍,舞刀,捶沙袋,过独木桥,扔石块,爬树,爬山,和爷爷摔跤,对打,还要自己摸自己身上的关节,筋骨,肌肉,熟悉各个部位并知道它们的作用,等等。
他甚至曾经以为别的孩子也和他一样,从小就和自己一样练习爷爷教的东西。
爷爷成功的把练习技击术融入了凌峰的生活,融入了他的骨头和血肉里,使凌峰在任何情况下都自然的每天练上至少两个小时。
“你练的不是功夫,甚至也不是打架的能力,你练的是符合你身体结构的行动能力,既让你少生病又让你最大程度的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记着,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自己,就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敌人。”
爷爷最爱说的这几句。
所以,作为小学体育老师的凌峰几乎不受影响的继续上课,认认真真的。
当然,他也教授一些时下流行的武术套路。
没人看得出他的真实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