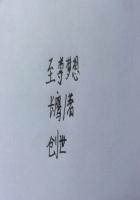外面下起了雨,大门咯吱一声响,又咣铛一声后,传来沙沙沙沙的雨声,雨水打在芭蕉叶上,发出毕毕剥剥之音,像是有女鬼在夜里发情。
徐雅楠遇害的那天夜里也下起来了雨。
手铐冰冷,沉重的铁椅子拴住了我,谁来帮我脱身?明天早上学校的女厕所里将呈现惨不忍睹的血腥画面,难道徐雅楠命中注定会死在女厕所里?
“还能找到吗?”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
刘平领着一个穿军装的女孩进来,女孩脸如银盘,唇红齿白,身姿曼妙,素净幽雅。她摘下军帽,甩了一下头,乌黑的长发倾泻而下。在我的印象中,普通女兵是不能留长发的,一般都是齐耳短发,能留长发的女兵,应该是文工团的,她脚上穿着黑色半高跟带扣布鞋,而不是解放鞋,这更加符合我的判断。
“真倒霉,看了场电影,自行车被偷了。”女孩说。
“请问您贵姓?”刘平和颜悦色,有点客气过头了,还贵姓,看来警察和吊丝一样,看到漂亮女孩也紧张。
“宋天娇。”
“嗯,天之骄子,好,你自行车是几点丢的?什么牌子的?”刘平说。
“几点?这不知道啊,自行车是凤凰牌的。”宋天娇说。
当宋天娇说完这句话后,我一下听出这个女孩是谁了,她就是刘平未来的老婆。我不由笑了。
“你笑什么?”刘平瞪了我一眼。
“笑笑也不行,你这派出所难道不让人笑?非得看人哭?”我说。
“蒋未生,我警告你,你给我老实点。”刘平说。
“这小孩怎么了?”宋天娇看了看我。
“这孩子胆子大得很,竟然绑架老师。”刘平说。
“绑架老师?为什么?”宋天娇一脸惊讶。
“为什么?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她说为什么了?”我说。
“宋天娇,你不用理他,这孩子有神经病,墙边那个老头是他大伯,也是神经病。”刘平说。
“我不是神经病,你才神经病呢。”我说。
“这么小年龄,就得神经病了?”宋天娇抖了一下肩膀上的雨滴。
“姐,我真不是神经病,我是被冤枉的,你救救我吧,我要回家。”我说。
宋天娇看了刘平一眼,“他说他不是神经病?”
“这小孩神经真的很不正常,他的话你别信,他还说他自己有特异功能呢。”刘平说。
“他真有特异功能?”宋天娇问。
“这孩子撒谎都不带打草稿的,你别信他的,还是说说你自行车的事吧。”刘平翻了一也笔记本。“宋天娇,你多大年龄?”
“我知道天娇姐多大年龄。”我急忙说道。
宋天娇眨了眨眼,“那你说说我多大?”
“今年是1987年吗?”我问。
“看吗,这不是废话吗?”刘平说,“我说这孩子脑子有病吧。”
“今年是1987年。”宋天娇说。
“1987年?好吧,我想想,你别急,”我暗暗自语,“火葬场那一年好像是兔年,应该是兔年。”
“别听他的,宋天娇,你的凤凰自行车锁了没有?”刘平问。
“好像锁了。”宋天娇说。
“天娇姐,你今年应该19岁,或者是20岁。”我说。
“那我是19岁还是20岁呢?”宋天娇娇滴滴地问。
“21岁。”我说。
“你确定?”宋天娇说。
“我确定你今年21岁,你比我大六岁的样子。”我说。
“没错,我是21岁,你怎么知道的?”宋天娇惊讶地问。
“天娇,你别听他的,这小孩是瞎蒙的。”刘平说。
“天娇姐,我可不是瞎蒙的,我还知道你住在大同街呢。”我说。
“是啊,我是住在大同街,你认识我?”宋天娇说。
“我当然不认识你了,这是我突然想到的。”我看了一眼手铐。
“这孩子好像真有特异功能呀?”宋天娇说。
“不可能,他百分之一百瞎蒙的。”刘平说。
“不是瞎蒙的,天娇姐,我还知道你是部队文工团的,是跳舞的,我没说错吧。”
“对啊,你还知道什么?”宋天娇把椅子朝我挪了挪。
“你应该在三十一军,你父亲也是军人。”我说。
“那我母亲呢?”宋天娇说。
“你母亲应该是随军家属。”我说。
“对,我是在三十一军文工团,我爸也是军人,但我母亲不是随军家属,我母亲在教育局上班。”宋天娇说。
“你看看,他说错了吧,我说他没有特异功能吧?”刘平拍了一下桌子。
“天娇姐,我想想,”我努力回忆着火葬场那天的情景,“对了,你喜欢戴玉镯子,你家里应该有一个祖传的玉镯子,XJ和田玉,墨绿色的。”
“哎呦,这你也知道。”宋天娇一脸惊讶。
“你家真有祖传玉镯子?”刘平问。
“对,他说的没错。”宋天娇点了点头,“我看他真有特异功能。”
刘平挠了挠头,一脸困惑的看着我。
“天娇姐,我还知道你以后会有一个女儿呢。”我说。
“是吗?我会有女儿?那我应该有爱人吧?”宋天娇说。
“当然有了,不过,不过,我还要想想。”我说。
“我怎么听起来,这孩子会算命?”刘平说。
“刘警官,你如果放了我,我就给你算算命,让你逢凶化吉。”我说。
“警官?谁是警官?给我算命?你小小的年龄,满脑子都是封建迷信。”刘平背着手呵斥道。
“公安同志,这孩子不像神经病,你们应该放了他。”宋天娇说。
“放他?他这是绑架案,这是大案子,我可当不了家,这要我们所长同意才能放。”刘平说。
“那就给你所长说说不就行了吗?”宋天娇说。
“所长去外地出差了,他明天应该能来,明天我请示一下,如果所长同意结案,那就可以放了。”刘平说。
“不行,我今天晚上就得出去,我还没吃饭呢?”我说。
“能不能今天晚上把他放了?”宋天娇说。
“绝对不行,这是违反纪律的。”刘平说。
“他就在这里坐一夜?”宋天娇说。
“只能这样了。”刘平说。
“他还是个孩子,你们让他坐一夜?这太残忍了吧。”宋天娇说。
“宋天娇,我们来说说你丢自行车的事吧。”刘平说。
“自行车你们什么时候能给我找到?”宋天娇说。
“说快也快,你别急,我一定想方设法给你找来,这事包在我身上了。”刘平说。
“说慢也慢是吧?你真能给我找来?”宋天娇问。
“如果找不来凤凰,我给你找个永久牌的自行车行不行?”刘平说。
“不行,我就要我的凤凰。”宋天娇说。
“刘公安,如果你放了我,现在我就能找到天娇姐的凤凰自行车。”我说。
“在哪了?你说,说出来我就放了你。”刘平说。
“放了我,我才能找,并且我自己带着天娇姐,才能找到。”我说。
“你这点小聪明,我看就算了吧,今天你休想出去。”刘平说。
宋天娇跺了跺脚,“你这公安同志,怎么这么不尽人情啊,你就不能放了这孩子?”
“我有名字的,我叫刘平,真得不好意思,不能放他,这是革命纪律。”
“什么革命纪律?真是的,我走了。”宋天娇说。
“你自行车的事,我还没问完呢!”刘平说。
宋天娇头也不回的走了。
刘平转过身来盯着我看。
我仰着脖子吹着口哨。
“你很有一套啊。”刘平捏着自己的大拇指。
“没什么,这女孩一会,还回来。”我说。
“真的?”
“这还能假?”
“她来干什么?”刘平问。
“她一会来给我给送饭。”我摸了摸肚子。
突然刘平抬起一脚踹过来,我和椅子重重地摔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