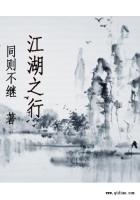何虾贵臃肿的孕肚在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招来了当地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因为何虾贵的两个孩子都是带在身边的,所以,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
计生办给他们最宽容的处理,就是限期撤离该镇,不给他们的工作业绩抹黑。租门面是有押金的,而急切间门面转不出去。蔡跃进就想把门面让何宝贵他们接了,这样蔡跃进的押金就不会白白丢了。
何宝贵自知跟蔡跃进打交道没有什么好处,自己又不是没有门面,也用不着再要门面。就不同意接手他们的门面。
蔡跃进力陈他们的门面好于何宝贵的门面。
这倒是真的。
何宝贵想,先借过来,再慢慢把自己的门面转出去也行。
接手的时候,蔡跃进又以玻璃柜台不方便带未接口,把玻璃柜台连同里面摆着的打火机以前作价给了何宝贵,
所有的钱款一次付清了。
蔡跃进、何虾贵他们搬到百十里外的县城去了。
门面不好转,加上这一年多雨,所以何宝贵灵机一动,决定用一套本钱做两个门面的生意。
廖又德的妹妹廖小芳过来帮忙了。
本来应该廖小芳带孩子做饭的,但是,廖又德说她不会做饭。
廖家兄妹带着孩子在以前的门面做,何宝贵就在姐姐转来的门面做。做饭也是何宝贵,
只有孩子要吃奶或者他们要吃饭了,廖家兄妹才会过来。
廖慧明吃了十个月的奶,后来她一吃奶,何宝贵就头晕。这样就把奶断了。
本以为一套本钱做两个门面的生意,是一个极好的主意但是何宝贵缺不知道,她这样跟他们分开着,等于是放任廖又德了
因为原来的门面隔壁是一家理发店,里面有四、五个年轻男女,跟廖家兄妹差不多的年纪。
以前何宝贵在店里,跟理发店没有过多的来往。何宝贵不在了,他们就天天玩在了一起。
开始是打牌,后来逗逗打打的渐渐就有些让旁人看不下去了。
平时跟何宝贵关系好的一个老板娘就提醒何宝贵注意。
何宝贵一天晚上提早收了生意,去到那边看,果然,廖又德跟他们玩牌正在兴头上,高声地叫着谁欠他钱还没有给,何宝贵去了他也没有发觉。
后来廖又德发现何宝贵去了,也毫不在意的跟两个女徒弟和一个附近的女人说笑叫闹着。
还真是有些放纵的样子!何宝贵当下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几个女人见何宝贵来了,才没有继续玩了。
过了不几天,廖小芳跟理发店的女徒弟发生了口角,你女徒弟说的话就是看不起他们的生意。
廖小芳以前打工手上攒了一点钱。在带侄女过来吃饭的时候,就跟何宝贵说,想把自己的钱借给他们扩大生意。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两个门面用原来的本钱,一点没加,确实没有把优势发挥出来。
所以,当廖又德过来吃饭的时候,何宝贵也坐下在吃饭,就说给他听。
“你妹妹说想把她的钱借出来给我们。”何宝贵一边吃饭一边说。
哪知道下一秒廖又德操起身边电饭煲的锅盖直接就照何宝贵的头上盖过来了。
何宝贵惊叫着,可是更加重的拳头雨点般地向她打来。
“走!我跟你去问她!看她哪里来的钱借给你!”,廖又德凶恶的叫着,把何宝贵拖向门店wa外。
立即,何宝贵只穿着短裤的膝盖上就被拖伤了。
是他妹妹自己说的借钱,借不借都好,何宝贵只是学说了一句而已。廖又德却突然给何宝贵一顿狠打。
看起来,廖又德是不想在一起过了。
何宝贵想起跟他在一起的日子,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伤心的事情,就再也忍不住了,要散就散,不散也不能这样生活。
但是,廖又德又不跟她说清楚,打完人,他让他妹妹跟何宝贵住,自己会老门面住。
第二天,何宝贵也没心情做生意,她到老门面去跟廖又德理论。
可是,廖又德管着门,不理她。
这时候街上的门面都已经开始做生意了。连生孩子都舍不得关门的何宝贵,两个门面都关着,而且,看样子也吵不出一个所以然。
“你这个缺德货!有本事打人就跟我说清楚!关着门是不是死在里面了?”,何宝贵眼见又要像以往一样,什么说法也没有就过去了,一急,就骂了。她手上抱着慧明。
“呼”的一声,店子的门被突然打开了,廖又德气势汹汹地跑出来。
何宝贵一看他又要打人了,赶紧跑。
廖又德居然追了很远,眼看快追上,何宝贵只得将孩子放下再往前跑。
大街上,上演着一幕狼追羊的惨剧。
廖又德先是抱起了慧明接着追赶何宝贵,后来邻居黄十元跟上来了,也许是来拉架的。廖又德竟然把孩子递给了黄十元,而黄十元竟然也接过了慧明。
廖又德大显神通,几步追上何宝贵,把她推到在地上,不等何宝贵反应过来,廖又德的脚就实实在在地踢在了何宝贵
倒在地上的头上。他还生怕踢的不实,还特在对著何宝贵脑门心的前脚掌又补了一把劲。
何宝贵当时就干呕起来。
而廖又德和黄士元已经走开了。
意识到自己躺在到街上呕吐,何宝贵爬起来,昏昏沉沉地走回了家。
这个黄士元也跟廖又德一样,是进过号子的,所以两人关系很好。而那个跟何宝贵关系好的老板娘,也就是黄士元的同居女友。他们也过着貌合神离的日子。
不过,他们两人因为没有孩子,不久就分开了。
分开前,黄十元公然无耻地上演了一场由他组织的赌博,把他们的钱输掉,让那个女人什么也没有的走了。
当时看,那个女人是吃了大亏,但其实她比何宝贵强---她开始了新的生活。
何宝贵回到店里,写了离婚诉状,到镇镇府去。
廖又德不去,她自己一个人去的。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干部接待了何宝贵。
那男干部一开口就是向着男性的口气,好像谁提出离婚就是谁的不对。
婚没有离成。也许,那个男干部也是一番好意。
这天晚上,何宝贵找出自己给廖又德织的毛裤,烧了。
那把火,烧的不仅仅是她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毛裤,烧的更是她对廖又德仅有的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