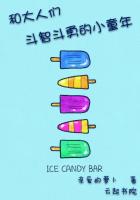天色渐渐暗淡下来。黑色一如既往,总是在准确的时间里对城市狼吞虎咽,城市却只能像个无助的孩子,微微亮起几点光亮垂死抵抗。
朝华公园玩耍的小孩,足个被成双成对的男男女女取代。
长条木椅上,伟人雕像旁,大树影低下,楼楼抱抱卿卿我我,扭动着身躯做出各式下流或无耻的动作。
大学生,本该是青年一个有着理想,憧憬和热血的时间段。然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青年并非怀揣着什么理想,憧憬。热血到是有,这种热血来至异性。
“尤老师。”空气中忽然荡漾起稚嫩、甜美却毫无感情色彩可言的女孩声气。
尤凡缓缓合起书本,抬起脑袋,朝向声音源由“下课了?”
眼前女孩儿身着蓝白相间色运动套装,短发干净干练,白嫩鸡蛋脸,架在弯弯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使得其气质看起更是清纯且学术渊博。
这些只是对‘零’外表的描述。事实上零不仅外表优秀内在更为优秀。
年仅19刚上大二就有着相当丰富的理科知识。14岁时便以发表在美国《Science》的《时间起源》入围若贝尔物理学奖。
不单如此她更是空手道9段,跆拳道2017年世界锦标赛冠军,擒拿格斗高手兼理论专家,中国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说典型点就是胡一菲百倍增强版。
而这一切的由来都归功于尤凡,零的义父或老师或朋友。
11年前,尤凡到东郊足足半年有余。
东郊的天不下雪,至少在50年的记录里不曾下雪,有过几次也只是雨夹雪。薄薄的类似雪花的冰片,从天而降落到人身上如针扎,刀割。
这年稀奇,5月下雪,真正的雪花。
鹅毛般的雪花,一片接着一片下落,落得满大街的柏油路白灿灿的,满大街的柳树枝白灿灿的,满大街的房顶白灿灿的。
尤凡裹紧薄薄的只得有一只袖子的劳保服。偶尔提提还是在校时发的裤子,裤腿磨破剩下半截。解放鞋鞋底几个大窟窿,脚后跟一起一伏,依稀可见。
他佝偻着背,步履蹒跚,仿若明国时期抽大烟的懒汉,混合在各式各样川流不息的羽绒服中。然而,无论多么拥挤他的周围都有很大空隙。因为没人愿意接近这个头发乱乱蓬蓬,近似乞丐的家伙。
13巷子街头转角,有两个大得能一口吃下一个人的绿色塑料桶。人们把生活中不再需要的东西往里扔,一日一日,一夜一夜,两口大桶永远不会满足。尤凡知道那是因为天还没亮就会有穿着黄色马甲的人把桶里的形形色色往白得发黑的挂车斗里一倒,便走了。
刚走到街头,一转角,像是某种力量牵引着尤凡停住脚步。
寒风凛冽,尤凡本就无神的眼神微眯。绿色大桶下躺出一双又小又瘦的腿,腿上的小皮鞋已经看不出颜色,几只小脚丫钻透鞋尖抵破的空洞,裸露在这极冷的冰雪天气里,冻得发紫。
犹豫片刻,尤凡始终低下的脑袋,不由朝两大桶中间缝隙仔细打量。
视线中是一个头发凌乱,衣服脏得离谱,裹着一条牛仔短裤双手抱着光溜溜的膝盖瑟瑟发抖的小女孩儿。
小女孩吃力的抬起小脑袋。脸青得跟黄瓜似地,咬紧牙齿努力控制身体不乱抖动,鼻子呼出的白烟一阵一阵往上冒。她睁大眼睛,用微微发黄的眸子死死盯着尤凡。
雪很大,风也很大。有些人恰在天堂,眼里竟是美的享受。有些人却在冰窟,饱受低温侵袭的不单是娇小的身躯,更是冰冷的心。
久久的对视,两人仿佛都生成了一种奇怪的心态,那像是比这对视的时间不知长上无数亿倍的亲情。
“来吧!孩子我带你走出痛苦。”尤凡伸出右手,摊开手掌,头发被风刮得左右晃动。
女孩看着尤凡坚定的眼神,许久。
“恩”突然也变得坚定,伸出瘦小而又胀呼呼的手。
风刮得异常的猛烈,雪也越堆堆厚,两排脚印,两个单薄的背影一高一矮,同样佝偻着背,同样步履蹒跚,渐渐朝雪的深处走去。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
“嗯。”
“这样啊!!!那想一个呗。”
“、、、”小女孩有些茫然,或许从未想过自己哪一天会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嗯!没有就是零。以后就叫你零吧!”
“嗯!”女孩欣喜若狂。
在尤凡那儿,零学到了许多人这一辈子或许都学不到的知识。从数字0到9到无穷大,从一元一次方程到多元复合函数,最后全微分方程解析。
力学,热学,声学,光学,电磁学最后原子物理学。元素周期表到各种反应式,各种反应方法,最后为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尤凡把所有自己拥有的知识都传授给了零。
不过零真的算是奇才!连尤凡对她所表现出的惊人能力,都不敢相信,甚至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个梦,只希望这梦不在醒来。偶尔想到自己一身的遭遇,失去所有亲人,受到所有同年人的排斥,心里都会出现极度的怨恨。可是一看到零的身影,又会不自觉的流露出笑意:“我的好运气。”
尤凡在传授零所有自然科学常识之余,哪怕是在那些最穷困潦倒的日子,也让零进入各类道馆学习各国各种格斗技巧,泰拳,跆拳道,柔道,太极等等。
“今天晚上我们在外面吃。”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