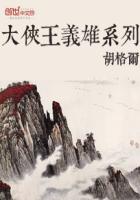司马頔听长兄给自己的形容,发现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天,每年这个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可以为所欲为的吃自己最喜欢的好吃的,可以穿阿母裁的新衣,还可以烧竹子玩,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只是竹子爆裂的那一瞬间阿姊害怕躲闪的模样司马頔挺喜欢的。
当然最最最重要的是阿翁也会陪着他们,这一天他便可以蜷成团窝在阿翁怀里听阿翁讲稀奇古怪的故事。
司马頔今天像个小老鼠,一刻也不停息的跑来跑去,实属难得!惊吓得司马祎赶紧把自己宝贝的书简全都收进了阿翁的书房,事出反常通常弟弟这样的时候都是他倒霉。
“彼那是穿着新衣服高兴的!”
司马祎看看出来替小弟解释的阿姊,有些愤恨,“彼若是再用我的书简练字,我..彼的衣服也别想穿了!”
司马姝掩面轻笑,每年都如此这般咬牙切齿的说一遍,可惜呀,书简照样都是被毁了,可是他的话哪一次都没有成行!
整个家中,赵陵在厨房和婢子们一起忙碌着做一顿丰盛的饭,司马姝也带着一两个小奴要把整个院落清扫一遍,至于那两位,一个只忙着虎视眈眈看着弟弟。
只是谁都没有注意司马姝中途出去了一小会儿,回来时面含桃花的匆匆跑回来,这次可没有躲过两个弟弟的眼睛,两个人一解“书简”的“仇怨”,相视一下心照不宣的露出奸笑。
到了夜晚,支起炉火,大家围炉而坐。
司马頔双手并用的往自己这里揽着吃食,自己最爱吃的恨不得塞满自己的嘴,最后还是阿翁无奈的像每年一般把他揽到自己怀里远离充满诱惑的几案,司马頔还会不甘心的挣扎两下,然后看着美味的食物泪眼汪汪。
轻轻捏一捏儿子极有肉感的脸,在揉一揉他的小肚子,古意拧紧眉头,“頔儿,可不能吃了。”
“可是..”司马頔撅着嘴有些不明白,做那么多好吃的不是让他来吃的么?
司马祎还故意气他,夹起一块美味的肉在他面前晃荡,再品味一番,“肉味香而不腻,阿母手艺真好!”
“哈哈,頔儿,今天吾让汝练的字练会了么?”
“会,会了!”司马頔窝在父亲怀里说的有些心虚。
一眼看穿了儿子的掩饰也不拆穿他,故意拿出一片简牍在他眼前轻晃,司马頔慌张的赶紧又往父亲怀里钻了钻,这一惊吓彻底把美味珍馐的事儿给忘到了脑后。
抱着小儿子还不忘调皮的对着其他人使了个眼色,大家看着司马頔都是一阵好笑。
其实司马頔还是很郁闷的,在他的人生观里这个重大的日子不就应该轻松一些么?不要练字只想休息!
不知道从哪里,他又掏出一卷竹简,用丝帛小心包好的一卷,看起来还很珍贵。
“祎郎,汝要学星算,这个是今年才编纂成书的算经,便先看看,之前汝看到的都是只言片语,来,看看这个!”
司马祎新奇又激动的双手接过,期间司马頔还伸出个小脑袋也想要,被长兄无情的给按了回去..
迫不及待的打开丝帛,摊开竹简就想赶紧去看,却被阿母拦了下来,对他摇头。
“今天可不许,这个我还让汝阿翁收了了几卷,但是今天这卷也不可以看,咱们好好聊聊!”
司马祎有些不舍的才把竹简收起,虚心受教。
两个儿子,一个太勤奋如丈夫一般嗜书如命,一个太懒整个人都是肉嘟嘟的。
其实聊天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事情,因为阿翁总是大江南北的跑,每年都能讲出很多稀奇古怪的见闻,还有很多闻所未闻的故事。
阿翁讲故事的手段很高超,引人入胜,所有人都不自觉的认真倾听。
比如赵破奴逃回来带回来的匈奴那方的见闻,阿翁攒了这么长时间就等着今日与一家人围在炉火边好好聊一聊,讲一讲。
司马姝眼睛瞬也不瞬的盯着父亲,总是有些迫不及待,“匈奴的人都是什么样的?”
“阿翁,匈奴人都吃什么?和咱们一样么?”
“阿翁,阿翁,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匈奴语,好奇怪哦!”
阿母会讲一些楚地的神话,讲一讲楚地巫师是如何的摆出阵势驱魔除邪,讲一讲湘君与湘夫人的故事,这时候阿翁还会吟唱出一段《九歌》相应和。
那些故事啊,有新的有旧的,但是总也听不厌。
司马祎觉得自己也长大了,应该也有些见闻拿出来分享一下,只是..狡黠的看一眼对面的阿姊,自己斟酌着才对着父母耳语。
“真的?”有些不敢相信的追问司马祎。
“阿翁,都是真的。”
赵陵只是拂袖掩笑看着女儿,轻声唤过女儿执起她的手,“姝儿,宣明的杨郎..”
“啊!”自知失态司马姝赶紧将脑袋埋起,一手还想用微凉的手为羞得发红的脸降温。
“祎郎瞎说!”最后辩驳的话语都是轻微无力的。
司马頔耳朵灵,揉揉眼睛看着阿姊,“小子也看见了啊,杨敞大兄,昨天还在..”话没说完收到阿姊的目光自觉的就消了音。人家说的是实话啊,为什么大家都满脸笑意只有阿姊那么凶呢?
揉揉司马頔的头发,笑的爽朗,“看来家中好事将近了!”
看着禁不住打趣已经脸色烧红的女儿,他还品一杯清酒,嘴角勾起微笑,故意大声道,“看来过几****要好好问一问杨郎了,彼可不能欺负了姝儿..”
“阿翁!”
司马姝打断父亲的话,却引来大家一阵低笑,被父亲给算计了呢!
司马頔完全不在状况,只是觉得自己也应该显摆一下最近的新鲜事儿,一直拉扯着父亲的衣袖,很久才得到注意,不觉有些委屈的瘪嘴。
“小子也有一件事儿想说。”
挑眉看向紧张不已的姝儿,笑意更盛,“好呀!”
大家都屏息等着司马頔,尤其是司马姝整个人紧张的一直在绞着自己的衣袖。
“前几天,夏叔对我说哦,咱们过这个时间过节才有四年,和我一样大!”
短暂的沉默却惹来的哄堂的大笑,司马頔大大的眼睛一眨一眨,不明白,这可是他最大的秘密等到现在才说的,他觉得长兄一定没发现!
司马祎笑得都流出了眼泪,点着他的额头,“汝真的不知道?”
“那是因为新的历法呀!”
司马頔眨眨眼完全的不明白。突然头顶受到父亲无情的蹂躏,梳的一丝不苟的发髻都凌乱了。
父亲敲了他脑门一下,把他拎出来,佯怒道,“汝是太初元年出生,记住啊!明天也与祎郎去看看星历!”
“哦..”虽然仍然不明白为什么。
后来长兄才悄声的给他解释,那是父亲主持修定的历法,没有太初历还没准没有他呢,说完长兄还一通低笑,只是司马頔完全不明白哪里好笑了?完全不明白其中的关联。
那年,天汉元年,是司马頔记忆中的第一个春节,也是他记忆中最美好的一个春节,第二年李陵出兵匈奴兵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