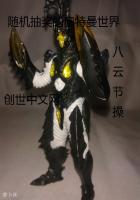几位长辈整天泡在太史府比我来得还勤,我几乎放下了所有的事情陪着他们,还有主上特准的我更要陪着去拜读父亲的书稿。面对如此的好机会我当然也不会错过,当作虚心的长辈一直追在他们后面请教为文做人的道理,与他们畅谈国家大事,甚至还会谈一谈父亲。而我只能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去了解,再了解。
盐铁会议也是进行了几天,收获颇丰,有识之士与御史大夫针锋相对的辩论是两个不同声音的对碰更是国家之幸。
这几天我说清闲也清闲说忙碌也忙碌,但也忙不过长兄,这些日子里他一面在与东方伯父商议我与东方子琪的嫁娶问题,一面又天天往阿私那里跑,两个人也时常聚在一起有所商议。
每每看到二人走在一起的身影我都觉得背脊发凉,两个都是有学有识又能洞晓一切的通透人物,两个人凑在一起..不敢想。
盐铁会议结束,我刚喘一口气准备继续我的修书事宜,却不料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从匈奴那方传来的消息,大汉也是相持了许久。十几年的等待十几年的坚守,今天终于得偿,回归故土!
苏武,我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大约只在父亲的口中偶尔会听到几声对他的叹息。
朝堂上对他的迎接极其盛大,民间的黔首也是沿街排开阵势相迎,十几年的坚守换得满世的赞誉,千秋百代的称颂,他回来了!只是那大漠那草原,有一个人似乎永远不会回来了..
盛大的典礼,对他拜官封赏,只是一个典属国的职位不得不让人唏嘘。主上宴请群臣,我诵读华章。
他的泪眼婆娑,看着主上,看着满室不再认识的同僚,那眼神也时不时的看向我。
“先生忠心赤胆,今日荣归故土,晚辈钦佩,小子在这里便敬君长一杯!”
我与同僚,端着酒卮向他敬酒,从我缓步走过来他的眼神便一直没有从我身上离开,为什么?是为了什么他会有如此的情绪,那满满的期待最终在看清我的面容之后化作无尽的失望。
“郎是..太史令?”
我微微一笑,对先生抱拳施礼,“是的。”
此后我们在宴上便再无他话。
回到家中,我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完,尤其是昨日修定的书稿今日也未做完全,如今的我真的是时不我待。
揉揉眉心,向小厮交代好后便一头扎进了书房。
只是新墨刚刚研好,还未起笔,外院便一阵喧哗,是有人来拜访,我平素并没有结交什么人,今日刚刚百官相会想也不应该有什么人再过来拜访,我思杵着也不敢怠慢只得亲自去迎。
来人却是我如何也没有想到的----苏武!
“这里?”他看看我又环视一番院落,“司马府,子长呢?”
我看着他因为太过激动而微微颤抖的身躯,我有些手足无措赶忙接住亲身搀扶。
“先生所说,先考?”
“什么?”
谁知他听到我的话更加激动了,整个人剧烈的颤抖,脸色发白,“先,先考?”
一句话刚刚说完便身子一虚软晕了过去。
吓得我也脸色刷白,头冒冷汗,苏武刚刚从匈奴归来,是万世称赞的楷模,不要第一天就气绝在我家啊,这个过失我可真的担不起。
赶忙招呼小厮婢子,我们几个人七手八脚的将苏武抬进了屋,腿脚利索的小奴更是赶忙跑去请长安最好的医匠。
原本寒凉的天气,我的衣衫却已经湿了一大半。小厮们面面相觑也是不知所措。
“主公,这..”
顾不得形象我随手用袖子擦了把汗,结果婢子端过来的羹,有些心烦意乱招呼他们下去,如此不如我亲自在这里侍候!
只是疾医没有等到倒先等来了一道回来的阿姊与长兄,得,这次我一家人还都齐了!
原本有说有笑的两个人听到小厮七嘴八舌的形容也都是瞬间变了脸色,顾不得其他也是赶忙过来查看。
阿姊在看到苏武那憔悴苍老的容颜当时就是泪如雨下,伏在榻上轻轻啼哭,长兄虽没有那么激动却也是眉头紧缩满脸的担忧,看到医匠过来他首先相迎,扯着医匠询问病情不敢有一丝的怠慢。
“苏伯父如何?”
“君长是太过激动了,调养一下,不可再神情激动!”医匠开了一个方子小心的递到了长兄的手中。
苏伯父?整个屋子中只有我是一脸的疑惑。
阿姊拉过我为我解疑,原来苏武便也是阿翁当年的挚友,只是离开大汉之时我还太过年幼并没有记事,那年的送别想不到竟是诀别。
苏伯父苏醒过来时我们都守在榻前不敢有一丝的怠慢,环视着我们他又有些许的激动,眼圈泛红,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长兄执起苏伯父的手,阿姊为他送来汤药。
“伯父,我是姝儿啊!”
“姝儿?汝是姝儿!”
“伯父看看我,我是祎郎!”
阿姊的模样大致没有太大的变化,苏伯父还可以隐约辨认出,只是长兄,他端详了好半天,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虽有儒雅气息但脸上伤疤可怖的人竟然会是我的长兄。
“祎郎?郎的脸..”
长兄轻笑,轻轻拿下苏伯父抚上他脸颊的手,执在自己手中,“无碍。”
长兄说得轻松,苏伯父还是一阵叹息,我在外围看了好半晌才有个机会插进来,也伏跪在榻前。
“伯父,我是頔儿。”
苏武瞬也不瞬的盯着我,仿佛就在昨日,一夜之间曾经的稚子如今竟是已经长大成人,接替父任了!
“郎是頔儿?”浑浊的眼泪不住的流下,“竟是,十几年未见了..”
“子长彼..”
提到父亲刚刚平缓下来的心情立马又激动起来,那个现实他不想知道,不敢碰触。一时间整个屋室都是沉默。
“先考,十年前,便..”
“十年!”一句话,他又险些晕死过去,惊吓的我真的不敢再与他答话了。
“子长,比我还要年幼啊,十年前,为什么!”
我悄悄拭去眼角的泪水,不愿回答。阿姊与长兄也没有人回答,具是低头垂泪。
苏武,捶打着床榻,涕泗横流,“那年,彼来送我,我们相约一起再去西市的酒肆相饮!”
“如今,彼在哪儿?为什么!”
“为什么!”
..
“长兄,小弟一杯薄酒相赠,待长兄归来之日,我们再一起去西市的酒肆相饮如何?”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