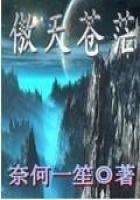夜深了,我瞪大双眼躺在床上,心想完了——白天睡多了,晚上睡不着了。
比困更让人不待见的感觉就是无聊。
要是榕榕在就好了,我们俩可以来个你侬我侬,要不然白毛也行,我们俩可以来个你死我活。
事实证明老天爷真的是存心耍我,好的不来坏的来。
骤然挂过一阵阴风,吹开了窗户,吹灭了烛火。
一名白衣依靠窗檐,白衣,白裤,白靴,肤如凝脂,温润如玉,那一头散开的长发,因为镀上了月光的银华,仿若凝霜。这样的一位男子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惊为天人’。
此时,此刻,此分,此秒,他正凝神看着我,一双丹凤眼里暗潮涌动,是说不明,道不出的情绪。
“噗嗤——”惊为天人的男子笑了——笑的跟放屁似的,而且还是个连环屁——“哈哈哈哈……”笑的前仰后合,捶胸砸地,嘴巴都快要咧到后脑勺了。
果然,无论外表装的怎么脱尘绝俗,鸟人就是鸟人,怎么装都改不了禽兽的本性。
“喂!”对他这种不雅的行为,本大爷表示十二万分的蔑视,“白毛,你笑够了没?”
没错,这货就是在山崖下跟我抢榕榕的那只白毛孔雀。
笑声戛然而止,白毛整了整衣襟,淡定的看着我,正色道:“没笑够。”随即又是‘噗嗤’的一声,如同黄狗放屁,“哈哈哈哈……”
“有本事别笑,咱俩一决雌雄。”我吼道,士可杀不可辱,‘唰——’的一声‘裂月’剑冲出脉门,握在手中。
“还有必要吗?决不决,你现如今都已经是雌的了。”说罢打量着我这幅肉身,“你别说,这乔家小姐的模样还不错,要是放在百十年前也能勉强入我的眼。”
你说这货是来找削的呢?还是找削的呢。还是找削的呢!
我一剑劈下去,堪堪削到他的面门,“今天本大爷就给你这只死鸟整整容。”
“榕榕托我来捎句话。”
剑顿住了,“什么话?”我和白毛吵归吵,打归打,可不能不听榕榕的话,毕竟她也曾经是我未过门的媳妇。
“榕儿说,咳咳。”白毛装腔作势的咳嗽两声,装的宛若大家闺秀一般,“榕儿说,没有你压制住她,她这些日子便可化作人形,所以不能有人打扰,让你安心装几天乔家大小姐,等到她化作人形后,自然会来寻你。”
我撅嘴道:“那要等多久,我跟榕榕可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别肉麻了。”白毛打断我的话,“你现在都变性了,就把你那点小色心收起来,榕儿……“语气一顿,指着自己骄傲道:”只能是本大爷的?“
”唉!“佯装没听见白毛的话,蓦地叹了口气,”罢了,罢了,两情若在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白毛嘴角抽搐道:”果然,你脑残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治。”说怕挥了挥衣袖,化作一缕白烟,飘渺而去,挺帅的——可是帅归帅,大半夜的你弄这么一出……
果然,一会儿满院子就传来了“不好了,闹鬼了……”,
“鬼啊……”
等等一声又一声的鬼哭狼嚎,本大爷捂住耳朵,暗自道:“白毛,你还真是作孽不浅。”
第二天,乔家闹鬼的传言在下人圈,以及部分上人圈,就传的沸沸扬扬,比如扫地的张大爷,被鬼下得掉进了茅坑,后院的老母猪,被鬼吓得难产,等等诸如此类的传言。
我只能再次感叹一声:“白毛,你果真是作孽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