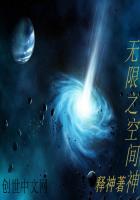低血糖只会让人短暂失去意识几秒钟,平躺之后保证血液循环,按压虎口的位置,就会很快恢复意识。即使在失去意识的这几秒钟里,仍旧可以感知外在的世界,可以清晰的听到谁在叫你,谁抱着你,谁为你垫上枕头……只是清醒后的满身虚汗和一丝寒意,总是让短暂的几秒记忆化成梦境,虽知它确确实实的存在却仍不相信它存在。
初冬阳每次晕倒的时间越来越长,医生说与低血糖和血液循环不佳的病症并不相关,有时是病人自己想借着第三空间的处境休息,才会多睡一会儿。晚上九点钟,她还没有醒来,六六和徐清风守在病床边,这个情景就像一年前的那天,她晕倒在火化场的时候。
“大括号,你说让冬阳重新遇到凌晨是对的吗?”六六看着脸色苍白的初冬阳。
“别胡思乱想了,冬阳下午插花的时候多开心,我们都多久没看到她这样了,她只是今天太累体力透支而已”徐清风拍了拍六六的肩膀。
凌晨和张旭穿着精致的礼服推门而入,纪念酒会还未结束,交代好一切便亟不可待的来到身边。
凌晨坐到六六让出的位子上,口袋里拿出创可贴,和一小袋消毒棉。把初冬阳的手展开,手心朝上露出几个被玫瑰刺伤的小伤口,有的浅,有的边缘凝结着黑色的小血块。每次她安静的躺在自己身边的时候,都是他为她疗伤的时候,虽然心疼,但仍感谢上天给他这个机会,让他能看到她这些伤口,能为她做这些事情。只是看不到的伤口,该如何是好。
张旭把六六和徐清风请出了病房,留下凌晨。空空的走廊,灯光却异常亮。六六靠在徐清风怀里,透过病房门的透明玻璃看着凌晨为冬阳小心翼翼的贴创可贴,他隔着病号服摸索着她腿上的疤,他给她擦干额头的冷汗,握着她的手安慰她。只是阵阵酸楚,只是局外人的惋惜:“如果那时候,他能这样对她,今天的一切就不会这样了。”
“六六,我请你们出来是想单独跟你说,冬阳这次的意外受伤,我怀疑是我们公司木村的人做的手脚,你在公司这么多年,应该比冬阳更了解我们公司的这些纷争”张旭坐在靠椅上,找出那张照片递了过去:“这是我们去天京出差的那天晚上我拍的,她发高烧,把凌晨看成了林嘉。”
六六接过手机和徐清风对视一下:“你是说,是因为这个冬阳以后会有危险是吗?”
“可以这么理解。”
“那我们该怎么做,让冬阳辞职离开凌海,离开盐城,是不是就没事了”六六焦急的拽紧徐清风的胳膊。
“你很清楚,现在这个时候无论她去哪里都会被人监视,她被木村视为凌晨的软肋,山下正一也算瞎猫撞了死耗子,猜得没错,她也的确是。所以我打算把冬阳接到我们身边,既然是凌晨的软肋,只有肋骨不离开身体别人才无从下手,你能明白我说的吗?”
“可她不会愿意的。”
“不错,所以我想请你帮忙。你这么聪明,应该不用我教你就知道怎么说吧。”
六六看着手机里的照片,又抬头看着抱着自己的徐清风,他对她点点头,张旭说的没错,让冬阳呆在凌晨身边这或许是最好的方法。毕竟除了自己,冬阳算的上举目无亲。而今天发生在眼前的一幕一幕又让自己清楚的意识到,凌晨,他是在意冬阳的。
凌晨这时开门出来,低声说:“她醒了,应该会找你”说完靠着墙边的排椅坐下,在她微动睫毛时他逃了出来,不想让她为难,以后也不想再质问她,就这样悄悄隔着一堵冰冷的墙守着她,像影子一样不离开就好。
张旭跟着六六和徐清风进病房时,对凌晨微点一下头,表示一切已安排妥当。
“冬阳,你醒了,感觉怎么样,这次怎么睡这么久?”六六焦急的趴在床边询问。
“好久没弄花,太累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大病没有,小病一堆”拉着六六的胳膊借力坐起来,徐清风也遥高了病床。
“你可真是为了公司肝脑涂地,尽职尽责了,张特助是不是该给我们冬阳发个大红包呀?”徐清风调侃道。
“别说红包了,帮了我这么大忙,以身相许也是愿意的,就是怕我们小主嫌弃”张旭做着讨好的表情坐在冬阳床头:“小主,不如您收了奴才吧,有什么吩咐,奴才定当尽心竭力给您完成。”
“我可不敢收,就我这小身板可养不起你陪嫁的三宫六院”初冬阳开玩笑道。
徐清风笑着给还有些犹豫的六六使了一个眼色。六六故作生气:“我们可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张特助,你把冬阳伤成这样,我现在外派郊区又不能照顾她,她这可算工伤,陪你跳舞,为你插花…你可要负责到底的。”
“绝对没问题呀,反正我也一个人住,还配备一个保姆,小主最近就到我的寒舍休养吉日吧,免得小六子担心,看不好公司的图纸可就坏大事了。”
“好啦,好啦,没你们说得那么严重,我自己可以照顾好我自己。你们别一唱一和的了”初冬阳笑着拍了六六手一下。
“冬阳,我们说的是真的,你不去张特助那,六六会担心的。我们最近还要忙婚礼的事,所以顾不上你,你先去他那借助几日,等你伤好了再回家,行吗”少言的徐清风也出口相劝。
初冬阳也不想让六六担心,不停的摸索着手指上不知何时多出的几个创可贴看着张旭:“你一个人住?我去会不会耽误你繁衍不息的业务。”
“放心吧,我的业务从不带回家,让她们知道我住哪儿可是泄漏商业机密呀。”
“那你不怕我把你卖了?”
“你光靠卖我的机密的钱这辈子都衣食无忧了,但我相信你不会,因为我伺候你,你也会衣食无忧的。”
“没正经”只是你来我往的玩笑话病房不再那么冷清,初冬阳摸着创可贴,混混沌沌中一个人小心翼翼贴它的样子。
走廊的排椅上,凌晨的身边不知何时落座了木村辉。两个敌对的人平静的坐着,依靠在门边的两个排椅,听着里面的小喧闹,安逸的待着。
“你和哈娜是什么关系?”木村辉闭着眼睛发问。
“是你让人伤了她吗?”凌晨侧头看着他。
“不是”睁开眼睛,看向看着自己的凌晨:“不过的确与我脱不了干系。”
“我们没什么关系,她和我接吻,是因为她发高烧把我错认成了林嘉”目视前方。
“那你为什么不拒绝?你的解释连我都说服不了,又怎么瞒过山下正一那只老狐狸,徒劳了,你已经把哈娜拉进你们的局了。”
“你想怎么样?”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一点也不稀罕你们凌海的这些股份,也根本不想参与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与其说是被委任为木村企业的代表,不如说是流放。”
“你想跟我合作?”
“不不不,误会了,我虽无意加入这场水平不高的战局,但我更无意伤害我自己的家族。我来找你理由很简单。把哈娜交给我,你保护不了她,而我可以”木村辉站起来:“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把她交给我,我等你联系。”
高级住宅区的角落里一处小院,一栋欧式的两层小楼,院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叶子由盛夏的油绿转向今日的紫红。清晨的阳光给红屋顶披上金黄薄纱,脚下的小路也泛着点点星光。
张妈听到车声开门出来:“旭少爷,您回来了。这位就是小初姐吧,您的房间已经给您准备好了,我扶您进去休息。”从张旭手中接过初冬阳的胳膊,楼梯旁的房间走去。
“张妈,剩下的事拜托你了,我去睡个回笼觉,冬阳你刚从医院出来,也接着睡一会儿”张旭一溜烟跑上了楼。
“阿姨,叫我冬阳就好”
“好,冬阳,以后叫我张妈就可以。少爷说你腿受伤了,上下楼不方便,让你住在楼下的房间,你看看还满意吗?”
房间里的床单被子都是花系列,桌子书柜上摆了几十只不同颜色的蜡烛,都是新的。床边的行李箱好像和自己的一模一样。矢车菊花丛中一位身着红色长裙,一只手按着头上的大摆圆边帽,阳光洒来的位置微仰起头的背影,有阳光的金黄又有星夜的斑斓暗灰,只是花丛里姑娘被风吹起的裙摆旁躺着的少年闭着眼微笑着。这幅油画挂在床头,阳光透过窗户像聚光灯一样照在它身上,让人不得不注目。
“这画是少爷画的,十几年前画的,那时夫人周末的时候会请老师来教他油画,这幅是他的结业作品。之前一直挂在少爷的房间,昨晚才拿下来挂在这的,希望你能喜欢。”
“房间很干净,也很漂亮,谢谢张妈。”
“少爷把床单被子都换了新的,有些摆设也是新添置的,我在这做了这么多年,还没见少爷对谁这么用心过呢,我们少爷……”
“咚咚”斜对着房间的楼梯下的小门里透出的声音打断了张妈的话,让她恍然记起昨晚凌晨的嘱托。
“张妈,这个小屋里面是做什么的,怎么好像有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哦,没什么,你听错了吧,可能是楼上旭少爷打沙袋的声音,这里只是个杂物间,没什么东西”张妈搪塞到:“对了,六六和她男朋友昨晚来这里把你的行李送了过来,我都整理到柜子里了,要是还有缺的,你就告诉我,我去买回来就好。”
“太麻烦你了张妈,我自己收拾就可以的。”
张妈扶着冬阳坐到床边:“不麻烦,不麻烦,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你休息会儿,早饭就不喊你吃了,午饭的时候我再来叫你。”
“好,谢谢张妈。”
“不用这么客气。”
剩下一个人在房间,初冬阳摸着床头的画,画里的人似曾相识,房间里的摆设跟自己的卧室也有几分相似,想不到大大咧咧的张旭,也有细致入微的时候,真是让她们几个为自己费心了。窗台上铺满蕾丝布,趴在上面,可以看到满院的风景,游泳池边的凉亭,几棵枯树脚下小白蘑菇,几朵自己叫不出名字的野花,似乎像是法国鸢尾,还有蔓延到窗边的爬山虎。院子不大,被妆点得很充实。
一个人吃了简单的午饭,喝了张妈特地炖的山药排骨汤,坐在院子里的小桌上捧一本张爱玲的《金锁记》,里面的七巧也住着这样一座别院,可惜一辈子都被这别院束缚,坑害了自己,也害惨了自己的孩子。初冬阳是同情长安的,每一次读到“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心中总是一番苦涩。上大学后,生活在手机电脑的娱乐生活里,刷着企鹅,微博,追韩剧,好久没有如此惬意的读书了,只是过去的一年虽空闲却总是在发呆和睡觉中徘徊,家里的书早已落满尘埃。
“冬阳,我要回家了,你想吃什么告诉我,我周一早晨来之前会顺便买菜过来”张妈挎着菜篮提着包,从房里出来。
“阿姨,我不挑食,您随便做就好。”
“那明天见。”
“阿姨,再见”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
院子里闲置的几个兔笼子锈迹斑斑,扔在墙角。初冬阳拖着左腿移到笼子旁,院墙下倾洒的爬山虎盖住了大半个笼子,本是精致的小房子,之前的白油漆依稀可见,顶部还有兔子形状的铁丝围成的图案,好像孩子被丢弃的童年玩具被遗忘在这个角落里。
心血来潮想把这份遗忘唤醒,想起斜对门的小仓库或许应该有自己需要的工具,拖着腿向房里走去。总觉得有双眼睛在哪个角落里注视着自己,不知是不是换了住处的错觉。一步步靠近那个门,气氛变得诡异,女人的直觉总是那样可怕,她摸着门却不敢打开,就像里面或许住着一个精灵,也同样摸着对面的自己。手机铃声响起:“起床了吗?冬阳。”
“嗯,你下楼吃点东西,张妈回家了,顺便帮我找点东西,我想给你付点房租”看着仓库的门踌躇不前,是不是该敲敲门,又没人住是仓库,为什么想敲门。
“你到院子等我,仓库里的东西太多了,你腿不方便,我马上下楼给你找。”
“哦,好。等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在仓库门口?”有些诧异。
“哦,这个,房间里装着摄像头,你抬头应该就能看到。”
初冬阳抬头,果然在右上角吊着一个发红光的小探头:“家里还装摄像头,你是又多没安全感。”
“之前住的阿姨装的,而且在出口那还贴了‘安全出口’字样呢,你没看见吗?”
一阵无语:“怪不得总觉得有人在看着我,那我去院子里等你。”
一转身,一声石头落地尘埃散尽的呼吸声,凌晨蜷缩靠在仓库的小门上,狭小的空间更突显出他的局促不安,忽然自己暗笑了起来,想不到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时刻,想不到这样的时刻自己竟然会有些兴奋如此开心,要是被加拿大的林女士知道,自己像老鼠一样躲躲藏藏估计会把她气疯。
锈迹斑斑的兔笼移到自己窗下,里里外外粉刷成白色,蔓延的爬山虎被几根细铁丝固定在笼子边缘的铁柱上,笼子顶端的兔子提手用爬山虎扭转成很好看的花,点缀在兔子耳朵边。张妈明天才来上班,张旭出去忙他所谓的业务,家里就剩下她自己。初冬阳站在院子里伸个懒腰,闭着眼睛呼吸着略带青涩的草绿味,初秋的露水味。一睁眼看到院子里晾着自己放在屋外洗衣箱里的衣服,内衣内裤袜子随着早晨的微风在自己眼里轻轻摇晃,只是觉得不真实。
厨房炖好的排骨汤香味怡人,还有一盘自己最爱的油焖大虾,倒好的牛奶。无论自己想干什么,总有一个人隐形人在自己之前做好一切,幻觉还是真的有个透明人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初冬阳靠在房间的窗户上,窗外空荡荡的院子,摆弄着窗边的爬山虎叶子。正欲关窗,草地上的那个黑黑的修长的人影让她一颤,从刚刚一直未移动过的那个身影,仔细看看的确是人的影子,是他的影子:“要是有两只小兔子住在这里就完美了,纯白色的小兔子”她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准备睡午觉。
凌晨站在窗外,等到房里没了动静,悄悄的开车出了院子。躺在床上的初冬阳听见院门自动关上的声音睁开眼睛,一瘸一拐的推开斜对面楼梯下小仓库的门,黑漆漆的房里轻微的显示器嗡嗡声,开门之后才听见的嗡嗡声。小到可怜的单人床,对面的墙上却挂着极不协调的显示器,显示着这栋房子房间外的每个角落,走廊、厨房、客厅、院子……床头摆着和她一样正在读的张爱玲的《金锁记》还有几本她桌子上也摆着的三毛文集,床头挂着一幅画,很熟悉,就像站在自己房间挂着画的墙里面,看清了那幅画的正面,看清画里那个裙摆在矢车菊花丛里飘起的女孩的脸。那个陪伴自己这几个夜晚的女孩,如此熟悉,只是没有猜到,会是自己,笑得如此开心的自己,就像那个雾蒙蒙的清晨,听到他对自己说“你没发现吗,其实已经变了很多了”时的自己。
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摸着胸前的平安扣,随着摇椅摇摇晃晃。阳光从开始的直射慢慢平移,金黄里增添了几分浓重的色彩,只是平静的接受着阳光的炙热。就坐在这等他回来,然后自己该说些什么呢?该说些什么以后才不会再有牵扯?闭上眼,不是在思索答案,而是那个小房间的影子,这几天偶尔会在自己身边晃过的身影,那两幅画,这些天和他重逢之后发生的点滴,还有久远久远的过去。
院门被吱呀推开,初冬阳没有睁眼睛,也没有动。停下的脚步声几秒钟的犹豫后轻轻的向冬阳走来。直到一个黑影完完整整的笼罩在自己身上,才知道他已站在自己身边。凌晨放下手中的小笼子,里面住着两只很可爱的垂耳兔。她似乎睡着了,她还是和以前一样睡得很沉,额头渗出细小的汗水,他站在她的脚边,挡住本该停留在她身上的所有阳光。掏出汗巾,伸手擦拭着她额头鼻尖的小汗珠。那时候,在操场他也这样看着熟睡的她,然后有了只有他知道的初吻。
一滴眼泪从初冬阳的眼角滑落,凌晨微皱眉头。他皱眉的样子还是让她有几分揪心。他在她的身边蹲下身子,凑到她耳边:“别怕,你还有我”吻干那滴泪。她咽下口水,睁开水汪汪的眼睛,眼圈泛红,泪水打转却不肯留下,咸咸的刺激着干涩的眼眶越发的红。凌晨也未被眼角下突然睁开的眼睛吓到,只是距离她的鼻尖定格在三厘米的位置,伸出两只手,挡住洒在她刚睁开的眼睛上的阳光,对着她笑,就像那幅画上她笑的样子。
只是无言以对的午后,长耳兔啃着磨牙棒窸窣作响,一阵风吹过爬山虎的叶子,声音像下了一场小雨,院门也吱呀一声被风轻轻关上。零星的几朵矢车菊随风转身,像见证人一样看着眼前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