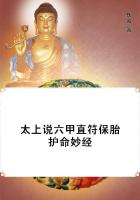从学校大门出去后,在第一个路口右拐,左边第一栋三层外贴着白瓷砖的楼房就是学校的特供楼,每层楼有着四个一室一厨一卫的单身公寓,二楼三楼都已经住满了,一楼则只有方志远一个人入住。
听老白说方志远楼上住的,虽然和方志远当年一样是县里的中考状元,却是仅差七分就考满分的变态,而方志远当年,差了二十三分。
“来,老白,这一瓶你的了。”白晓开了一瓶啤酒,递给老白。
“安近轩,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应该为了你的梦留在教室里好好听课吗?”老白接过酒,而后又从身前的两杯白酒中挑了一杯较少些许的推出来。
“**梦,猪去了BJ,回来还是猪。”方志远从身后拿了张凳子,递给我。
“听什么课,有酒喝还上课,傻子吧,虽然我有时候是挺傻,但今天可是有五粮液,逃课,不过分吧?”我接过凳子坐在白晓旁边,把老白推出来的白酒端过来。“来,一起喝一口。”
“我就说,几兄弟在一起这么开心,他不可能不来的。”白晓从兜里掏出烟,撒了一圈,而后才端起酒杯抿了一小口。
“你干嘛?不好喝是吗?不好喝倒给我,来来来。”赵立端起杯子,一口喝完后,看着才湿了嘴的白晓说。
赵立就是这样一个人,喝白酒无论杯子里有多少,就是一口闷,他自己给出的理由是慢慢喝容易醉。而白晓,喜欢小口小口的慢慢酌。
只要他俩一起参与的酒局,相互挤兑是在所难免的。
“喝酒要慢慢品,越好的酒越要慢,像你一般,牛嚼牡丹,不懂欣赏。”
“还会用成语了,小伙子有前途,看来经常来特供楼还是有点作用的。”
“你今天逃课不怕了?昨天晚上死活都要去上晚自习的人。”老白喝完酒咧着嘴问我。
“**,如果今天不是音乐、美术、体育、计算机四节没作用的课,你看他来不,你看他今天去上晚自习不?”方志远点燃烟,转头看着老白说:“也就老白这样单纯的人才和白晓那样肠子里都是坏水的人赌。”
“是的,我肠子里都是坏水,你肠子里都是矿泉水,老白单纯,你装逼,还要劝,劝不动还得动手。”白晓把桌上的牌拿起来,随意的切了两下,抽了一张明牌插进中间。“老规矩,八点,老白抓牌。”
“老白单纯?很明显,他是贪酒,怕你们喝不醉他,这点小伎俩都看不穿。”我随口回应着,心里却是渐渐有了一丝不安。
“我何时开始过着这样的生活?还喜欢上了这样的生活,居然还逃课了!”
我说完之后,他们四人都盯着我看,然后便是沉默,不仅沉默,仿佛时间也定格了,没人抓牌,甚至没人呼吸,只有香烟上不断冒起的烟线,随着时间的流逝扭曲着,而后消散在静谧的空气中。
“是这样的,第一次带你来这里的是我,方志远生日那天。”老白举起手说。
“第一次陪你喝酒的也是我们这几个。”白晓说。
“那天晚上都喝醉了,就都挤在方志远的床上睡了。”赵立指着床说。
“第二天是你买的酒和牌,是你拉着我们打‘五朋友’,是你,对,就是你。”方志远说。
“第二个周末是你叫我联系人来这里打牌,酒还是你买的,你还买了菜,说要露一手。”老白再次举着手说。
“我这人唯一不好就是有一种信念,吃人三餐,还人一顿,第三个周末是我买的酒和菜,地点还是这里,当然,你的手艺还是值得夸赞的。”白晓抽着烟说。
“**反正从那以后每个周末,你们就都像土匪一样来我这里,从不把自己当**外人。”方志远补充说明。
然后,他们四人互相看了看,异口同声地说:“这都怪你,开了个好头。”
随着他们这么一闹,那心底的一丝不安也消逝不见了。
“那还打扰你们学习了?”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到谁抓牌了?”
“打扰**,他们几个有学习吗?我还需要学习吗?”
“就佩服你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俗话说的好,别的全不怕,就怕母猪有文化。”白晓边抓牌边说。
“对对对,白晓还是有文化,俗语成语张嘴就来。”赵立抓完牌后压着底牌,说:“庄家两杯,朋友一杯,闲家一人一杯,春天翻倍,一百分朋友明牌打,春天照算,六十五起底,暗底,不埋分,不查底,老白要分。”
……
就这样,五个人,两箱啤酒,大半瓶白酒,推杯换盏,时光荏苒。
本该在学校好好上课的我们,在彼此揭短、互相伤害中度过了一个下午,我们乐于互相伤害,也渐渐的善于互相伤害。
晚上,只有我和方志远去上课,他们仨又去拿了一箱啤酒,继续互相伤害着。
方志远换了位置,坐在了我的旁边说:“安安,你还是有救的,**的,不像他们仨,彻底堕落了。”
“你没救了,已经到了眼看兄弟堕落却不伸手的地步。”
“**,他们仨,你去救他,他会拼命的把你拉下水。”
“或许在他们仨的眼中,他们并不在水里,而是在天堂,他们不过是想拉你进天堂,志远,人心并不都是那样坏的。”
“我明白,我可不是你说的那些**‘读书患者’,就**知道读书的死脑筋,只是,家世不一样,不是谁都可以像白晓一样每时每刻没心没肺的笑着。”
“你也见过白晓跪地上哭的时候,和家世无关,只是你愿不愿意而已,老白家里比你还艰难,但他,不对,我不应该劝你放纵的,毕竟,从道理上说,你是对的。”
“安安,你说,为什么做对的事情,反而没有做错的事情容易开心?”方志远难得不带脏字的说。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说。
老白沉默了,呆呆的盯着课桌上的地理书,翻开的书页上,是一副等高线地形图。
上课铃声响起,赵丽如往常一样开始点名,点到他们仨的时候,我和方志远都没有帮他们仨答“到”,因为地理老师是一个很古板的人,他讲课的时候会走到每一个空位旁边,问是谁没来,然后用下课前的十分钟,倾其所有的语言表达能力,挨个点着名批评这些没来上课的人。只是批评的效果十分有限,一是被批评的人本就没在场,二是他毕竟不是语文老师。
晚上九点下晚课,下课之后,走读生便都回家去了,而住校生,则得在教室自习到十点半。
也不是非要在教室呆到十点半不可,只是宿舍十点半才开门,除了那些恋人,几乎也没人愿意呆在除了教室之外黑灯瞎火的地方。
下课后王慧和王菊在窗外向我招手,方志远起身和我一起出去,问我要不要再喝一点,我摇了摇头,搭着他的肩膀叫他少喝点。
王慧递给我一个袋子,说:“洗干净一点。”而后拉着王菊一溜烟的就跑了,留下我呆呆的看着手里下意识接着的袋子,里面装着中午王慧穿着的那条牛仔裤。
“安安,你居然帮她洗裤子,看**不出来。”方志远看了看袋子里的裤子,而后笑着走了。
我垂下头,叹了口气,已无力解释,把袋子放在窗台上,回身进了教室,从包里拿出郭敬明的幻城,沉浸其中,久久不能自拔,直到老白勾着我的肩膀把我从雪国强行拽出来。
“你们两个好上了?”
“什么好上了,你想什么呢?”
“没好?没好你会帮她洗裤子?你觉得一个女孩的裤子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洗的?”
“我什么时候说要洗?我连自己的衣服裤子都懒得洗,我帮她洗,她想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她给我洗,我敢洗吗?我愿洗吗?她是脑残,你也是脑残?”
“那她为什么要给你洗?”
“我哪知道,别烦我。”
我把眼光重新聚焦到幻城上,却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了。
“你怎么回来了?”我合上书,转头问老白。
“听说了,就回来看看,况且,白晓要回家,赵立也喝醉了,就剩我和方志远,怎么喝?不是,我不懂,她为什么要让你帮她洗裤子?没理由啊。”
“你没跟他俩说过我是彝族?”
“没有,她们没问,我也就没说。”
“就是中午,他俩当着我用彝语说要把我灌醉,听听我的真心话,我正在喝酒,一口喷在了王慧裤子上,王菊说让我洗干净,我就说脱下来我马上洗,结果,哎!”
“你,你现在,相信了吧,你根本就,不像一个,彝族。”老白笑得前俯后仰,努力平复下来,才说。
我拿出一支烟,点燃,却被老白抢了去,只好再点一支。前座的冉风雪估计是因为听见火机的声响,转头横眉冷眼看了看我,收起桌上的书本,朝着前面没人的空位走去。
“裤子在哪,我看看。”
“你还有这癖好?喏,自己看。”我朝着王慧位置旁边的窗户指了指。
“你该不是真的不准备洗吧?”
“我说的是当时,当时她敢脱,我就敢洗,现在,过时不候。”
“又不是说让你亲手洗,你把她的裤子和你那些脏衣服一起扔胖哥家不就好了,你这样放在窗台上,总归是不好的。”
“不好吧?还和我的衣服一起。”
“有什么不好,洗干净就好,管它谁洗,而且你拿衣服去胖哥那里洗,他不也是和别人的衣服一起洗的。”
“那我把它拿回去?明天扔到胖哥那里?”
“yes,You are a gentleman。”
就这样,在老白的劝说下,我提着王慧的裤子,踏着晚自习下课铃声,回了宿舍。
“如果明天还有那么美的朝阳,你就别再把窗帘拉上了。”
“那么美是多美?”
“反正你别拉上窗帘就好。”
“明天再说吧,夜了,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