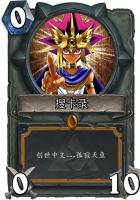“主公,莫非朝中有变故,或许正如九公子所言,开战是假,调离是真,如若不是,怡州为何无战事发生!”文骇凊已然对临行前韩鹭之言深信不疑。
“朝中之事暂且不议,我等还是专心应对战事,如今肃谷已失,虽说有了破喷火鸟之策,但后日才有大雨,倘若敌军明日攻来,如何抵敌?”韩缘与那喷火鸟虽只是初次交锋,如若不是敌将执意追杀,他未必能安然逃至太景。
“主公,莫非你忘了昔日你曾用怒天冲破西瞬鸟群之法,那喷火鸟虽说凶猛无比,但它也要低空飞行才能喷火,到那时,用怒天冲便可击杀。”
刘霸摇头道:“此时非彼时,彼时乃是攻城,我军可在阵中摆放怒天冲,守护全军,而此时乃是守城,我军怎能将那怒天冲放置在城楼之上,即使勉强摆上,可守城将士们行动不便,如何抵御敌军从云梯上爬上城楼?”
“仅仅是这喷火鸟便如此棘手,那喷火鸟数量并不多,诚之国也不过二十余只,但那绝地象不仅象牙锋利,而且全负铠甲,狂奔之时能使得地动山摇,及其恐怖!”对于绝地象,单云林也是束手无策。
“先生可有妙计破敌?”韩缘便将目光抛向了刘霸。
“主公,那喷火鸟虽说凶猛,但总数不过二十余只,我等可遣西瞬鸟骑士应敌,即使有些伤亡,但也能将喷火鸟击败,至于那绝地象,固然勇猛,并不擅攻城,倘若敌军使之攻城,我军用弓弩伤它不得,若用爆破雷,它必死无疑!”
韩缘听了刘霸计策后大笑道:“军师不愧为我肃州第一智囊,明日交战,我军必胜!”
“主公过奖。”
次日辰时二刻,诚之国敌军骤然而至,将太景城围了个水泄不通。那敌将二话不说,下令攻城,步军簇拥着云梯与冲城锤从路面杀至城墙,喷火鸟从空中袭向城楼。
韩缘亦令西瞬鸟骑士驾驭西瞬鸟腾空而起,那喷火鸟体格庞大,反应极快,还不曾近得它身,便被烧死十余人,而那喷火鸟骑士也持枪投掷,天空中西瞬鸟惨叫声不断传来,陆续有尸体从天而降。
西瞬鸟骑士冒着必胜决心,终于张弓搭箭射中那喷火鸟,却不料那喷火鸟并无损伤,好似那身体已练就得金刚不坏。
“那喷火鸟体肤怎会如此坚硬?”刘霸错愕不已。
韩缘也不答话,随即朝身旁的西瞬鸟统领附语一番,那西瞬鸟统领随即下了城楼。随即见百余只西瞬鸟升空,径直朝喷火鸟飞去,那背上的西瞬鸟骑士只是用心闪躲喷火鸟所喷火焰与喷火鸟骑士所掷枪矛,莫非他是想要撞击喷火鸟?可那喷火鸟体型比西瞬鸟大了足足两倍,即便是撞击,陨落的也只会是西瞬鸟罢了。
那百余只西瞬鸟也有不慎被喷火鸟烧伤而坠落者,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如飞火扑火般奋勇向前。直到有一只西瞬鸟撞击到一只喷火鸟身上之时,一声巨响传来,那喷火鸟与西瞬鸟尽皆被炸得四分五裂。
“是爆破雷!主公,你竟然有如此后招,属下佩服万分!”刘霸一眼便认出了是爆破雷。
原来那西瞬鸟骑士一个个都身携爆破雷,这是要与喷火鸟同归于尽之意,韩缘也是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
喷火鸟骑士见状,急忙扭头回逃,逃亡之中,不断有西瞬鸟成功撞击至喷火鸟身上,只闻得空中传来一声声爆破之音,成功逃脱者不过三两只。
城楼下的敌军也攻了许久,不曾有一人攻上城楼,城楼下已是尸横遍野,加之喷火鸟被杀,敌军士气也有些低沉。
那敌将显然是沉不住气,竟然用绝地象袭来,只见百余只绝地象在城楼下狂奔,瞬间地动山摇,城楼上守军与城楼下敌军没有一个能站得住脚。
随后,两只绝地象朝城门处奔来,用那象牙撞击城门,如若那城门不是铜铸,早已被它象牙刺得四分五裂。
刘霸被那狂奔的绝地象震得瘫倒在地,失声大喊道:“快!快用爆破雷!”
只见一群西瞬鸟飞来,从空中抛下爆破雷,那百余只绝地象被炸死炸伤者过半,但城楼上守军也有被炸伤者,这便是不用爆破雷守护城楼原因之一,爆破力度强劲,容易伤到自家军马。
所幸那城门铸得坚硬无比,并没被爆破雷炸开。
敌将急忙鸣金收兵,他敢用不寻常攻法,韩缘也敢用不寻常守法。那敌将收了兵后,便下令撤军,逃回肃谷。
单云林见状后进言道:“那敌将怎会如此行事?虽说他特战兵有些伤亡,可他依然有十万大军,只要坚持攻城,我军定然是守不住太景城的!”
文骇凊揣测道:“应是那敌将见主公用兵刚烈,不想做无谓牺牲,因此才撤军。”
“暂且休整待命,等七弟与八弟领兵前来再作商议。”
韩聘与韩茂领着五万大军一路急性,当日亥时终于抵达太景,韩缘令士卒们歇息一晚,次日听候调遣。
次日辰时,大雨果然如期而至,这深秋暴雨下了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韩缘令韩聘与韩茂领着五万大军趁着大雨兵发肃谷城。
这大雨果如单云林所料,足足下了四个时辰,未时才停。原本那敌军在肃谷城内按兵不动,忽见得大水突然朝城内袭来,城内十万敌军无不惊慌,那大水势不可挡,将这肃谷城尽皆淹没,敌军十有九死,所幸那大水只能淹没城内房屋,并不能淹至城楼之上,因此敌军尚有万余人众能存活。
正当敌军庆幸之时,只见韩聘与韩茂乘船领兵而至,那城楼上万余人众都是紧挨着,如何抵挡韩聘与韩茂大军,只得投降,只可惜那敌将乘着喷火鸟逃离,因此不曾捉得。
这大水为何会突然袭来,原来是那肃谷城西有坐山谷,山谷上有条河,那河从山谷上径直留下,经过肃谷北面,韩缘令文骇凊在山谷上筑坝,暴雨下了四个时辰,待暴雨停后,文骇凊便放坝决堤,那河水便淹至肃谷城。
韩缘得到诚之国这万余降兵后方知敌军原本就只打算攻克一城,然后坚守不出,只是那敌将心高气傲,执意要去攻太景城,因此才令特战队伤亡惨重,收兵后便下令坚守不出。
“坚守不出是何意?莫非诚之国此次入侵别有用意?”韩聘看向韩缘道,“三哥,你可知那诚之国究竟有何诡计?”
“此事来得太过突然,我还得仔细斟酌,你与八弟领这五万兵协同太景郡守兵与铭之国降兵驻守太景郡,每日遣探子刺探,如若敌军再来,飞马来报!”
韩缘吩咐既定,便同刘霸、单云林与文骇凊回了肃宁。据那降兵之言,敌军愿意便是只攻一城,然后按兵不动,显然是有意拖延,究竟为何拖延,令韩缘百思不得其解。
韩缘寄出家书迟迟未有回信,也不禁令他有些焦急。按理说这一骑飞马来回肃宁与皓云,也补消如此之久,因此韩缘再三遣人送去家书,接连一月,已送了七封,那七个送信之人至今无一人归来。
此时韩缘正在房中写第八封家书,他已不奢望这封家书会有回信,但他无能为力,又不能擅离职守,只能多写几封家书前去。
“主公,妾有一言,不知当讲与否?”徐思鸢在一旁细声道。
“但说无妨。”
徐思鸢定色道:“妾以为,接连一月,七封家书都不曾有回信,我想必定是朝中有变,只能亲自去一趟皓云方能知晓。”
“徐姐姐所言甚是,九弟曾有言宣战是假,调离是真,如今恐怕那海泉正安心对付父亲,而那怡州未有战事便是证据,海泉必然是与铭之国密谋好,拖延二哥、四弟与主公,令你三人无法回朝救父亲!”
韩缘听了黎姝之言后,慌忙扔了笔墨,大呼道:“爱妾一言,韩缘如梦初醒!”
韩缘随即离开房间,挑了两只西瞬鸟骑士,与韩鹭一人乘坐一只,飞奔皓云而去。
一路飞去,方才知晓肃州入直州所有要道都有人把手,原来那送信之人尽皆被他们捕获,到得皓云才知城外韩家军大营早已不在。入得皓云城内方知,偌大的忠君王府竟然已经被封了。
韩缘与韩鹭便趁夜悄悄潜入严衡府中,严衡府中管家认得韩鹭,便急忙领他二人前往严衡所在之处。
只见那严衡在后院之中大哭,前方设有一灵堂,灵堂上放着尊灵位,灵位上刻有八个大字——忠君王韩腾之灵位。
韩缘与韩聘见那灵位,吓得魂飞魄散,慌忙朝那灵位扑去,放声大哭,失声大喊道:“父亲!您怎能离孩儿而去!”
“三公子,九公子,你二人为何在此?”严衡见是韩缘与韩鹭,惊喜之中又有惊慌,急忙环顾四周。
“严大人,为何我父亲会……”
“九公子,忠君王被陛下召入宫中,陛下言他谋反,令弓弩手杀之,忠君王身受万箭穿心而死。”严衡老泪纵横,“陛下还将忠君王府抄了,也不许我等大臣祭拜,因此我才在家中后院暗设灵位!”
“放屁!父亲忠心耿耿,无人不知,怎会谋反,是那狗皇帝血口喷人,我韩鹭不杀他誓不为人!”
“两位公子,切莫冲动,你等且回肃州,与其他公子一同起兵,杀奔皓云,兴师问罪,我严某必当全力支持,到那时里应外合,皓云必破!”严衡咬牙切齿,满心愤怒道,“那狗皇帝不辨忠奸,听信小人之言,此等无道昏君,人人得而诛之。”
韩缘在一旁一言不发,眼神也变得极其黯淡,心中充满了恨意,眉宇间显露出一股冰凉的杀气,冰冷冷的声音传来:“此仇不报枉为人!九弟,随我回肃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