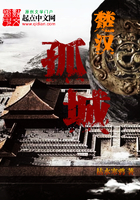“夫人,少爷都跪了一宿了,再跪下去会伤身子的。少爷身上还有伤呢。”一个苍老的声音充满了心疼和担忧。
“让他跪着,这个不懂事的东西,先帝教了那么多年怎么还是这么个样子,做事如此毛躁将来如何成事!此事必然要在朝中闹出乱子。”一个女子怒不可遏。
“唉。”老人叹息一声,出去了。看着园中的景色,还是那般,可是园中主阁前却跪着一位少年,剑眉凛凛,英气逼人,许是跪了一宿,又许是手上有伤脸上显出掩不住的疲惫和苍白。
“少爷,你这还有伤呢,咱们先去把药上了,吃点东西再来跪着,身体要紧啊。”老人又在少年面前连哄带劝的说着。
“老管家我无碍的,此事本就是我先做错了,待母亲气消再去也是一样的。”少年疲惫的脸上强打出笑颜。老人也不再劝了,这是第几次他自己都说不清了。
“唉。一家子一样犟,王爷是个犟筋,犟的几年不回来,少爷也是个犟筋,犟的带着伤不吃不喝一跪就是一宿,夫人在王爷不在的时候也是个犟筋,要是王爷受了伤看你还这般心硬!这会肯定哭天抹泪的。呸呸呸。我这乌鸦嘴,王爷不会受伤的。小郡主再大些是不是也是个犟筋。唉。这一家子小犟筋。”老人低声自言自语,摇着头无奈的走开了。此处正是兴都北城,大将军王府,沁心园。
兴都东城,一处府邸。门口的石狮子怒目圆睁,门楼也是威武不凡,院内摆着各种各样的兵器,各种练武器具一应俱全,一看就是武将世家的府邸。府中却清冷异常,门口更是门可罗雀,与大气磅礴的府邸相比,这清冷的气氛却是有些不合常理了。
府邸后园,几个丫鬟和下人在一间不大的房前站着,面色焦急,像是在等着什么。家中的主人去世的早,只留下一个小少爷,而昨夜子时,下午还欢喜出门的少爷却被人抬了回来。幸好送少爷回来的人也带了医官,不然深更半夜的兴都虽大但他们也真不知道上哪去找个好医官为少爷治伤。
在他们不远处的石桌旁,两位少年更是一脸愁云,而旁边的一位将军倒是从早上过来就大大咧咧的在府中个出溜达,溜达的累了就过来与两位少年闲聊。与这三位都不同的是一位裙摆上血祭斑斑的白衣女子,他们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可是这位女子却像是个呆子一样,只是看着少爷的那间房间,不说话,也不休息,少爷被抬进去一宿,她也在门口瞅了一宿,绝世的容颜配上沾血的裙子,让这些下人没有一个敢靠近,有两个小丫鬟甚至认为这是说书人说的勾人摄魄女鬼。
兴都,皇城,勤政殿。
庞大的宫殿气势恢宏,琉璃瓦在晨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勤政殿中,一人四十来岁模样,身着龙袍,冠九旒冕,端坐在鎏金九龙椅上,威仪万千,龙袍上金线所绣的金龙栩栩如生,九旒冕的珠子垂在脸前轻轻摆动。此人正是月国皇帝慕楚云。龙台之下,百官肃立,左边的朝臣以睿王钱王和宰相岑安为首,是朝中文官。右边的朝臣因大将军王多年不朝,所以以羽林军将军魏武,辅国将军张百川,车骑将军秦东为武官排首。之后文臣武将按官职品级站成八行八列取八方臣服之意。
“早朝开始,众臣议事。”龙台上的太监尖声喊道。
言毕,文臣班中走出一人,行礼道“臣,御史台杨宁,启奏陛下,镇西将军宇文贪狼目无国法军纪,私离驻地秘密带兵进京,其心难测,望陛下严查。”
钱王睿王对视一眼,轻笑不语。
“哦?城门校尉何在?杨御史所言属实否?”慕楚云威严道。
言毕武将之末出班一人,急忙跪下言道“回陛下,昨日酉时宇文将军带一百亲兵入城。”
“启奏陛下,不仅如此,臣听闻,昨日宇文将军带兵入城直奔醉梦阁,并大闹醉梦阁,打伤威烈公南宫青云,慕亦城小王爷也受伤,血洒当场。更激的小王爷对儒家有所偏视。此事见者众多,今日已传遍兴都,若陛下不加严惩以儆效尤,众武将竟皆效仿怕是国家不宁,社稷不安。”礼部尚书孟明出班奏道。
“启奏陛下,此事臣也有耳闻,只怕不严惩不足以显陛下之威,不严惩不足以显国法军纪之用,不严惩不足以显百官嫉恶之德。”武英殿大学士陈文出班奏道。
此言一出,文臣班稀稀拉拉跪了一半,皆表示附议。
“启奏陛下,宇文将军军功卓著,在军中声望甚高,若不详查只听之言片语便定罪重罚,恐寒了镇西将军府十万大军的军心,望陛下兼听明察。”辅国将军张百川出班奏道。此言一出八成武将皆跪下齐声奏道“望陛下兼听明察。”几十个武将齐声一奏,威势滔天,连勤政殿似乎都震的抖了一抖。
“启奏陛下,宇文贪狼入京之前曾向兵部报备,非私自带兵入京。”文臣之中走出一人,虽是文臣却虎背熊腰,声若洪钟。
“既然早有报备,纳兰爱卿何不早奏?”慕楚云有些不悦。
“回陛下,臣本欲早奏,然众位大臣忙着为宇文将军罗织其心不测之罪,臣实在无机可乘。还望陛下恕罪。”纳兰破军不卑不亢的解释。
“陛下,纳兰破军与宇文贪狼早年同在大将军王麾下为将,私交甚厚,其言不可信。”御史杨宁又奏道。
“哦?杨御史这是在说我纳兰破军徇私枉法了?”纳兰破军转身似笑非笑道。
“你和宇文贪狼私交甚厚谁人不知?说你徇私枉法还是轻。”
“住口,杨御史,以下犯上成何体统。”宰相岑安厉声喝道。
“陛下,杨御史心直口快,还望陛下赦其罪,以显陛下宽仁。”岑安躬身向慕楚云走到。
“准奏,杨御史以后可要慎言啊。”慕楚云大有深意的说道。
“陛下,宇文贪狼虽不是私自进京,然他打伤威烈公,致使慕亦城小王爷受伤之事却是众人皆知,证据确凿,此事不可不罚。否则尊卑失序,于国不利。”岑安不紧不慢的奏道。
睿王和钱王又对视一眼,眉间浮起一丝愁云,心道,姜还是老的辣,宇文贪狼进京怎么会没有准备,纳兰破军又是兵部尚书,朝中武将又都是当年袍泽,私自进京这种事告不倒宇文贪狼,一个不小心就会搞的跟刚才一样,差点被纳兰破军抓住机会告他个污蔑上官,若不是岑安及时拦住并请旨,纳兰破军怕是早就将杨宁送进大牢了。只是这伤了国中重爵,又是众目睽睽无可辩解,慕亦城受伤也是事实,又不能在朝堂上说慕亦城是为救一青楼女子,即使大家谁都清楚,但是谁都不能说。重伤国公,致使王族受伤,这种罪名一旦坐实,死罪纵然可免,活罪也是难逃啊。
“刑部可有人在?”慕楚云问道。
“臣刑部尚书,郭静通叩见陛下。”
“郭卿,重伤国公,致使王族受伤该当何罪?”
“这。。”
“照实说。”慕楚云冷声道。
“启奏陛下,若无爵位,私伤国公论罪。当诛三族。”
“既如此就按律办吧。”
“皇兄不可。”睿王慕楚炎急忙阻拦。
“睿王弟有何话说?你法家也要为触法之人说情了么?”慕楚云不悦道。
睿王不紧不慢道“皇兄误会了,臣弟出自法家,自然不会为触法之人说情,然法者重功罚罪,宇文贪狼军功甚大,诛三族恐不妥,不若只杀一人,也显得我朝不忘旧日之功。”
“也好,那就收监宇文贪狼,即日立即处斩。”
“皇兄,还是不可。”慕楚炎又阻拦道。
“这又是为何?”慕楚云有些怒意。
“处斩之事,非罪大恶极之人一般只在秋后,宇文贪狼虽私伤国之重爵,然非罪大恶极之人,故请皇兄收回成命,改为秋后处斩。”慕楚炎说道。
“陛下不可,此等恶徒有伤礼教,不杀不足以平众怒,且致秋后还有半年之久,恐生变数,望陛下圣裁。”岑安出班奏道。
一时之间睿王派和宰相派的官员相持不下,大殿里的跪得就剩下户部工部的一些人了。
“额。皇兄,宇文贪狼虽然犯有重罪,然秋后处斩也是刑律所定,既然两方相持不下,不如各退一步,将日期改为五月初五,端阳佳节也算是为宇文将军找了个好日子,皇兄意下如何?”胖胖的钱王眯着小眼睛对龙台上的慕楚云说道。
看着底下争的一团乱,慕楚云也知这方法是最好的,而且只剩一月不到,便点头答应了。
“朕有些乏了,退朝吧”
“退朝。。”
“臣等恭送陛下。”
兴都东城,威烈公府。
一队羽林军冲进国公府,为首的一位百长拿出一卷黄绸子,对着众人喊道“你们谁是宇文贪狼。”
“我是。”宇文贪狼答道。
“宇文贪狼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西将军宇文贪狼嚣张跋扈,私伤国中重爵,致使龙脉受伤,尊卑失序,有伤礼教,罪不容恕。故免去宇文贪狼镇西将军之职,收押天牢,于正元元年五月初五处斩。钦此。”
“宇文将军得罪了。拿下。”宣完圣旨,那名百长当即下令抓了宇文贪狼。
“且慢。”一旁的慕天衡拦住那位百长,问道“镇西将军何罪?”
“你是何人?”那百长一脸一脸不屑。
“兄弟,他是睿王世子。别乱说话,当心落个和我一样的罪名”宇文贪狼笑道,好像刚才的圣旨和他没关系一般。
“啊?小校有眼无珠,小王爷恕罪。”那百长急忙说道。
“圣旨可否给我一看?”慕天衡问道。
那百长哪敢阻拦,只得把圣旨给力慕天衡。慕天衡看完将圣旨还给百长。那百长将圣旨收好,对慕天衡恭敬道“若是小王爷无事,我们便回去复命了。”慕天衡点了下头,没有说话。只对着宇文贪狼说了句“宇文将军保重,我等定有再见之时。”
待那队军士走远,国公府的众人才平静下来,他们至今也搞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
慕天金看了看慕天衡说“看来今日朝中出了乱子。”
“看来还是冲七叔来的。”
“睿王叔也能没拦住。”
“怨不得父王,只是这私伤重爵的罪名能大能小,不想杀你你就没罪,要杀你,这罪就比天还大。”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两人轻叹一声,看了看那间房子,还有那依旧呆滞的清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