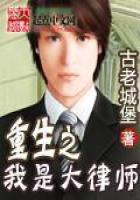拜别了父亲的韩虎去和钟离将军会合,钟离将军说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特地放两天假,大伙儿可以随意逛逛洛阳城。韩虎兄弟们欢呼雀跃,急不可耐地玩耍去了。
韩虎偷偷叫住了哥几个,责备道:“你们几个就知道玩?我们出来一趟不容易,辛苦了这么久,空着手就回去像什么话?你们一点儿也不明白将军的意思?”
“什么意思?”鲍维嚷道。
于思击了一下掌叹道:“是啊,虎兄说得对呀!差点忘了正事!洛阳城这么多显贵富户,不拿他几样,岂不白来的洛阳城?呵呵!”
“怎么?要偷东西?”黄丰乐道。
“说什么呢?这么难听?”鲍维不乐意了。
韩虎笑道:“不乐意的,可以不去。”
黄丰不支声了。
韩虎接着说道:“先说三条规矩。第一不去大富大贵之家,也不去小门小户;第二只可觅寻常之物,不可动奇珍异宝;第三,多件只可取一二件,孤件不取。听清楚了吗?”
“这是为何?”于思问道。
没等韩虎说话,乌隹道:“这还不明了?大富大贵之家,防范必严,难免会有争斗。小门小户本已艰难,再取岂不心头剜肉?寻常之物寻常有寻常用,奇珍异宝一则惊动太大,二则益害难辨,弄不好伤了自己就麻烦了。虎兄,是不是这个理?”
“那就不对了,”黄丰抢过话头,“奇珍异宝不取?孤件不要?那可都是值钱的玩意!”
于思反驳道:“你要这玩意卖给谁?你还想当珠宝贩子不成?”
哥几个哄笑一片。黄丰苦于辩解无法,着急之下抓耳挠腮,又惹来一阵笑。
在顺了几串珍珠玛瑙之后,哥几个经过一处宅院,翻墙进去,搜寻的搜寻,把风的把风。韩虎走过一扇窗下,忽然涌来一阵亲切感。
韩虎点破窗纸,一个熟悉的香囊放在小案桌上,正是柳瓷送韩虎的那个。顺着桌上的手臂,韩虎看见了她,正是柳瓷。这么晚了,她怎么还没睡?
柳瓷正在写信,全神贯注,看样子是在写家书。一缕乌黑的长刘海老是调皮地跑到额前,她也时常忘了再把它挂在耳后。温暖的夜灯照着她小巧的脸,玲珑的轮廓更为清晰。韩虎甚至可以看到她脸上泛着微光的柔柔的绒毛,以及可爱的眼睛里流淌的无限哀愁。韩虎凝视了一会儿,被黄丰毛手毛脚地打断了。
“看什么呢?”黄丰举着手里的一捧珠宝笑道:“这家不错呀,看看!”
韩虎看了一眼沉着脸道:“放回去!全都放回去!”
黄丰急了,趁机在窗纸孔里向里面看了一眼,笑道:“老相识啊?”
韩虎催促道:“快快,快点放回去!”
“哎!”黄丰叹口气道:“你不早说?这么多宝贝,全白忙活了!”
柳瓷久无睡意,韩虎也不愿弟兄们再等,就和弟兄们去了别处。
第二晚,韩虎安排由鲍维领着他们几个去逛,自己单独去了柳瓷家。柳瓷性情大变,趴在案桌上痛哭不已。韩虎久等不及,轻轻推开了窗。柳瓷听见响声,抹了泪过来关上窗。韩虎一用力,嘭的一声,窗框打在柳瓷的额头上,卒不及防的柳瓷直挺挺地往地上倒,后脑勺撞在地砖上,登时昏了过去。
韩虎听了一会儿,没有人来,就要跳过窗户去扶柳瓷。忽然想起钟离将军的嘱托,阴阳不得接触,否则会使人阳气大损,久病难愈。
韩虎狠了狠心,退了出来,躲在墙外的角落里,灵魂出窍,去找柳瓷。
柳瓷坠在一团白雾中,茫然不知所措,左转右撞再也走不出来,直到韩虎出现在身旁。韩虎拉着她一路小跑,很快就来到了他们熟悉的那条小河。他们躺在柔软的青草上,天空明朗,清风和煦。
柳瓷喘息未定,忽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韩虎拉起柳瓷跑向小河,韩虎跃入河中,接过跳下来的柳瓷,把她托到河沿上的一个小洞里。接着,韩虎也爬了上来,钻进小洞里。
小洞很小,似乎是以前挖螃蟹的洞,口小內阔,但刚好能藏下他们两个。洞壁很光滑,湿润而温暖,感觉很舒服很安全。
雨越下越大。韩虎问道:“雨为什么这么大?”
柳瓷答道:“雨大吗?它还不及我的悲伤。”
“为我吗?”韩虎看着柳瓷,眼里一片温柔。
柳瓷低下了头,轻声道:“为我的父母!”
“他们不是在洛阳吗?”
柳瓷摇了摇头,道:“这里是我姑丈家,他们在长安。不过现在他们也不在了。”
“怎么了?”韩虎看着柳瓷问。
雨太大了,听不见雨声和水流声,只剩下单调的轰鸣声掩盖了柳瓷的声音。
韩虎从洞里扯下块儿大石头,挡在洞口,又用泥巴给糊紧,洞里又恢复了平静。
“今天,长安的家奴来报信,”柳瓷缓缓地说道,她的眼里无神,似乎是在诉说别人的事情。“他说,长安的宛家没了,我父母被新来的将军害死了,家产也全被充官,奴仆也被遣散。我没有家了。”柳瓷抬起头,对着韩虎苦笑了一下。
这个笑令韩虎倍感揪心。又劝她道:“这里不是你的另一个家吗?”
“这里?”柳瓷撇了嘴道:“以前还算衣食无忧,以后怕要看他人脸色了。”
“我父亲也在洛阳,要不你搬我家去住。”
“什么?你立功了吗?也来洛阳了?”柳瓷的眼里闪出一丝光彩。
“不,是我父亲立了功,调到京师宿卫军。现在的宅院比长安的时候大多了,还有丫鬟小厮伺候呢。虽然没有这里大,但你会觉得你就是主人。”韩虎努力打消着柳瓷的疑虑。
“那…你是…要…娶我吗?”柳瓷突然结巴起来,说完,又低下了头,叹口气道:“可是,我父母新亡,我要守孝。父三年,母三年,就是六年。哎,这六年可怎么过啊!”
“你别着急!我父亲这两天就去接我母亲和妹子回来,也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你耐心等等,我母亲一回来,就让她来接你。”
“去你家有何用?你会在六年之后娶我吗?你已经死了!”柳瓷再次陷入迷茫。
韩虎没有办法了,仍劝道:“可是……你也不愿呆在这个家…。。”
外面传来了撞击声,洞口的泥土也在发颤。柳瓷死死拽住韩虎,颤抖地依偎在他身边,不愿放手。韩虎安慰道:“别害怕,我出去看看怎么回事,马上就回来。”
韩虎慢慢起身,小心地把柳瓷安顿在一个舒服的位置,就从洞口冲了出去。
冰冷的河水从洞口轰的涌入,瞬间淹没了小洞。冷——冷——刺骨的痛包裹着柳瓷,柳瓷挣扎着,翻滚着。水掩盖了她的呼救,也撕裂了她的声音,使她所做的一切都变得无力、无助、无用。
“啊!”柳瓷终于吐出了口气,“韩虎,韩虎!”柳瓷的手四处乱抓,但摸到的只有冰凉的地面——透骨的冰凉。
柳瓷醒了,她看了看四周,终于意识到自己摔倒了。她慢慢爬起来,摸了摸疼痛难忍的后脑勺,还好,没流血。柳瓷起身去关好窗户,不久,韩虎就在窗外听到了里面的抽泣声,却一直没见其他人来。
第二天,正暗自伤神的柳瓷听到姑母叫她,柳瓷心里一哆嗦。但姑母却是一副满面春风的样子,唤她去拜见义父。
义父?哪里来的义父?柳瓷心里直嘀咕,却不得不上下仔细整饬一通,跟着姑母出去了。
随着姑母的指引,柳瓷先对着坐在贵客座位的人拜了拜,而后才抬目细看。那人一身京师宿卫军装束,中等身材,四十岁上下,眉眼像极了韩虎,只是和蔼多了。
“你是……韩伯父?”柳瓷轻呼道。
“正是。伯父也是才知道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来,你快坐下。”韩雄见柳瓷眼圈一红,有些恍惚,赶紧要把她让进旁边的椅子上。
“真是个不懂礼的娇小姐,直叫长官见笑了。”柳瓷姑母过来扶着柳瓷打圆场,不小心碰着了柳瓷的后脑勺,柳瓷痛苦地呲了一下嘴。
“豌儿姑娘有伤?刚好伯父带有药箱,让伯父施展一下手艺如何?”
柳瓷姑丈道:“有伤?是怎么回事?”
柳瓷回道:“是我自己不小心碰的。”
柳瓷姑母道:“有伤就要治嘛!来,坐下。”
韩雄向堂下招招手,又被韩雄找回来的那个小厮抱着药箱趋到韩雄身边。韩雄让姑母小心分开柳瓷的头发,韩雄仔细看了一番,说道:“不妨事,只是有些红肿。我这里有药膏,涂抹几天,就会见好。”
“还不快谢过韩长官!”姑母催促柳瓷道。
“我本是军医,举手之劳而已。”韩雄回到座位,接着说道:“我今天来,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给你说,瓷儿姑娘,你看看这封信。”
柳瓷迟疑地接过信,打开来,竟是父亲的手迹,泪水忽的就涌了出来。泪眼婆娑中,柳瓷艰难地看着信,这是父亲在韩虎战死后写给韩伯父的信,柳瓷硬撑了几次,再也读不下去了。
韩雄缓缓说道:“令尊膝下无子,宛老爷待虎儿视如己出,虎儿也敬之如父,伯父可不能忘记他这份情谊。如今,瓷儿姑娘若不嫌弃,奉我一碗茶,叫我一声义父,我也好还了柳老弟的心意。”
柳瓷泣不成声,泪光里看着韩雄殷切的眼神,浑身颤抖,不能自已。姑母赶紧递过一碗茶,催促柳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