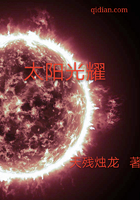“喂,你没死吧?醒醒!醒醒!喂……咳…嗯,不就是被几个牲畜咬了几口?伤得也没多重啊,不至于呀……咳…咳,哼,哪买的酒?真够烈的,也不知掺杂了什么假药草没?差点呛死爷了…咳……嘿!有了!哈!嘻嘻!“
“咳…咳……”
仿是荒洪的浑沌被擎天一剑劈裂两半,一股气直冲昏神穴天门,他一下激醒过来,张大嘴巴猛呼气。
“啩咻…”
他一下蹩不过气,大口大口吸着久维了的空气,很清新,充满了黎晨的生机,“我没……还没死?”
………
“你是还没死……不过我说,你是不是应该先同我说句对不住?……,给你灌酒是不对,但你即是再大不满,也不应该如此对待你的救命大恩人吧!”
仇望黎炸然大醒,顺声望去,这才发现一个黑色秀发穿着蓝色绸衣的翩翩少男双手握着一酒坛,正满脸怒容地注视着他,顿时吓了一跳。
那黑色秀发的少男正抖动肩手的绸袖擦拭着一脸湿漉酒味的发鬓,很是狼狈。
“就是你过于激动,我可以理解。但你也应告诉我一声啊!不必一醒来就如此答谢我吧!”
“咳……这!……这!……”仇望黎霍然惊醒,尚有一丝糊迷地望着眼前这位大是火气的“古怪”男子,整理清思路,愣过神,也明白了事情的经过。饶是他脸皮再厚,也不由得尴尬地咳笑几声。
“罢了!醒了就好,看在你没死的份上,也实是够可怜的,也就不责怪你了。懒得我废工夫同你东西瞎扯的无聊聊!算爷我倒霉!”少男没好气地看着仇望黎冷声道。
责怪?没死的份上?实在够可怜?……
仇望黎看着眼前这位豪迈又傲慢的大爷,实在无语,有一种鸡蛋扔石头的感觉一一无奈……
“是……阁下救了……我?”仇望黎从小没跟他人说过几句话,便是没人时自己跟自己也说不了几句,有谁会在意一个乞儿呢?谁会喜一乞儿?谁会同一乞儿说话?谁会不嫌弃他?乞儿是没有心的,因为没人陪他们说话,乞儿不会说话。乞儿说话只为乞讨,只为活下去。
而陪乞儿谈语的人,不是傻子便是傻子他爹。
仇望黎自知,他也不喜他们。
他少有张口,有的乞儿是不需张口的。
仇望黎是一个很孤僻的乞儿,这是仇望黎第一次与自己同一龄差不多的人说话,还是一个看似很不平凡的人。其实对他来说,只有他自己才是平凡的。
重要的是,他救了他。
仇望黎不知怎么称呼少男,便称为“阁下”这个他尽有的代他人称。
他话音微有些颤抖,明显有些慌乱。
“谢谢!”他很艰难地说道,他说的很用力。“不知阁下是谁?”
见仇望黎如此郑重地道谢,少男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用手擦拭着脸颊,挠搓了下额头,怒气尽消。
“你这人真用真,我不过说笑耍你一下玩儿而已。你真作真啊!不过,我救你还真有目的,我需要你帮我个忙……”说到后半,少男脸色一下变得凝重。
目的!?
仇望黎脸色大变,霎由苍白变成紫青。
“哈哈…你这人真好玩!太好玩了!哈哈!”少男却是一下大笑起来。
“对了,我姓余名亦。余剩的余,亦有的亦。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小室很诗雅,颇有文人风居格调。余亦的笑声显得宣嚣刺耳之极。
仇望黎死盯着余亦,全身冰冷,一颗心掉入了冰川,瞳目中透露出无限疑迷与寒意。
他是天孤,早已习惯了孤寂,他不喜投命他人而来换取生,生是自己所决定的,自己的生才是生。
他是天孤,生来独孤,这,便是他的生。为他人之下来讨他徒之巧?那他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说来可笑,他只是个乞儿,却瞧不起那些高上权贵的公子秀才公!但对他而言,不愿就是不愿,就是如此简单而已!
“仇望黎。”他语气僵硬地道,“仇苦之仇,冀望之望,黎晨之黎。”他没有多说姓或名,他的姓便是名,名便是姓,没有字。他的姓名便像余亦的名与字一样,都很独特。
“仇望黎?”余亦一直看着仇望黎,他右手抬起手中的酒坛,托着大口大口连接狂饮了好六七口,方才咂咂嘴,称赞道:“好名字!名好字也好!”
“妙!妙哉!”他也没问仇望黎哪为名,字是什么,却是直接称赞“妙哉”!
忽然,他一把将尚未喝完的酒坛冲地一摔。
可怜孤个的薄片酒坛瓦层又怎厚硬能及板实的地块?端是摔成五方七片的破烂碎块,盛着的烈酒佳酿顿时四溅欢喜飞洒,辣悚浓烈的酒味儿一下运散室内流动。
余亦眼里划过一片穹天。
眼神再落到仇望黎青白的脸上,哪还有刚才嘻哈声笑的神色!他凝视着仇望黎的眼睛,仿丝毫不察觉其中的冰冷寒意。
他眉头直竖成两条锐锋,一字一顿重重地说道:“这酒,不应用来待客朋友!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余亦的朋友!”
“接住。”隔空取物变戏法般不知何手段,一道青影便飞向仇望黎,落到仇望黎其身上盖下,却是一衫毫无花纹的青色长袍大褂。
随后,他也不顾仇望黎反应,转背过身去。
一把小刀片突然旋转着圈儿出现在他左姆食指间尖上,化成一道亮丽的白光扫成地上残留的碎瓦酒坛块片儿,归于烟粉消于虚无里!
他大步跨走出房门,冷低声道:“天门府?他几个牲畜也敢负我朋友?哼!你自睡好,明日我再陪你上前找仇,保准让天门府给你跪下磕着!”
………………
屋内尚留着浓浓的烈酒味几,久久不肯散去。仇望黎神色复杂空白地望着刚才地下残留的碎瓦屑处,已无半点丁屑片,光滑空阔一片。他很是反感地皱了皱鼻子,低咕呓语了两个字:“浪费!”
指肤触摸着盖在身上的青色长袍大褂,仿似揉捏抚顺着逸流飘浮着的青柳絮叶芽儿,丝丝的温暖之意传过指尖。
晃晃晕昏昏的脑袋,闭上双眼,疲弱地躺下。脑子一片混乱池水。
天门府?一道惊雷霹雳闪过,响起无数震波雲霁!鬼阴十地?……小阳子?……血煞?……归魂?……修仙?……阵枢?……血穹?……小路?……食尸妖犬?……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不过空梦一场?……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不!不可能,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
想来想去,他实在想不清楚,徒增疑虑,快要抓狂!锁屑就不想了。静静地躯着,却又浮上了青色长袍大褂在心头,又联想起了青色长袍大褂的主人一一余亦!
余亦?真是个他不知怎么形容的人!…嗯!……很特别!
好像有一个朋友也不错?
昏乎乎的,他又睡着了,
眉间的冰冷也变成了静谧。
……就这样,奇之又奇,又似命中有缘自定,一个天孤一个独煞,一个孤寂另一个却狂傲的两人即成为了各自生命中唯一的第一的朋友!
不问生世不问何为,只因那个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