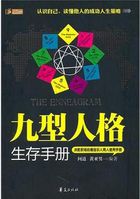右手指骨尽碎的猛逵单膝跪在泉珏面前,表情痛苦狰狞。
只是一握之力,便让谷幽族世子疼到跪下,众人哗然!
而且对方不过是个浊知境的弱者!
猛逵混在人群中的随身侍卫们眼中满是怒火,然而没有一个人贸然上前,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比试,在蛮州,随意参与或者打扰他人之间的比斗是对比斗者最大的侮辱。
泉珏绕过面前的猛逵,携杭净秋向九曲黄河湾走去,遮了半面的折扇依旧没有放下。猛逵左手扶着右腕,垂头跪在原地一动不动,众人都以为他是承受不了这等荒谬失败的打击,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他为自己今天犯下的错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失败跌倒了可以重新爬起来,指骨碎了可以重接,但他却无法阻止自己下跪的膝盖,明明不甘却无可反抗!
下跪不只是因疼痛而产生的反应,更是一种仪式,是笼罩在蛮州王室千年的阴影。
即便是整条胳膊碎了,他又怎会轻易下跪?
“我叫泉珏,白水之泉,二玉相合之珏。”猛逵身后缓步走向九曲黄河湾的泉珏说道,声音洪亮铿锵。
杭净秋摘下头顶的轻纱斗笠,露出姣好的容颜。人群沸腾,雕花楼上杭之扬尴尬异常。
既然泉珏身旁的少女是杭净秋,那雕花楼上薄纱后的女子明显是假的。就算杭家千金未曾出阁,可这个时常闹得南扬州满城风雨的少女谁人不识?
杭净秋当众摘下面纱,偏就是要给自己父亲这个难堪。
雕花楼上,杭之扬一把扯断薄纱,对着薄纱后坐着的丫鬟喝到:“好大的胆子,竟又和这捣蛋闺女合起伙来欺瞒我,给我拖下去,打断她的腿!”杭之扬不愧是在风雨中打熬多年的老狐狸,一句话便给自己找了个下脚的台阶。
“英雄出年少,美人正芳华,岂不是如花美眷?”人群中,一副说书先生打扮的中年男子叫唱道。
泉珏打败了猛逵,出尽风头,中年男子这一叫唱,引的百姓拍掌,万众喝彩。
泉珏走在九曲黄河湾中,身旁杭净秋默默跟随,他有种恍惚回到从前的感觉。物换星移,换了风景,换了人心。如同闲庭信步一般,泉珏和杭净秋走在通往绣球最近的那条道路上,扑朔迷离的阵法在泉珏面前如同儿戏,黄河湾内充斥的陷阱也没有一个被触发。两人就这样散着步,走到了绣球面前,泉珏右手遮面的折扇仍然没有放下。
泉珏将绣球摘下,递给杭净秋。
杭净秋把绣球抱在怀中,笑了起来。
灿若桃花。
泉珏转身,跨过矮墙,径直朝九曲黄河阵外走去,雕花楼上杭之扬给场外裁判使了个眼色,裁判举旗喊道:“泉珏违规逾越矮墙,出局,本次招亲试无胜者——”
泉珏心里明白,就算自己捧着绣球好好地走出九曲黄河湾,走到杭之扬面前,杭之扬依旧会千方百计把自己踢出局,所以他把绣球交给了杭净秋,把那个决定了她一生的东西交给了她。
“谁说没有胜者!”杭净秋喊道,“我就是胜者!”
她抱着绣球一步步在九曲黄河湾中走了起来,按原路退回,走得很艰难,却很坚定。
如果建立阵法的人在旁边观看一定会非常诧异,因为九曲黄河湾显然已被完全破解,现在的九曲黄河湾已经变成了一座死阵。
“胡闹!你还能嫁给自己不成!”雕花楼上的杭之扬厉喝道。
“我不是要嫁给自己,泉哥哥将绣球交给我,就是要让我自己选择未来的人生,我的人生不应该也不能被一场招亲试来决定!”杭净秋转头望向泉珏离开的方向,发现泉珏早已不知去向,之前跪在原地的猛逵也消失不见。
杭净秋突然有些想哭。
她忍住眼泪,继续认真地走起了九曲黄河湾。
她知道泉珏无能为力,她也无能为力,他们只是傻傻地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已,所以不论往后的生活如何,不论她是否会嫁入胡家,不论她是否还能见到泉哥哥,是否还能找到龙儿,是否还能向之前一样笑得灿若桃花,她都必须把今天的九曲黄河湾走完,像一个祭祀之前的仪式一样,像走完自己剩余的时光一样,像烟花一样。
美丽却又悲伤。
她还是忍不住落下泪来。
泉珏没有回客栈,他径直向北门走去,出城,走上去往东离之东的路上,继续自己的修行。
又变得孤单起来,他望了望天,这样想到。
晚霞烧红了半个天空,南扬州外青草盈野,绿柳成荫,在晚霞的映照下美得有些不真实。泉珏努力向让眼前的景色占满脑海,他想像着人们成群结队在郊外踏青的景象;想像晚霞就像血一样洒在土地里,和之前残酷的战争一般,将大地染成朱砂的颜色;想像长亭外的书生折柳送别的情形。
他还是忍不住想到了杭净秋,他怀疑自己就这样离开是否正确,是否应该看着她走出九曲黄河阵,是否应该帮她找到龙儿,是否应该折柳送别,道一声珍重。
他又开始望着天,向前走。
“我要找一只猫。”
“因为它很长啊,比一般的猫都长……”
“可以叫虫儿啊,虫儿也是长长的。”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名字才能配得上泉哥哥你啊。”
杭净秋的声音依旧回荡在耳旁,像生了根一样,泉珏摇头苦笑,明明只是相处了一天而已。
还是说他们都太过孤单。
他甚至不敢在南扬州多留一夜,他知道该割舍的终究要割舍,不该留恋的终究只能告别。
多么美丽的邂逅,只是美得太过悲伤罢了。
天欲晚,柳枝轻摆,一挂残阳。
人独走,剑袂微荡,半壁红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