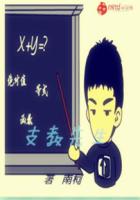(作者寄语:本作是在我最为愤世嫉俗的年纪时写的,所以有很多价值观十分激进且错误,望大家能分辨)
天气阴冷阴冷的,不见阳光。
近来几天,成CD都的天气一直就这样。伊瓦诺娃在一家咖啡屋里,隔着落地玻璃窗看着街上零零散散的路人,毫无思绪。
“我来成CD都这两天,这天气就一直是这样。”伊瓦诺娃扭头看了看坐在自己对面的俞鸿钧说道,“喂喂,有人像你这样喝咖啡的吗?”
俞鸿钧一直往自己的杯里丢方糖,丢得咖啡都快满出来了,“这东西难喝的要命,我都搞不懂为啥子你们会喜欢喝。”伊瓦诺娃笑了笑,说:“好一个乡巴佬。”
“切”俞鸿钧没作理会,只顾着往自己杯里放糖,见放得差不多,就拿着小勺子搅拌起来。“如果这次又是徒劳无功,你还会查下去吗?”伊瓦诺娃问道。他搅拌着杯中的咖啡,敲得“叮叮”作响,道:“查,只要还有时间,我就会继续查。”
伊瓦诺娃把杯子放到唇边,小抿了一口,说道:“那你有没有什么新方向?”俞鸿钧摇了摇头,也喝了一口咖啡,“哇!还是那么难喝。”接着,又继续往杯子里放糖。伊瓦诺娃看着他像吃了大便一样的表情,不禁觉得好笑。
“那你呢?”俞鸿钧问道,“如果查不下去,你就竹篮子打水喽。”
“那也没办法啊,谁叫跟我合作的人是个人头猪脑的家伙。”说着,伊瓦诺娃对着他微微一笑。
俞鸿钧白了她一眼,道:“你要是真那么精明,就不用叫我这人头猪脑的家伙陪你坐在这里喝着这些难喝的东西。”
“好。”伊瓦诺娃笑意盈盈,举起手中的咖啡杯,道:“就为了咱俩的愚蠢,干杯。”
俞鸿钧心道,这洋娃儿一定是仗着自己长得好看,经常卖笑迷惑众生。昨天在审讯室对着单面镜一笑,就已把那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廖迷得魂不附体,我可是从风雨走过来的,哪会受这妖孽迷惑!
他举起手中杯,道:“干杯就干杯。”伊瓦诺娃不知他在心里暗骂自己是妖孽,只管递杯相碰,嘴角微扬,粉唇轻咬杯缘,斜杯浅酌。俞鸿钧看着她这般妩媚之举,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愉快兀然从心头盛起,在杯子嵌于唇间之际,竟偷偷扬起笑意,也不觉咖啡苦涩。
冬雨忽地从天而降,滴滴嗒嗒的湿润了街上的尘土与行人,敲响了咖啡厅的雨蓬和窗。雨水的节奏时而轻,时而急,慢慢由小转大,像是在告诉人们,它终于来到了这片久违的土地上。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扰乱了雨水的节奏。
“喂,小华。”俞鸿钧接起电话说道。
只见他嗯嗯哦哦了几句,便对伊瓦诺娃说道:“有消息了,咱们回局里吧。”
就在他们俩前脚跨进刑侦科办公室大门时,小华就第一时间拿着份资料迎了上去。小华看着他们被淋个半湿,俞鸿钧还给伊瓦诺娃递纸擦水,一时间心里很不是滋味。
“有啥子消息了?”俞鸿钧边擦水,边问道。
正当小华想说的时候,却想起伊瓦诺娃站在旁边,当即有点儿言不由衷。俞鸿钧知道她心里的顾虑,说道:“没得关系,你说。”
伊瓦诺娃察觉到她满是提防的眼神中还夹着些奇异的感觉,就推却说道:“算了算了,有些事情我还是不知道的比较好。”又对俞鸿钧说:“我去洗手间补补妆,你要是觉得可以让我知道的就告诉我,免得我心理有负担。”说完,朝小华笑了笑,走了出去。
小华的眼睛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伊瓦诺娃,直到俞鸿钧再问的时候,她才像刚捡回灵魂似的反应过来。
“你又说有消息?愣着干嘛?到我办公室里说吧。”
他把小华领到自己的办公室,两人相对而坐。小华把手上的资料递了给他,说道:“你要找的那个柳晴诗,广州那边的同僚已经找到噻。”
“哦?”俞鸿钧看了看表,“才两个小时就找到了?这次咋这么快?”
“是的。”小华说道:“因为对于我们当警察的来说,没得啥子东西比领了死亡证的人更好找了。”
“你说啥子?”俞鸿钧愕然,道:“那个女人死了?”
“是的。”小华说着,从资料里抽出其中一张,“这就是那个女人的死亡证明和尸检报告。”
俞鸿钧看着资料上的内容,“死者左手手腕静脉处有长2。8公分、深0。8公分的直线割裂性创口,死因失血过多,死亡性质为自杀。”他一边看一边说道:“死者是孕妇,死的时候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婴儿夭折……”他越往下看,眉头就越紧,“尸体发现时,死者已经死亡接近四十八小时,推断死亡时间为2007年5月1日下午四点左右。”
“还有这张——”小华又给他递上另一份资料,“这里说,是死者的母亲发现死者陈尸于自己房间,死者母亲还要求给死者跟死者腹中的婴儿做了化验,最后还牵扯上另一起民事诉讼。”
俞鸿钧一边听,一边看着小华翻弄着资料。只听见她继续说道:“死者母亲凭着死者腹中婴儿的化验报告把婴儿的嫡父告上法庭,要追究其责任。不过,由于死者的死跟婴儿的嫡父没有直接关系,法庭不好追究其刑事责任,最后只判决他履行道德责任,赔偿死者母亲各种损失合计人民币三十万元,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可是队长,你可能万万也没得想到,这个婴儿的嫡父是谁。”说着,小华递给俞鸿钧另一张资料,“他就是顾纬越年半前在广州犯的那起命案的受害者——许明亨!”
俞鸿钧愣住了,彻彻底底的愣住了,翻来覆去绕了大圈,终究是在回到了原点的这一刻才水落石出。
只见他马上回过神来,掏出手机,把伊瓦诺娃叫到办公室,然后他把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伊瓦诺娃。“你的独家专访有着落了。”看着她脸上惊讶的表情,俞鸿钧笑了笑,说:“看来,这就是一切的序幕。”
顾纬越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走着。在他的印象中,这条路都不知道走了多少遍——领着他的还是那个民警,楼梯还是那条楼梯,走廊还是那条走廊。每当他在这条走廊上经过的时候,他都非常希望自己是直接给押上车,然后直奔刑场,最后直接给枪毙。可是,他希望的却从不曾出现,相反每次都事与愿违的走到审讯室门口。
说真的,他已经厌烦看到审讯室的大门,他讨厌那门的颜色,也讨厌“审讯室”三个大字,更讨厌开门之后所看到的一切。
在审讯室里,俞鸿钧、伊瓦诺娃和小华三人早已在此等候。顾纬越被带到椅子前坐下,那民警正要反铐他的时候,俞鸿钧却摆了摆手,示意那民警不必这样做。
顾纬越却显得有点好奇,笑了笑说:“今天的人真齐啊,是来给我送行的吗?”俞鸿钧给伊瓦诺娃使了个眼神,轻声说道:“看你发挥了。”然后与小华坐到一旁。
伊瓦诺娃也笑了笑,说:“今天不关他们俩的事,是我找你聊天而已,不过他俩非得要来,那我也没办法。”
“我跟你还有什么可聊的?伊瓦诺娃小姐。”顾纬越看了看坐在一旁的俞鸿钧,说道:“俞长官,能赏根烟吗?”
“见我一面就能记住我名字的中国人不多啊。”伊瓦诺娃笑道。
顾纬越接过俞鸿钧抛来的烟跟火机,“你是在夸奖我的记忆力吗?”说着,他点着一根烟,“入主题吧,你又来找我这个将死之人,不知有什么指教呢?”
伊瓦诺娃感到有点意外地“哦?”了一声,问道:“今天你怎么变得开门见山了?”
“说话绕圈子好累。”顾纬越说道。
“那好,我今天来是为了跟你聊聊之前还没说话的话题。”
“什么话题?”
“你的作案动机。”
顾纬越冷笑一声,“我不是跟你们说过,这个没什么好谈的。你们只需要赏我这个罪该万死的人一颗子弹就可以了。”伊瓦诺娃笑道:“你也知道自己罪该万死,那你打算死一次就能抵偿了?”
“可惜我只有一条命。”顾纬越边抽着烟边说道:“不然我肯定有多少赔多少。”
“那好。”伊瓦诺娃说道:“既然你不肯说,那你就听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顾纬越扬起嘴角,笑道:“好啊!都很久很久没人跟我讲过故事了。不过你的故事一定要很精彩哦,不然我会睡着的。”
“绝对精彩得出乎你想像。”伊瓦诺娃说着,便站了起来,她清了清嗓子。“话说从前,有一个男人深深地爱着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也同样爱着他。这男人把他力所能及的一切都奉献给那个女人,他以为,只要这样做,大家就可以相亲相爱一辈子。可是,就在他以为一切都会按照自己意愿去进行的时候,事情发生了——”伊瓦诺娃突然用双手撑在桌面上,两颗褐色的瞳孔盯着顾纬越,“那个女人变节了。”
听到这些,顾纬越噜起嘴一个颈的点头,像是非常认真听的样子。伊瓦诺娃继续说道:“那个女人喜欢上另外一个男人了,不!应该说是爱上另外一个男人了。”她在说到“爱”字的时候,故意把声音加重,“男人知道女人变节后,悲痛万分,无法自拔。伤心欲绝的他几度尝试自杀,可是却欠缺勇气。”
顾纬越手上的烟已经快烧到了尽头,可他却丝毫没有察觉。“就这样,这个男人渡过了无数个伤心的夜晚,他把自己灌倒在街上或者厕所里,但他却始终无法抛开过往的一切。不久,他就开始堕落,开始自暴自弃,他把他原本拥有的家人、朋友、事业……等等一切都当成是可有可无的废物,他的思想开始偏离正轨。最后,伤心终于把这个男人完全吞没,让这个男人失去了自我,他把自己曾经奉献给那女人的爱当作是他报复的资本,他开始想到了去摧毁别人的幸福!”
“这男人把自己报复的魔爪伸向他之前深爱的女人,他就像魔鬼一样,要彻底摧毁那女人的生活,他不停的骚扰那女人,不停的用人身安全去威胁她,甚至实施行动来胁迫那女人离开她现在的男人。最后女人不堪精神上的沉重压力,选择了轻生。”
说到这,伊瓦诺娃故意把自己的声线调成悲恸频道,“可怜那女人,芳华正茂,死的时候腹中还有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可是!”她又突然愤慨起来,“女人所遭遇的一切,正正是这个魔鬼般的男人快乐的源泉!就在他获知女人的死讯后,他兴奋地想到另一场悲剧。他想:既然这个婊子如此爱着那个姘头,而且还怀了他的孽种,那我就成人之美,送他们一家三口到地狱相聚吧!接着,这男人竟然再次痛下杀手,把他的情敌淹死在浴缸之中——”
伊瓦诺娃摇着头,叹气说道:“可怜那一家两口三条人命,就是给这恶魔般的男人,无情地践踏在血泊之中。”
“够了。”
“接着,这个男人因为身犯两命,开始潜逃——”
“我说够了!”
顾纬越猛地喝了一声,举起两手使尽全身力气拍往桌子——“嘭”的一声巨响,震撼了整个房间!这一声,把伊瓦诺娃,俞鸿钧,还有那个真以为自己在听故事的小华吓了一大跳。
房间里顿时变得死寂一片,只有那根快短路的灯管“嗞嗞”作响。
所有人的眼光都聚焦在顾纬越身上,而他却在那里坐着,一动不动。伊瓦诺娃跟俞鸿钧眉来眼去了两下,不知道接着该怎么办。小华在俞鸿钧耳旁小声说道:“队长,需不需要把他铐上?”
俞鸿钧摇摇头,示意她们静观其变。
良久,伊瓦诺娃终于忍不住这种气氛,试探性般说道:“怎么了顾先生?我的故事不好听吗?”谁知顾纬越竟然笑了起来,“哈哈哈哈,没错!你的故事就跟湿了水的手纸一样,烂得一塌糊涂!”
“哦?难道顾先生你有更好的故事吗?”伊瓦诺娃顺手推舟的问道。
“你们真的那么想听故事?”顾纬越恶狠狠地盯着伊瓦诺娃说道:“听我的故事可是有代价的!”
“什么代价?”
“你要是把故事听完,这个代价自然会找上你。”顾纬越说道,“还想听吗?”伊瓦诺娃笑了笑,说:“我喜欢未知的世界,更喜欢探寻秘密,就像剥洋葱那样一层一层地剥,这才有意思。”
“那如果我的故事只想说给你一个人听呢?”顾纬越狡黠地笑了,“而且,我不想被铐着,这有碍我的思维。那你还听吗?”
在场所有人都明白,顾纬越的意思就是想支开俞鸿钧跟小华。只见俞鸿钧冲伊瓦诺娃摇了摇头,岂料她转过头来,说:“那就麻烦两位,请通个方便了。”
只见俞鸿钧走了过去,一手把她拽了过来,轻声说道:“你疯了!这家伙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你尽管放心吧。”伊瓦诺娃说道:“那门就在我身后,难道我还跑不出去吗?再说了,这里不是公安局吗?”说着,她扭头看向顾纬越,“那顾先生,你需要俞警官把烟留给你吗?”
“那就最好不过了。”顾纬越笑着说。
接着,伊瓦诺娃把俞鸿钧跟小华生拉硬扯地推了出门,然后毫无顾虑似的把门关上。被堵在门外的俞鸿钧跟小华面面相觑。突然,他拍了拍小华的肩膀说道:“叫人过来准备一下,以防出啥子情况。”小华犹豫了一下,没有动作。俞鸿钧却催促道:“你倒是别像棵树那样站着啊!快去啊。”
“是,队长。”俞鸿钧的焦急,小华是从未见过,不知道为什么,她只觉得一阵难受的感觉突涌心头,但也没好说什么,只好按俞鸿钧的意思去做了。
审讯室里,只留下伊瓦诺娃与行动自由的顾纬越。只见她不慌不忙地坐了下来,说道:“现在就只有咱俩了,我非常期待想听你的故事。”
“是吗?”顾纬越笑了,笑得有点阴险,“我的故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却说顾父一个人坐在那家破落的小招待所里,拿着手机正说着些什么。
“嗯,是的,我明白。”他的语气里满是憔悴,眼神中尽是落寞。
手机那头是个女人的声音:“顾先生,你都知道情况了。如果可以请你尽快回来,不然可能来不及见她最后一面了。”
“是的,医生。我还想了解一下,她现在状态怎样?她感觉痛苦吗?”顾父问道。
只听见对方顿了顿,说:“她现在就是昏迷状态,偶尔醒一下,但时间不长。那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胃部了,不能吃东西了,只能够输液维持生命。她有时候醒了,但神智好像不太清醒,嘴里老喊着阿越的,阿越应该是你吧先生。”
“哦不,阿越是我们的儿子。”
“你妻子的情况在电话里头也不好说,反正我就建议你们早点回来,不要给她留下什么遗憾。”
顾父最后说了句“谢谢”,便把电话挂了。
其实妻子的病,他早就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一直以为自己有了充足的心理准备,但当事情真的来临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所谓的心理准备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他,还没有准备与妻子告别;
他,还没有准备咋去过没有了妻子的日子;
然而,他还要面对自己儿子亦将离他而去的事实。他想回去见他妻子最后一面,可他又想留在成CD都帮帮儿子,哪怕最终依然改变不了什么,那至少可以陪着儿子走完最后的路,把儿子的骨灰带回故土。
可为什么?为什么老天爷要让他在两名至亲之间作选择?
他盘腿坐在床上,一头青白相间的发丝乱作一团,两行眼泪哗啦啦地往外倾泻,满脸泪痕掩盖不住他年暮的痕迹,像是预兆着他的晚年将会孤独无依。
老人的泪水潸然而下,不禁苦问一句:“我顾万祥到底做错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