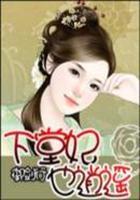晏夫人訾氏沉疴缠身好几年,没能熬过这个冬天,月半前离世,夫主晏佑安行商未归,丧仪无人主持,停棺在城外报恩寺,晏府的中馈暂且交予宠妾千落接管,大管家晏夔协助。
押送炭车的青年一边想着传闻,一边翻身下马,欣长身形穿一件竹青蝠纹劲装,袖箭鞣靴,外罩白狐皮大麾,一看就是豪绅公子。
大管家晏夔远远瞧见车马,认出是城外陆氏商行的少东陆东元,不好怠慢了,走到槅门外接待。
陆东元趋步上前拱手:“大管家安好,府上预定的十车暖炭都送到了,您老瞧瞧卸在哪个门洞口方便?”
晏夔喊来司厨的管事,领着十几个精壮仆役过去收卸暖炭。
大雪壅门,檐下垂冰,家里一大一小两个精贵主子,二十多个棒疮客患,百十名仆役,缺了取暖的柴炭可不行。
那小陆掌柜卸了暖炭,领了赏钱,恭恭敬敬作揖告辞,不忘提醒晏管家:
“家父有几句闲话,好叫您老知道,连日里雪大成灾,封门塞路,武阳城外的河面结冰三指,漕运的大船开不过来,柴、炭、米、油、棉布、白叠、细鞣皮革都紧俏起来,行情越来越涨,府上虽然囤货多……离开春解冻行船,还有好几个月的,提早筹备起来总是好的。”
说罢又作揖,也不等晏管家回话,径自蹬车而上,驭马原路返回。
晏管家在原地默一阵儿,懂了陆氏大掌柜的弦外之音。
晏府财雄势大,米油柴炭涨不涨价本不在意,焦灼的是运河从北往南冻得梆硬,在河面上走船行商的家主还没返回,连同他带出去的三百多号人手一起,杳无音讯。
月半之前,掌管中馈的晏夫人訾氏也病故,偌大一座晏府,居然没了正经主子支应门面,千落再似模似样也是个妾,她生的儿子过罢年才满十五,半大小子不服众。
晏大管家内忧外困,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撑多久,能不能撑到家主平安返回那一日,如果他也倒了,撇下千落母子势单力孤,能不能保住这座晏府?
晏管家已经五旬开外,鬓角花白,身形瘦矍,早起穿了一领蜜合湖绉精绵襦衣,外罩白麂皮长膝褂袄,内里衬着织缎底衣,腰悬青玉,脚踩玄色皮鳞履,乍一看像殷实人家的员外,半点没有下仆的寒酸黯淡。
他不但是外宅大管家,早些年还天南地北的跟着家主行商,水里火里都蹚过,又是打小伺候家主笔墨车马的小厮,极得信任,这是他能在家主不归、夫人病故的乱局下岿然不动的底气和倚仗。
连绵大雪遮天蔽地,府内悬挂的白纸灯笼、素布帷帐,连同仆役臂上缠着的孝幛都被雪色压下,不再那么刺目,人心暗流却更加汹涌。
身为淮安府有名的豪绅,晏家家大业大,却人丁稀疏。
家主晏佑安三旬开外,豪阔剽悍,十五岁那年跟随父母从北疆归籍,凭着智计过人,生财有道,一跃而成淮安府有名的豪绅,捐了五品同知的官身,人称晏大官人,常年领着几百号人手在运河走船行商,做珠宝丝帛药材买卖。
晏家的老太爷,当年携妻儿从北疆回原籍的路上就病势渐沉,回乡后第十天就殁了,太夫人悲恸过度,一年后也撒手人寰,临终前给儿子娶娘家侄女小訾氏为妻。
晏家几代单传,叔伯、兄弟、姊妹一个也无,族亲之中血脉最亲近的一房,也挂在五服的边沿外。
亲族稀疏,子嗣不丰,晏大官人三旬过半的年纪,膝下仅有宠妾千落生的庶子晏令樵,爱若珍宝,呱呱落地就抱去嫡妻訾氏房里教养。
这位晏夫人小家碧玉,柔顺贤惠,生前给丈夫纳的美妾千落,风传是从扬州花船赎出,也有人说是改嫁的小寡妇,总归不是正经人家。
这千落以色侍人,再怎么得宠,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侍妾,执掌中馈名不正言不顺。
偌大一座晏府,只剩她生的儿子晏令樵一个正经主子。
身为家主的独子,晏公子过罢这个年才满十五,却没有寻常少年人的畏寒赖床,早早就洗漱停当,穿上新穰雪缎丝麒麟通袖直裰,扎了鱼白束脚膝裤,外罩黑獭皮鹤氅,脚上犀皮皂靴,头发用素银丝镂编成的发冠束在顶上,既合服丧的规矩,又气派富贵,眼角眉梢的少年稚气也被冲淡了。
他负手背后,沿着仆役清扫出的道路,把九进的宅邸巡查一遍,经过二门东厢客院的时候,身形掩在几簇雪松后,停驻许久,脸上的表情变幻不定。
跟着他的小厮墨言忐忑不安,总觉得主子这几天古古怪怪,动辄闭门不出就罢了,还爱绕着宅院乱走,尤其是这处安置伤患的客院,每日必来探看一次。
私底下,还指派他和弟弟墨语,想办法打探这伙伤患的动静,墨言不晓得自家主子怀疑人家什么,讷讷劝说:“公子,这些人都是家主行商结识的好朋友,领头的祝三爷,晏管家也认识他,说是家主早年的结义兄弟……”
晏令樵心里哂笑,好个结义祝三爷,人前号称“簪花案首、玉面祝郎”,背后却是勾结旁人谋夺义兄家财的鼠辈!
他重生回来,比谁都清楚祝煦文是如何处心积虑,一步步取得晏家上下的信任,在晏佑安一去不归杳无消息之后,反客为主,恣意妄为。
祝煦文想先欺占庶嫂千落,再霸占晏家,诡计未遂,他又跟晏家的远房亲族勾连,诬蔑千落跟人有私情!
祝煦文带来晏家的这二三十个青壮男子,乍看人模人样,穿戴举止不俗,实则皆是老饕鼠辈,鲜有纯良之人,晏令樵暗下决心,要用快刀戳破穿这群宵小的画皮,不让他们有机会作妖。
祝煦文再怎么手段高妙,来晏家的时日尚短,发挥的余地有限。
晏令樵正好用这伙奸狡鼠辈立威,杀一杀府中的邪气,敲打敲打倚老卖老的刁奴。
想透了关窍,晏令樵长吁一口气,不觉松开了手中紧攥着的松枝,倏然腾起一簇积雪,扑簌簌溅了小厮墨言一脸,气得他抓耳挠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