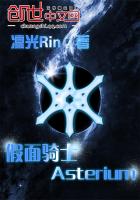他绘声绘色讲到这里,沈灵以为弟弟妹有了,脑袋“轰”的一声,人顿时倒在楚宏怀里。小禄子急忙跑上来,掐手心把她弄醒,口中不住声叫道:“新贵人保重贵体、新贵人保重贵体!”沈灵只是哭叫道:“郁剑呢?我要我弟弟、我要我弟弟!”
楚宏被哭得心神大乱,厉声道:“既然事先知道,为什么不把人救下来?”钰王道:“回皇上,不是没救,而是救不出来——”刚说到这里,沈灵悲痛过度,人又昏过去。楚宏大发雷霆,斥骂陶仲恺道:“狗奴才,你看见刽子手砍人,也不出声阻止?”
陶仲恺趴在地上,磕头道:“回皇上,那时候奴才人单势孤,如果出声阻止,恐怕会被丞相一道儿捆了。”楚宏骂道:“你这么怕死,明天朕就叫人把你的头也砍了。”陶仲恺磕头不止,口中道:“皇上,您别着急,奴才虽然没有出声阻止,可也没让刽子手把沈将军的头砍掉。”
他刚说完这话,刚刚还昏迷的沈灵一下子便清醒过来。楚宏道:“究竟怎么回事?你们不要拐弯抹角跟朕说话!”
陶仲恺又磕了一个头,挺直身体道:“皇上,丞相是天子老师,没有皇上旨意,臣等委实不能从他手中救出一个人来。”楚宏大怒,道:“谁颁布的这条规矩?你们现在就去相府替朕把人救出来,少一根汗毛唯你等试问!”
钰王翁婿大喜,领皇上口谕到相府搜人。王府里那个客卿把沈郁剑藏在非常隐蔽的地方,平安侯进去就把人搜出来,还添加了不少抽打的痕迹——这些都是遮人耳目的手段,并不用真正拿鞭子抽打在身上。
钰王一众把人送还到楚宏面前,沈灵在旁边,看到弟弟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脸都黑了,哭得话都说不出来。小禄子和一干宫女太监拼命劝,皇上却是铁青着脸,半个字也不说。
且不言小禄子张罗把人抬下去救治,但说丞相陈谦脱了官服来到延庆殿,见圣驾立而不跪,朗声道:“皇上,老臣今天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天下社稷。”
楚宏刚刚打发走钰王等人,见他不请自到,原本就不开心的心情更添恼怒,道:“丞相,朕还没有想到怪你,有什么事明天金殿再说吧?”陈谦不卑不亢,昂头道:“皇上,不管你如何处置老臣,我都是那句话,新贵人要废,沈郁剑要逐,你今天不听老臣劝告,日后倾国就迟啦!”
楚宏左手轻轻抚弄额头,一边听他说话,一边在神色间显出疲惫来,道:“丞相还是退吧,朕的头很痛,所有的事都等到明天在金殿说。”说着叫小太监把御林军副指挥使曹应钦叫过来,吩咐曹应钦带一百人众护送丞相回去。这招看起来是帝王对其老师的关心,其实是要把陈谦看押起来。曹应钦与皇上最为贴心,当下对陈谦道:“老丞相,请吧?”
陈谦对天大叫:“昏王重色,圣朝将倾……”他从殿上一直叫到殿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两句, 到皇宫门口也不停歇。奉旨看押他的曹应钦心想:“假如被京城的老百姓听到,可就大大不好了。”于是命人从衣服上撕下一角,把陈谦的嘴牢牢封住,叫他徒有满腹愁绪、一腔怨恨,从此再也说不出一句来。
延庆殿上,楚宏还撑住额头想心思,小禄子在旁边轻轻道:“皇上,时辰不早啦,睡吧?”楚宏“嗯”了一声,问沈家姐弟怎么样了?小禄子道:“新贵人没有什么,沈将军身上受的乃是皮外伤,也没什么。”楚宏问道:“那毒呢,太医能不能解?”小禄子道:“太医不能解,可是新贵人能解。新贵人刚刚配了一剂药给沈将军吃,沈将军吃下去就把胸中的毒吐出来,落在地上全是黑血,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楚宏这才放心。今天的事来得是在突兀,他心里一点准备也没有,匆匆结束后心里犹如留下一团乱麻,快刀斩了固然干脆,可是心里头那个痛呀,别人又如何能知?
钰王和两个女婿——曾广义、陶仲恺,三个人整倒了丞相陈谦,心里开心,出了皇宫未走出一射之地,便忍不住相顾大笑。耳边听到马挂鸾铃的声音,翁婿三人连忙把笑声收住,闪目看见大路那头来了一骑马,鞍鞒上端坐一人,正是他们不想见、见了还特别头疼的武阳王沈风。
沈风自从被削却兵权后,连早朝也免了,一直呆在家里不出来。今天,曾广义、陶仲恺两个人看到他,都感到这个原本得意的将军清减了不少,原本丰神俊朗的一张脸,也带上不应该属于他眼下这个年纪的沧桑之色。
钰王当先迎上来,抱拳道:“高王爷,难得见到你呀,这些天可好否?”沈风还礼道:“承蒙千岁关爱,下官好得很。”说着跳下马来,问道:“王爷刚从皇宫出来吗?”钰王“哈哈”笑道:“是啊,皇上正发着脾气,高王爷来得正好,赶上给丞相求情。”沈风低头想了想,道:“我也是这样想,如是,少陪了!”两方人分了手,钰王翁婿回府。
沈风只身来到宫门口,黄门官为他通报。楚宏正命曹应钦押解丞相回去,按说不会再见其他臣子,但是小太监把话传上去,片刻带下话来,说皇上宣高王爷。黄门官忙颠颠地跑出来,客客气气把沈风请进去,脸上表情说不出的谄媚。
沈风来到延庆殿,看见楚宏一个人坐在上面,形影孑孓,孤独桀骜冷清。他进前一步行了君臣大礼,站起来道:“皇上,您真的要惩罚丞相吗?”
楚宏从台阶上走下来道:“如果朕的回答是肯定的,你会作何想法?”
沈风道:“我会认为皇上你真的变成了一个虚伪、无情的人。”
楚宏道:“你心里本来就在怨朕,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