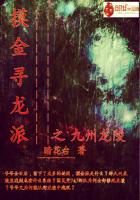张忠义道:“殿下既然什么都知道了,那么还想从罪臣这里听到什么呢?”
我被他这种不咸不淡的态度哽得心口疼,“听到什么?张大人张忠义!本宫记得你也是十年苦读一朝及第,你也是跨马东游接受过百姓叩首的,你也曾殿前立誓一展抱负!父皇赞过你廉洁,丞相誉你为君子!宛城老小都曾封你为神,奉你为青天!你就是这样给他们当神当天的?!你这是天塌了!你数数被你砸死的百姓,他们是不是你当年考场里御殿前笔下口中的‘国之根本’‘立身之根本’!”
张忠义终于变了脸色,他一直无悲无喜的脸上露出一种挣扎无奈的青白,像是一座巨峰砸在了他的身上,挣不开又受不住。
窗外是赵恒领了兵队路过的铁甲碰撞声,有孩子轻轻地抽噎透过窗随着风飘进来,混在归鸟的嘶鸣里,像是谁家在唱一首挽歌,“张大人,他们是你的子民百姓吗?”
张忠义闭了眼,过重的力气将他的脸扯得皮肉分离,皱成一团,他这个时候终于有了些人的样子,让我觉得他的心还是血肉做的,不是一块冷冰冰的石头。
“张大人,把你知道的告诉本宫好吗?”
我的问话很轻,落在张忠义耳朵里大概分量很重,他隐在宽袍大袖里的手颤抖地像是寒风里的枯叶。
我抬头望了一眼窗户,关得紧紧的,外面的冷风一丝一毫都吹不进来。
不过即便是这样,我还是能听到外面风啸的声音,明明尚是秋天,地处南方的宛城却冷得厉害,仿佛北方的跨越了山川江流,执意要在这春娇夏媚的地方安家。
“殿下……您想知道什么呢?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张忠义的声音似乎是划过枯木的老锯子一般,嘶哑得让人皮肤战栗。
与其是他是忠诚得拒不配合,倒不如说是看透一切的认命,是对自己的放逐,更是对我的同情。
可是,我又什么好同情的呢?
张忠义不再言语,我相信就凭他现在这副态度,我就是各项酷刑轮番上阵他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这样子一想倒是显得我暴虐,他是个英雄了。
我缓了一下语气,往前踱了几步,“既然张大人已经认罪了,”我从一旁的桌子上拿了纸笔仍在他面前,“倒是省了本宫严刑逼供。写吧。”
张忠义扫了一眼,然后毫不犹豫地跪在地上写了起来。即便是伏地而写,脊骨也是挺得笔直,字迹刚劲有力,横竖之间自有风骨,让人想不到他会是做出这么多残忍之事的始作俑者。
我站在他身旁,看着他将自己的罪过一桩桩一件件的地写下来,落在纸上的墨迹颜色一点点变浅。
张忠义似乎不是在写自己的罪,而是在列自己的功绩,陈列的无比认真。
整整三页纸,与成仁所说果然大同小异。
我拿起端详了半天,哼笑道:“怕是少了一点儿什么吧?”
张忠义道:“三年恶行,丝毫不少。”
我道:“不是少了什么事,而是少了什么人。”
张忠义的神色终于出现了变化,他的疑惑似乎并不是作假,他低声道,这句话却像是在问他自己,“少了什么人?”
我用笔杆在他写完的纸上轻轻敲了几下,之战簌簌的声音格外明显,“你的那位好师爷。石昊。”
张忠义皱眉,“一人做事一人当。无端牵扯别人,脱自身之罪非君子所为。”
我听得好笑,“哈哈哈哈君子?张大人啊张大人,你跟我说君子?你可别忘了,这纸上的桩桩件件又哪里是君子可为的?”
“张大人真的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张忠义从这一刻开始励志要做一个有道德心的哑巴,该说的不该说的统统不说。
“好,很好。你不说,自然有人说。”
张忠仁抬头看我。
我开了门端详,杨柳冲我点点头,我笑道:“要说的人来了。”
驿站的大门打开,绕过照碑墙走进来的是一身青衣做书生打扮的石昊。
这两人不愧是主仆,都是这么一副身不关己的泰然神色,他闲庭信步一般,好似这次只是前来向我请一声安而已。
他分外悠然地向我行了一个礼,我指指身后,道:“石师爷,不然进来聊?”
石昊点头。
他甫一进门,望见跪在地上的张忠义,大惊失色,扑过去跪在他身边:“大人,大人?”
张忠义并不言语,石昊只得又扭头向我寻求答案,“殿下,这是……”
我拍了拍自己的衣服,“你们家大人懂不懂就要跪下锻炼一下腿脚,这又不是第一次了,你早应该习惯了吧。”
石昊却完全不觉得我缓和气氛的笑话好笑,他是一点儿都笑不出来,现下这个屋子里还能够勉力笑两声的应该只剩了我一个人吧。
他低头扶着张忠义的胳膊,“大人,您这是做什么?”
张忠义自然不会回答他。
我上前几步,半弯了腰凑近石昊的跟前,在他额角脖颈处细细端详,啧啧称奇道:“果然是好手法,竟然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了。”
石昊也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人,我这一句话自然炸不出他的神色惶惶,他被我看得有些不自在,有碍于我的身份不便避开,“殿下,您这是做什么?”
我依旧是端详着他的脸,漫不经心地笑道:“没什么,有些好奇罢了。你知道的,女孩子嘛,总是拿着自己的脸当成绝无仅有的珍宝,一点小伤都受不了的,除了一丁点儿小问题”,我用手指比了个不大的缝隙,“也是要赶紧医治的。”
“那是怕要让殿下失望了,草民一介布衣,早年间风餐露宿,并不知如何呵护面皮。”石昊坦然道,说道惭愧处,还向我拱了拱手,半遮了脸。“再者说,草民没什么本事,略略识得几个字而已,殿下的相貌早已经是天人之姿,世间难寻,便是殿下想讨要什么保养秘法,所寻之人也不该是草民啊。”
我看着他那张比之寻常妇人还要白净上几分的面容笑了笑,起身离他远了些。
“石师爷过谦。”
我转身回了上座坐下,拿起不知道放了多长时间的茶水抿了一口,茶水早就凉了,此时入口,带着几分涩意,“石师爷是什么时候开始跟着张大人来着?”
石昊恭敬道:“三年前。”
这件事情许多人都知道,他也没有隐瞒的必要。三年前啊……又是三年前,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惹得他们一个人两个人都是性情大变。
“之前本宫听人说,石师爷在宛城教书,为人师表,君子端方,也不曾寻个一官半职,凭石师爷的本事,怎么就不如官场呢?难不成是看不上?”
石昊摆摆手,面上露出几分愧意,“殿下说笑了,是草民才疏学浅,当个少数先生尚且是在误人子弟,又哪里有本事金榜题名得见天颜呢?”
“不知道师爷可否婚配?”
“……未曾。”
我唏嘘道:“不知道师爷贵庚几何了?”
石昊顿了顿,“三十有二。”
我咂摸了一下,左手拍着自己的右手,“已过而立之年……怎么身边就没有个可心的人呢?你们家大人今年多大来着?似乎和你也差不了几岁吧,过不了两年就要当祖父了,”我的眼神在他身上转了转,他被我的眼神看的有些脸色发青,“总不能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石昊咬牙道:“多谢殿下挂记,不过是草民习惯了独身一人,无财无业,不愿耽误好人家的姑娘。”
我盯着他泛青的脸,情真意切地操着一颗媒婆的心,“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石师爷,不娶妻哪里来的子,没有子女,令尊令堂无法相守天伦之乐,他们恐怕是不会开心的。你想想是也不是,作为一个孝子,你就没想过娶一个肤白貌美的妻子?”
石昊似乎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可是他必须继续忍,“多谢殿下的好意,不过草民幼年失怙,早年间失恃,独身一人,并无父母催促成婚。”
“啊,原来这样,”我做出极其不忍又因自己失言而追悔莫及的神色,石昊却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就好像他口里提及的那两个人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一般。
三十有二,年少孤露,虽说是他面上已经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但是这个世界上又哪里存在毫无痕迹的伤痕?他的左半张脸从鼻翼处延绵到发际处,实际肤色略深,表面上大概是敷了什么粉,深深浅浅地一遮,不留心看竟然也没有什么异样。
“石昊?还是说,本宫应该叫你刘昊呢?”我面上含了笑意看着他,心下却没有本分的笑意,沉甸甸地压得人难受。
石昊果然是心态极好,我这样直截了当地指出他的身份,他也没有半分惊慌神色。
“恕草民不知道殿下在说什么?”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啊,”我喃喃道,“城南刘家似乎还剩了一位老妪勉强度日……也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当年的事情……”
我的视线落在他的腰腹处,我知道我说这些话令人难堪得很,却不得不说,“有些东西是生时带来的,怕是死也带不走吧。”
石昊的脸色瞬间由黑变白。
“哦?就算是草民承认本家姓刘,那又说明什么呢?我不姓石而是姓刘难不成就是罪过?殿下是有证据证明我杀人了还是有人指正我放火了?!”他这样一个克己守礼的人竟也抛了谦称,一口一个“我”自称,可见他的内心并不能再保持之前的平静,“倘若什么证据都没有,就凭殿下一张嘴空口认定我姓‘刘’是罪,恕草民做不到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