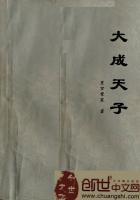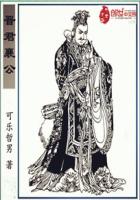三个县令连带郭正庭一起变了颜色!
郭正庭身为人上峰,此时自是要出头的:“请张将军慎言。”
“慎言?”
张昌宗幽幽一笑,终扭头正眼看向郭正庭,正容道:“使君常驻边疆,想来于本地民情上至少应该比我这个外来人熟悉些吧?边民要受突厥不时的劫掠,这是我等军人的职责没做好,但是,山匪为何却屡禁不绝?难道山匪便那般凶猛,连官军也不敌的程度吗?”
张昌宗这次剿匪是亲自去的,攻打山寨难者在于地形,而非兵卒的素质、兵器之类的。山匪里最好的武器也不过是大刀、长矛,好弓那是一把都见不着,多是些自制的竹弓,如何比得上官军的武器犀利。
更不用提人员素质。张昌宗接手十万大军已经大半年,在他手里不说令行禁止,纪律方面却非山匪可比拟。山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
郭正庭世家出身,讲的是个礼法,也是要脸的人,被张昌宗近乎指着鼻子骂他尸位素餐不作为,瞬间满脸通红,问题他还辩驳都无法辩驳。
张昌宗冷冷扫那仨县令一眼,径直道:“说来说去,山匪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聚众为乱,你们非是不能敌,说白了不过是不作为三个字,所谓的管辖权不过是笑话。”
潞县县令、广平县令俱都满面羞愧的低头,唯有蓟县县令还想辩驳:“将军容禀,非是下官不剿匪,下官也曾下令剿匪,只是,山匪狡猾,逃亡别州去了,下官总不好越界,若是贸然越界,于规矩不合,怕是早被人一本疏奏参到陛下面前了。”
张昌宗扭头看他,面上早没了笑模样儿,定定地看着蓟县县令:“怕被人参奏你便不剿匪了?便坐视之下百姓受匪患之苦?混账!你以为百姓是什么?要你这个县令是做什么的?”
为了官声考评好看,闹匪患都不管,随便寻了个借口便混吃装死,这等人最是可恶。自己庸碌还找借口……没得叫人恶心。
张昌宗连骂都懒得骂了,怒瞪着他了一会儿,扭头看郭正庭,正色道:“三州之地,唯一出兵剿匪,对山匪尚有威慑之力的,唯使君一人。原以为使君自与旁人不同,或能理解我此次贸然行动的理由,不想使君竟为这等人张目……使君何以如此自甘堕落罗?罢了!不拘是使君也好,还是三位县令,若有异议,自可上疏参奏我便是。本将军府中尚有事务,告辞,后会有期!”
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郭正庭满脸通红,都是被张昌宗骂了羞愧的,他的想法就跟时下大多数官员差不多,治下闹匪患,他也派兵剿过,只是,山匪狡猾,又熟悉本地地形,直接跑别州去了。
若他有心,这个问题操作起来也不难,问题他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见跑别州去就没再管。他所谓的剿匪,其实更多是驱赶,说是剿匪实有些虚。之所以为三个县令撑腰来拦张昌宗,不过也是出于自身的考虑,不像张昌宗——
作为领兵屯田戍边的大将,剿匪本不在他责任之内。真论下来,剿匪实为各地父母官的职责。张昌宗大概是看不下去了,才会派兵剿匪吧?这等用心,倒叫人羞煞。
“使君……”
三个县令神色各异的看着郭正庭,郭正庭沉着一张脸,道:“此事……终究是尔等做的不好,遭人捏了把柄,张昌宗即便做得略过了些,然也是一心为民,你三人各自回去,且好好查治下,莫再出这等事情,本府不想再被人指着鼻子骂却一字也回不得,要脸呢!”
三人俱感羞愧,连声应着:“喏。”
把三个县令并郭正庭骂了一顿,张昌宗便把剿匪的事情丢开,把主要的注意力投到别的事情上,整军备防,结果,防备了一段时间,连剿匪的事情都弄完了,突厥也没来。
阿椰他们传来的消息,突厥也没整军动武的意思,倒是阙特勤回去,与默啜的儿子匍俱闹了矛盾,若不是兄长默矩拦下,怕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打起来,然就算拦下了,两人也好不了了,见到了也颇为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
张昌宗看了,把戒严等级降低了几分,不过,该操练的依旧操练着。屯田自有屯田的制度和做法,张昌宗也不擅改,不是所有后世的东西就都是先进的,好的,也要看是否合乎时宜,若是不合乎当下的时宜,便是再好的政策也只能扑街。
例如历史上著名的王莽,他颁发施行的那些政策,谁看了都忍不住会怀疑他是否是穿的,政策都是后世证明好的政策,但不合乎当时的时宜,他就被人干翻了,不能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啊。
张昌宗时常在想,有着后世的知识储备,从来就不是万能的,穿越也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这个时空,这个世界,生存着的所有人,包括一草一木,都是真实的,并非是一团数据或是史书上的一句话,这是个真实的世界,为人当有敬畏之心,为官当有对百姓的敬畏之心,太宗言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实是至理名言。所有无视民心洪流的,都被洪流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了。
张昌宗身后还有一大家子,虽然他是幼子,按照时下的宗法,承宗承嗣的只能是大哥张昌期,可是,在这个时代的礼法之下,他要是行差踏错,死的除了他自己,还有那一大家子。做人不能只顾自己痛快不是?强大是为了能更好的张开羽翼护持想护持的人。
张昌宗一路想着些有的没有的,骑在马上回将军府。到了将军府门口,下了马,把缰绳丢给迎上来的马倌儿,自己摘了头盔大步往过了中门,就见薛崇秀袅袅娜娜地站在廊檐下笑看着他。
看见老婆,恶劣的心情不禁一散,面上带了笑大步走过去,不好当着一众下人的面抱人,很是克制的伸手握着人小手,满脸的笑:“秀儿妹妹!”
薛崇秀笑着抬眼望他:“欢迎回来,一路辛苦了,我已命人备下洗浴用的水,先进去卸了甲,坐下歇一歇,然后再沐浴?”
“嗯!行!”
张昌宗哪里还有不答应的,与老婆手牵手的进去。便是为了这一刻,也容不得他肆意妄为,他的身后人太多,任性不得,妄为不得。
“……这趟跑得满意吧?”
“还行,这一趟跑了,能歇上一歇。兄台你呢?”
“彼此,彼此!可惜的是,这次这般规模的队伍,并不是经常能组织得起来的。”
“是极,是极。这次大家聚在一起,声势浩大,大家召集的护卫一起,才没有盗匪拦路,大家都知道北边的皮子、药材好,可打不开商路,也只能眼看着钱财飞走。”
商队正在歇脚,准备吃晚饭。夏日昼长,天还没黑,篝火已经点起来,护卫们四散着,等着用晚饭。不远处的小山包上,一支鸣镝腾空而起,原本四散的护卫腾地站起来:“列阵!”
商队的一众商贾,愣愣地看着平日里寡言少语的护卫们,这行动倒像是朝廷才有的精兵,哪里还有平日闲散护卫的影子。
“除战斗人员外,其余人等全都躲到马车和货物后面,马贼来了!”
“啊!马贼……”
惊叫声尚未叫完,一支箭嗖地射到脚旁,惊叫声戛然而止,畏惧的迎上护卫森冷透着杀气的眼睛,还有指着自己的拉满的弓。
“听命令行事,否则,杀无赦!”
惧怕的商人再不敢乱喊,捂着嘴巴,乖乖按照命令行事,心头又惊又疑——
这……这真是他们在京里顾的护卫?怎地现在护卫也这等悍勇了?!
把所有非战斗人员都赶到马车和货物围成的圈里,所有护卫取出弓刀,严阵以待。不一会儿,视线里,一队人马挥舞着大刀,围着兜头的布巾,气势汹汹的冲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