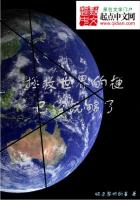不去看秦渊,段南歌又柔声细语地对殷嬷嬷说道:“听湘君她们说您这一整天都没吃东西,这粥是温的,您现在喝一些吗?”
眼神微闪,殷嬷嬷笑道:“先放着吧,老身跟五殿下说说话,说完再吃。”
秦渊扭身坐在床边,伸手端起那碗粥,笑道:“我今儿就在这里陪着月姨,咱们不忙说话,先把粥喝了。”
说着,秦渊就舀一勺粥送到殷嬷嬷嘴边。
“使不得使不得!”殷嬷嬷慌张摇头,可就连摇头都是件略显艰难的事情,“老身自己能喝,不敢劳烦殿下。”
“可是……”秦渊瞄了眼殷嬷嬷的手。
月姨那手瞧着就是使不出力气的样子,她……拿得住碗吗?
见状,段南歌将殷嬷嬷的手塞进了被子里,顺手连被子一起掖好:“月姨您就让他伺候您吧,他那么久没来看您,心里虚着呢,这是怕您心里埋怨他,有意在讨好您呢,您若不受,他晚上可要睡不好觉了。”
秦渊把嘴一撇,颇为哀怨地看斜段南歌一眼:“看破不说破,让月姨笑话。”
段南歌也笑着白了秦渊一眼,起身往桌边走去:“就你那点儿小心思,还能瞒得住月姨吗?”
秦渊扁嘴,不再说话,只委屈地看着殷嬷嬷,把手上的那勺粥又往前送了送。
殷嬷嬷眉开眼笑地喝下了那勺粥。
走到桌边,段南歌就见装着药香的香盒正摆在香炉旁,暗道湘君和云昭细心周到,段南歌打开盒子取出一炷香点燃。
“月姨,这香是药香,对您的身体有好处,我会嘱咐湘君,让她给您日日燃着。”
这些事段南歌是说给殷嬷嬷听的,也是说给秦渊听的。
果然,秦渊的眼神一沉,心里就有了底。
粥是温的,不能冷不能热,且熬得时间太久都要成了米糊,若不是月姨的胃只允许她喝这样的东西,南歌怎会特地让厨房准备?
而说起那汤药时,南歌特地提起了自己曾喝过的那副药,那副药的用途和药效没人比他更清楚,当初他顾着南歌的身体,宁愿药效慢一些也不愿用烈性药再伤了南歌,而公孙月给月姨用的方子竟比南歌那副药还要温和,而且还要以药香辅助……
是他没照顾好月姨。
殷嬷嬷的身体到底还是太过虚弱,喝完了粥和药之后,没跟秦渊说上几句话就昏昏欲睡,只是还想跟秦渊再多说一些话,就勉强支撑着,秦渊再三保证自己往后每日都会来陪殷嬷嬷说会话,殷嬷嬷这才抵挡不住疲倦,安然睡下。
段南歌和秦渊离开殷嬷嬷的屋子时,夜色已深,秦渊牵着段南歌缓步走出德灵院,回去琼莹院,仍旧是一路无话。
吃过晚饭,段南歌就去沐浴,等段南歌回到主屋房内,就见秦渊已然是一副沐浴过后的懒散模样,歪靠在床尾,眉眼带笑地看着段南歌。
“过来。”秦渊向段南歌招了招手。
眉眼一动,段南歌款步走了过去:“怎么?”
将段南歌拉到自己身边坐下,秦渊就拿过段南歌手上的布巾,替段南歌擦拭半干的长发。
眨眨眼,段南歌狐疑地看着秦渊。
他特地把她叫过来,就为了干这事儿?
瞥见段南歌狐疑的视线,秦渊反倒生出几分疑惑:“怎么?”
“没什么。”段南歌摇摇头,软软地靠在了秦渊支起的腿上。
过了一会儿,秦渊轻声说道:“爷方才回了一趟上庸院。”
“哦。”段南歌转头看向秦渊。
所以呢?
秦渊眼中的笑意加深:“德灵院里的事情爷都打听过了。”
段南歌轻笑一声,调侃道:“都是发生在你府里的事情,你怎么还要去向人打听?”
秦渊也跟着笑了,道:“可不是嘛,明明是爷府里的事情,明明该是爷费心劳力,结果却都是你在做,爷可不是为了让你受累才将你娶进门来的。辛苦你了。”
“无妨,”段南歌撇撇嘴,“德灵院里那点事算不得辛苦。”
秦渊挑眉:“怎么?你还做了别的事情?给爷说说最辛苦的是哪件?”
看着秦渊,段南歌的眉梢眼角都是柔情缱绻:“最辛苦的是想你了,却怎么都见不着。”
秦渊一怔,将布巾扔到不远处的桌上就将段南歌拉进怀里抱住:“只此一次,以后爷去哪儿都带着你。”
软软地伏在秦渊怀里,段南歌语音俏皮道:“你爱带不带,反正你若不带,我就自己跟着去。”
秦渊摇头失笑,笑过之后又道:“那苏玉姐妹……听说你承诺要让她们做回一等女婢?”
他当初怎么会让那样一对心肠歹毒的姐妹去侍奉月姨!
听出秦渊言辞中的不解和不愿,段南歌柔声细语道:“你若觉得她们不可原谅,寻个借口惩办了就是。”
“你想留下她们?”秦渊问段南歌。
“嗯,”段南歌直言道,“你这吴王府里的女婢也不知道都是谁挑选的,个个都是敦厚纯良的性子,唯独苏玉在宫里伺候久了,经过不少事似的,心肠勉强算得上是有点儿歹毒。”
一听这话秦渊心里就气,怒道:“她那样哪是有点儿歹毒?你看月姨都被她们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段南歌撇嘴:“所以我才说,若你觉得她们不可饶恕,惩办了就是,我若想用这样的人,再寻一个也是一样。”
秦渊皱眉:“你要这样心肠歹毒的女人做什么?”
段南歌这才仰脸看着秦渊,柳眉微拧:“我也有需要有人帮我出个坏主意的时候,可你看看我身边,白茗是国公爷亲自教导出来的,忠正耿直的性子像极了国公爷,但国公爷却没教她构陷他人的方法。公孙月是个医者,我能让她给想那些害人的办法吗?你安排在琼莹院照顾我的秋心虽然做事麻利,可论及心性却还是个小女孩。你觉得她们哪个能帮我出个坏主意?”
秦渊眉心紧蹙,思索半晌后看着段南歌道:“爷给你出坏主意。”
段南歌当即就瞪了秦渊一眼,惹得秦渊眉心舒展,轻笑不止。
思索一番,秦渊道:“是爷思虑不周,爷给这琼莹院里选女婢的时候就该选个能跟你一起狼狈为奸的。”
一听到狼狈为奸这个词,段南歌就在秦渊的腰侧掐了一把,惹得秦渊龇牙咧嘴地又是一阵笑。
“疼,”握住段南歌的手拉开,秦渊继续说道,“你也别再找旁的人了,就苏玉吧。”
眉梢轻挑,段南歌又仰起头看着秦渊:“容得下她?”
秦渊笑笑:“有什么容不下的?爷都容了陈江那么些年,如今还非得置于个女婢于死地不成?而且正因为她做错了事,你才能对她施恩让她心怀感激,她自觉欠着爷的,对爷也会多几分顾虑和忌惮,不敢妄为,留在你身边刚好。”
秦渊应下了,段南歌却不安心了:“我再另找一个人也是一样的,说不定还能找到比苏玉更适合的。”
粲然一笑,秦渊在段南歌的眉心落下一吻:“你若再找个比苏玉更坏的岂不是更麻烦了?就她吧。而且月姨的事情说到底都是爷的错,是爷疏忽了,没能照顾好月姨。”
偏头枕在秦渊胸口,段南歌柔声道:“只要你好好的,月姨就会好好的。”
厚实的手掌在段南歌的背上摩挲,静默半晌,秦渊似有些艰难地开口问道:“南歌,月姨的身体……究竟差到什么程度?”
早知道秦渊要问,段南歌也没想过要瞒:“公孙月说,就算十分小心地调养,月姨的寿命也只剩三五年了。”
“三五年……”秦渊抿嘴,半晌之后才再度开口,“也好,我们带她去广陵,听说那里比京城养人,有雪阳先生在,月姨能活得久一些。”
“秦渊,”段南歌撑起身看着秦渊,“月姨她……不能跟我们一起去广陵,她的身体……”
“爷知道,”秦渊打断段南歌的话,“可爷是廖氏的大当家,是天宋最受宠的皇子,爷的身边有你、有雪阳先生、有父皇、有国公爷、有廖氏那么多的人,总能想出办法的对吗?雪阳先生的方子不就把你治好了吗?”
顿了顿,段南歌扬了扬嘴角,轻轻点头:“嗯,总会有办法的,我们去请雪阳先生来再给月姨看看。”
“嗯,我们去请雪阳先生来,再去找找其他人,你身边不是还有南楚圣女就给你的人?”伸手将段南歌抱回怀里,秦渊低声念叨,“一定会有办法的,哪怕一年也好,就只有一年也好。”
回抱着秦渊,段南歌没再说话。
段南歌知道她不必再多说什么,该说的都已经说过,殷嬷嬷的状况秦渊心里自然有数,但若只是因为知道现状就放弃去争取所有的可能性,那这个人也就不是秦渊、不是廖五爷了,更何况秦渊的心里还有一份懊悔,一份对自己没能照顾好殷嬷嬷的懊悔。
这一夜秦渊睡得并不安稳,似乎是被殷嬷嬷勾起了太多与过往有关的回忆,这一夜秦渊噩梦连连,梦中胡乱的呓语总会将本就浅眠的段南歌惊醒。
段南歌也不知如何是好,每每醒来都只能握紧秦渊的手在秦渊耳畔哼唱着舒缓的曲调,直到秦渊安然睡去,段南歌才能入睡。